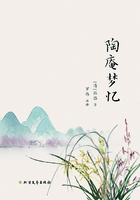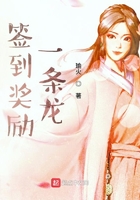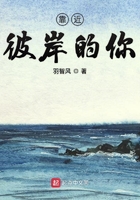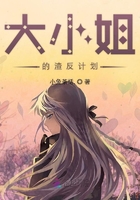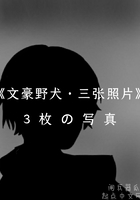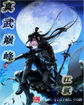吐蕃统治时期由中原传人敦煌的俗讲活动,晚唐以来逐渐兴盛起来。俗讲内容包括“押座文”、“解座文”、“讲经文”、“因缘”等,是通俗化地宣传佛教的一种形式。“押座文”是俗讲正式开讲之前转诵的一种诗篇,犹如宋元话本之开话诗词,近世弹词之“开篇”小段。押座之“押”与“压”字相同,所谓“押座”乃是一种安定听众,使其息虑收心、专致静听的手段。敦煌文献中的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等等。解座文是俗讲结束后所诵之文,同押座文一样,多由七言诗组成,解座文分别保存于P.2305、P.3128、s.2440等卷号中。讲经文是俗讲的主要内容,是俗讲的底本,取材全部选自佛教经典。敦煌文献中现存的讲经底本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维摩诘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盂兰盆经讲经文》、《说三归五戒讲经文》等。因缘,又称说因缘,与俗讲同样是一种在斋会上由僧侣演出的宗教说唱活动,主要讲佛弟子或善男信女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故事。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因缘作品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欢喜国王因缘》、《目连缘起》、《丑女缘起》、《四兽因缘》、《佛图澄和尚因缘记》、《隋净影寺沙门慧远和尚因缘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灵州和尚因缘记》等。其中如《丑女缘起》讲的是波斯匿王有一女因前世不敬佛而生得容貌极其丑陋,丑女长大后痛苦万分,遂焚香礼拜,虔诚奉佛,终于得到报应,容颜顿改,变成了一位美丽妩媚的女子。《欢喜国王缘》主要通过欢喜王与夫人有相生死悲欢的遭遇,宣扬万事皆有因果,人生苦空无常,只有皈依佛门,修行持戒,才能超拔浊世,得生天国。正是由于俗讲、说因缘等所讲唱的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群众,所以更容易为僧俗群众所接受,敦煌文献中大量俗讲文献的遗存,正说明晚唐五代以来敦煌俗讲的兴盛。
还有与俗讲密切相关的说唱形式——变文,晚唐五代以来,其讲唱范围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出现了许多世俗内容的作品,并且出现了敦煌本地自己创作的变文作品,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中原佛教影响敦煌的历史见证,而且今天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中原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还需特别提及的是五代以来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传人。五台山被佛教徒认为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之地,自北朝以来,五台山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开始兴盛起来,至唐代宗大历年间,宰相王缙于五台山建金阁寺,五台山佛教益盛,声名远扬。但五台山文殊信仰传人敦煌的时间要晚得多。从敦煌文献和其他有关材料来看,在后唐同光年间,五台山才开始成为西北诸民族巡礼、供养的对象。这一时期,随着沙州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重新沟通,有关歌咏五台山圣境的《五台山曲子》、《礼五台山偈》以及各种《五台山赞文》涌入敦煌,很快在这个佛教圣地流传开来,到节度使曹元忠统治时期(944年~974年)发展到高峰。除了“新样文殊”在敦煌雕版印行外,值得一提的是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此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尊,并利用整个后壁,绘制了一幅精细的五台山图。这幅图规模空前,总面积45平方米,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整幅壁画。图上山峦起伏,五台并峙。正中一峰最高,榜题“中台之顶”,两侧有“南台之顶”、“东台之顶”等4座高峰。五台山之间遍布大大小小的寺院和佛塔约六七十处,其中包括“大法华之寺”、“大佛光之寺”、“大福圣之寺”、“大建安之寺”、“大清凉之寺”等16所大寺。中台则有雄伟的“万菩萨楼”和“大圣文殊真身殿”。画部下面还画了镇州(今河北正定)、太原城和五台县等城镇。描绘了其间千里江山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诸如朝山、送贡、行脚、商旅、刈草、饮畜、推磨、舂米,乃至桥梁、店房等,形象真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61窟的《五台山图》不仅是一幅形象的历史地图,而且也是一幅精美的山水人物画,图中山高水远,林木扶疏,道路纵横,殿宇耸峙,云霭飘漾,瑞鸟飞鸣。正是这风景优美的佛教圣地,才吸引了无数佛教徒对它的顶礼膜拜,亦成为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见证。
五代以来,像唐前期全国统一时那种以中央写经传送地方的文化传播形式已不可能,随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民俗佛教的发展,五台山文殊信仰也从中原传到敦煌。这不仅为敦煌的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同时它所宣扬的救世护民的思想,也影响着敦煌的社会。
晚唐、五代、北宋初期,中原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五代及宋初,经过敦煌前往印度求法巡礼的高僧,依然不绝于途。敦煌文献S.5981《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智严巡礼圣迹后记》,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途经敦煌,发愿“故往西天求请我佛遗法”。“智严回日,誓愿将此凡身,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北京图书馆《敦煌劫余录续编》0002号《妙法莲花经》第2卷尾朱笔:“西天取经僧继从,乾德二年(964年)六月拜记。”北图收字4号《至道元年(995年)往西天取经僧道猷牒》是寄住于敦煌灵图寺僧人写给当时的归军义节度使曹延禄的。其次,敦煌不断向中原求乞本地已欠损的佛经。敦煌文献P.4962背保存了归义军建立后不久,敦煌佛教教团向中原王朝申请补赐欠损佛经的文稿。s.2140中保存了曹氏归义军初期的《沙州乞经状》。曹延禄时期,又曾向宋朝皇帝求得一部《金字藏》。实际上,敦煌佛教界从中原取回的经典,除了补缺外,还有佛经的注释和偈赞之类的典籍。第三,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带到敦煌。如敦煌文献P.3023中保存的《妙法莲花经赞文》,就是北宋开宝寺和尚继从在开封所撰,在他西行求法路经敦煌时作为礼品献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西行求法的僧人有时还将西域取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如S.3424背保存的《菩萨戒本》,就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中原僧人志坚从西域取回的戒本抄本。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西川(成都)佛教界与敦煌和西域佛教界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当时,四川通西域的道路,也是经过敦煌的。据北图冬号62字背《维摩诘所说经》题记,后周广顺八年(958年),去西天(印度)取经的西川善兴大寺院法主大师法宗,归途中曾在敦煌作短暂停留,将抄写的佛典《维摩诘所说经》献给曹元忠。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不少依据“西川本”抄写的佛经。
由于这一时期敦煌佛教已形成自己独立的特点,而这一时期中原佛教自唐武宗灭佛后其势已衰,佛教典籍的流失在所难免。因此,在晚唐、北宋时,敦煌保存了不少在中原看不到的佛教典籍。张氏归义军时期,张议潮曾向中原王朝进献在敦煌流行的佛教典籍。在曹氏归义军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常把从敦煌搜求佛典作为目的之一,如北宋僧人惠銮因见中原流行的陀罗尼译著拙劣,就曾奉皇帝之命赴敦煌搜求较好的译本,在敦煌三界寺观音院抄写了优于中原译本的《大悲心陀罗尼》和《尊胜陀罗尼》。
晚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佛教既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又影响了西域佛教。佛教自传人敦煌后,一直保持着常盛不衰的势头。人唐以后,敦煌佛教经过吐蕃时期的推波助澜,又躲过了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使敦煌佛教处于河西领导地位。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河西的最高僧官都僧统即住锡沙州,维系着拥有数千僧众的庞大的佛教教团。因此,晚唐、五代以来,敦煌无疑代表了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正由于此,敦煌地区的佛教也对西域产生着影响。今吐鲁番地区,9世纪末,西迁回鹘在这里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并逐渐信仰佛教。10世纪,佛教在西州回鹘地区迅速发展,佛教典籍也被大量译成回鹘文。而西州回鹘所得到的汉文典籍,则主要来自敦煌。在英藏敦煌文献中,有一件因为背面绘有图画而被作为艺术品存放在英国博物馆中的卷子,该卷编号C11.00207,正面写有《乾德四年(966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功德记》,这件文书明确记载了沙州归义军首脑在请人抄写《佛名经》时,特别为西州回鹘抄写了一部,并派人送去,以补西州《大藏经》所欠《佛名经》,说明沙州官府十分了解西州经藏的情况,也透露出西州回鹘有过向沙州乞经的活动。《妙法莲花经玄赞》是唐代法相唯识学权威、玄奘弟子、慈恩大师窥基(632年~682年)的著作。在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写本中,也有一件《法华玄赞》的抄本(ch.1215r),抄写时代为9世纪至10世纪(Periode D),很可能是从敦煌传过去的。汉文本《法华玄赞》西传吐鲁番,对西州回鹘的佛教产生了直接影响。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的回鹘语佛典写本《法华玄赞》,就是根据汉文本《法华玄赞》翻译的。由此可见,五代以来,敦煌佛教对西州回鹘佛教的发展,的确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敦煌佛教在对西域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而以于阗佛教的影响最为典型。9世纪中叶,随着吐蕃在西域统治的衰落,处在吐蕃统治下的于阗,脱离吐蕃羁绊,重又独立,恢复了自汉代以来就在于阗当政的尉迟家族王统。于阗偏处塔里木盆地南沿,虽然已独立于吐蕃,并且早已脱离唐朝的羁縻统治,但其国王仍自称为唐之宗属,积极与中原王朝加紧联系,而处在河西的归义军政权,则成为于阗人心目中中原王朝的代表。从901年于阗使者首次来敦煌,到1006年于阗被黑韩(喀喇汗)王朝灭亡之前,于阗与敦煌的使节往来从未间断。
于阗是西域地区大乘佛教中心,在逗留敦煌的于阗使者中,有不少僧人。由于佛教在于阗被尊为国教,所以来到沙州的于阗太子、宰相和一般人员,也有不少是熟谙佛典的饱学之士。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于阗语佛典,有不少是相当完整的文献,它们大多是这些信士从于阗带来或在沙州写成的。藏经洞出土的于阗文佛典,现主要存放在英、法两国。英藏于阗文佛典现存于英国图书馆所属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其中编号为ch.00274《佛本生赞》、ch.I.00216《金刚乘文献》,就是完成于于阗而由张金山在982年出使沙州时带到敦煌的。另外,ch.002"75《金刚般若经》和ch.xlvi.0015《佛说无量寿宗要经》,也是保存完整的于阗语佛教文献。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于阗语佛典P.4099《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也是写于尉迟输罗王在位时期(966年~976年)。P.3513佛教文献集,内容有《佛名经》、《般若心经疏》、《普贤行愿赞》、《金光明最胜王经·忏悔品》、《从德太子礼忏文》,是于阗国从德太子在敦煌期间写成的。从德太子是于阗王李圣天和曹议金女结婚后所生长子,儿童时期(935年前后)就被带到敦煌,966年奉命入宋朝贡。翌年,其父王晏驾,从德作为合法继承人,回于阗即位为王,即尉迟输罗,年号天尊。上述P.3513佛教文献就是从德太子935年至966年在敦煌写成的。而佛教文献《善财童子譬喻经》的于阗语写本(ch.00266,P.2025+P.4089a,P.2957,P.2896,P.2784,P.5536bis,丽字73号),其完成时间也当在同一时期。10世纪的敦煌,除了长期居留和短期经过的于阗人外,还有不少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人学士能够读懂于阒文,因此,大批于阗文佛典流入沙州,必然会影响到敦煌佛教。
于阗佛教对敦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佛教典籍流入沙州,而且随着于阗和敦煌联系的紧密,五代、宋初以来,大量有关于阗守护神的瑞像图开始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唐、五代、宋初的于阗,关于佛教像法阶段即将过去,末法阶段即将到来的思想在这个佛教国家中广泛流行起来,加上内忧外患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开始企求神灵的护佑,特别是求助于佛典中所记载的于阗守护神们的佑持,这些神灵于是大量以瑞像形式出现。随着敦煌同于阒关系的加强,这些瑞像也传到敦煌,并出现在莫高窟壁画中。敦煌莫高窟瑞像图大多出现于晚唐、五代、宋初,尤以五代宋初曹氏掌权时为多。在瑞像中,释尊等神祗运用神力飞来于阗的瑞像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在这一类瑞像中,牛头山以及与牛头山有关的瑞像占着中心位置。牛头山在今新疆和田县城(伊里奇城)南偏西20余公里处,相传释迦牟尼自印度腾空而来牛头山结跏七日,牛头山遂成于阒佛教圣地。于阗瑞像在敦煌石窟中出现,不仅说明于阗和敦煌有长期紧密的联系,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于阗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对敦煌佛教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位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其佛教才在西域及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开花结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佛教,成为中原汉化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无疑代表着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