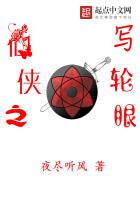中国自上古以来就开始了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互相联系与促进的历程。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与交流的精神形态。从先秦两汉时代的思想对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互动与繁荣,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先秦时代(指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年代,前770—前221)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代”。这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情形,一直为后人瞩目。
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也是文艺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毁灭。因此,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特点。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术语,表示公元前500年前后,或泛言之,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特征。那是宗教和超凡人物突现的时代,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佛陀,中国的孔孟老庄,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以赛亚和以西结的时代,是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及希腊三杰)的时代。卡尔·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开创性研讨,见《历史的源起和目的》(伦敦,RoutledgeandKeganPaul,1953,译自1949年德文版),特别是第1和第5部分。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百家争鸣如果没有思想对话的展开,就会导致秦朝焚书坑儒的悲剧出现。要想避免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则自由的思想对话是前提。从先秦到两汉时代,这里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曾出现,成为令后人感思的历史现象。
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深沉反省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这一点在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中可谓针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是分歧与争议颇大。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儒家的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的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制度;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提出用法术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和政治文化相关系,所以,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乃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奠定了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互相补充又互相对立的格局,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
§§§第一节孔子与文艺对话
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对中国古代文艺对话的思想智慧与语录体影响甚深,其门人记录下来的《论语》直接开启了以语录体来教育学生、从事思想阐释与建树的先河。《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关于文艺的对话,堪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文艺对话录相媲美,从中可以见出中西文艺观念的不同与各自风采。
一、《论语》中所见孔门师生对话之特点
孔子将仁学与礼乐文明结合起来,用诗书礼乐教化学生,培育人格。孔子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仁学与礼乐思想。他从精神文化的高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批评方法。《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具体解释道:
梁皇侃撰《论语通》曰:《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夫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或负扆御众,服龙衮于庙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缝掖于黉校之中。但圣师孔子,苻应颓周,生鲁长宋,游历诸国,以鲁哀公十一年冬,从卫反鲁,删诗定礼于洙泗之间,门徒三千人,达者七十有二。
但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则朽没之期亦等。故叹发吾衰悲,因逝水托梦两楹,寄歌颓坏。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后,过隙叵驻。门人痛大山长毁,哀梁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
从孔颖达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为了传承其思想事迹而编成的一部书。值得关注的是,孔颖达用了三国时魏国玄学家王弼关于圣人有情而不累于情的观点,说明孔子是一位深于情者,平时应对不同弟子,随机而教。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又分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郑注《周礼》云:‘发端曰言,答述为语。’今按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论语》这种体裁。所谓“论难答述”,就是指的这种思想对话的特点。
《论语》所以采用对话体,与孔子的仁教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论语·先进》载孔门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言语一科牵涉到思想对话与修辞艺术方面,刘宋时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的前四个门类就是这四科,而且其中言语门100条记录尤其体现魏晋对话精神与风采艺术。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孔门弟子的四科情况也作了详细记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对此作了具体解释:“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钱穆:《国史新论》,2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可见言语与道义之学的结合是孔门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述而》中又补充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集解曰:“四者有形质可举以教。”从现有的《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等资料来看,孔子以文章、行为、忠、信这四项内容与四科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
从人物性格来说,孔子与学生相处,一向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激发道德思想的火花。这种从当下性生发出来的思想品格,本身就具有感性特点和审美价值,而且孔子与学生对话中产生出来的隽言妙语,极具文学性,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的诗话体。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卷一《孔子的智慧》,1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林语堂为此在20个世纪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林语堂认为孔子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话语所以“妙不可言”,往往在于其即兴而言,这本是审美体验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文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古希腊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对话有所不同。前者重在理性的彰显,而后者则重在知性的感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孔子思想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什么体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的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与理论观念。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而黑格尔自己大约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的二百多年后,他的故乡德国也兴起了一股反对唯理论、倡导现象学与当下性的思潮,影响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东方孔子式的语录体语境中。
先秦诸子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的看法上面。而礼乐涵括了道德与文艺的内容,因此先秦儒家思想是从礼乐角度去体认道德与文艺问题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孔子本人十分重视文艺的对话与沟通作用,这是由农业文明与继之而起的宗法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血缘宗法作为纽带的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时候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进行。学问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切磋,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念很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萌发了。而诗歌与音乐在当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承担了人际关系的交流。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源自个体与社会的沟通,是祛除个体孤独的重要渠道。(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4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这一思想与孔老夫子的诗学倒是颇为相合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据后人解释,也就是“群居而切磋”,即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的意思。(《论语正义》引孔安国说:“群居而切磋”,即相互启发,互相砥砺。朱熹则在《四书章句集注》里解释为“和而不流”。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将“群”解释为“作为一种社交造诣的文雅的说话方式”。)可见对话能够拓展人的思想境界。古代中国人对于诗乐舞的功能与作用,是从农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中去体认的,强调在诗乐之中通过思想交流,促进对话,和合人际关系。这不同于西方的人际关系中的理性思维、人际对话,往往在于其不经意间产生诗兴和随意性,后世诗话与词话中的随笔也大体如此。“诗可以兴”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实际上,诗的“兴”、“观”、“怨”,都是在“群”的基础之上得到认同的,而不是游离于此而展开的。此一点要特别强调。明末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提出: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怨,怨亦不亡;以其怨而群,群乃愈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