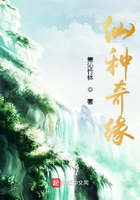文中通过孔子学生阳子与弟子的对话,阐明了自美者不美的道理,极言审美判断的相对性,对方以为美而自己并不以为美。康德曾说美是主观的合目的性,而庄子则将目的论设定为更无规定性的大道,矗立在具体之上。从美的形态之中,庄子弘扬了那种汪洋恣肆的大美。这是一种与自大无知相对立的美。在《庄子·秋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
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
文中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彰显了两种思想天地,一种是局于一隅,一种是至人神至。河伯代表了天下曲士的共同心态,仄陋而自得,不识天地之大,于是才望洋兴叹。而北海若则通过河与海的比较,教训他要悟出天地之大与大道之要:“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北海若向河伯宣明,天外有天,河外有海,推而言之,人在天地之间又何等渺小,四海之在天地之间又何等渺小,从而说明了自己心仪的大美是无限之美。这种思想通过对话,形象而生动地表达出来,比起抽象地说起大美要好得多。
《庄子·秋水》中还有一段对话,是著名的庄子与惠施辩游鱼之乐的,其中谈到庄子与惠施辩论的要害是人能否知鱼之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认为自己可以知鱼之乐,而惠施则强调庄子不是鱼,怎么能够知道鱼之乐呢。争论的关键在于人有没有可能进入到物化之境中。在庄子看来,只要物化其境,如庄周梦蝶一般,就能够与对象合为一体,自然也就知鱼之乐了。在道的境地之中,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同体,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这段对话将对象与自我的复杂关系,论述得趣味横生。强调人可以通过设身处地而知晓对象,对于中国古代的鉴赏论影响甚大。刘勰《文心雕龙》的《知音》强调知音与体验,钟嵘的《诗品》赞赏体验式批评,多受其影响。清代文士刘风苞《南华雪心编》总论《秋水》时说:“尤妙在濠梁观鱼一段,从寓意中见出一片真境,绝顶文心,原只在寻常物理上体会得来。末二句更为透彻圆通,面面俱到。内篇庄化为蝶,蝶化为庄,可以悟《齐物》之旨;外篇子亦知我,我亦知鱼,可以得‘反真’之义。无法属上乘慧业,不能有二之文。”可以说揭示了对话中的奥妙所在。
《庄子》中的文艺批评与审美道理,仅靠玄思很难解释清楚。这一点老庄有着明显的不同,老子依靠哲学思辨与世人对话,而庄子则喜欢通过形象化的寓言来阐述。这种文体在《庄子》中是不少的,比如《庄子·天道》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的时代是一个看重有形与物质的时代,世人唯知追逐物欲,迷而不知所归,于是老子与庄子这些坚守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便十分地失望。而儒家的思想方法也是重视书本却忽略书本中的意蕴,从而导致了迷信书本的倾向。庄子提出,那些书本不过是记载道理意蕴的工具罢了,而且真正的精神意蕴是不可言说的,是只能领会的。但是此中的玄奥与体会,只靠思辨与泛泛而论是不能说清楚的。因此,庄子巧妙地借着寓言对话体加以阐释。试看下面有名的轮扁凿轮的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庄子之论言意关系,透过这段生动的对话说明得很清楚。工匠轮扁向齐桓公说明,自己凿轮最后的成功与否,特别是轮中之轴心的小大是否合适,在于多年的心得与体会,“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以此证明圣人之真谛也是不可言传的。言意之辨本是一个十分难懂与说清楚的道理,但是庄子却很善于通过工匠创作的事情来加以说明,真是举重若轻。言意之辨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与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与问题,得到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应验与论述,对意境与境界等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此中的玄奥则是在庄子的这段工匠与国君的对话中得到说明的。耐人寻味的是,工匠轮扁的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奥妙,且后世艺术创作的许多道理以此为例。《庄子》中的许多类似的寓言对话,往往是将玄奥的哲理通过一些工匠的创作道理加以说明,比如著名的庖丁解牛、工旋而盖规矩、梓庆削木为、匠石运斤成风等等,本是为了说明一定的哲理,并不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去切入的,但是无意之中却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甘苦,因而又成为艺术创作的哲学与美学的说明。迄今为止,庄子这段论述言意之辨与寓言可以分开说明言意关系的对话,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艺批评与美学中成为重要的话题与范畴。(到了魏晋时代,言意之辨成为玄学的主要论题之一。除欧阳建倡“言尽意”论外,荀粲、王弼等人都主“言不尽意”论或“得意忘言”论,继续发挥庄子的观点。如王弼《周易例略·明象》中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发展得意忘言,用庄子思想来解释《周易·系辞》关于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陆机《文赋》:“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这种观点后来为刘勰所总结。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意在言外”,“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佚文)。)
《庄子》一书,往往还通过对话,将艺术的至境加以演绎。在《庄子·天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这里说的是北成门听到黄帝在洞庭之野奏咸池天乐时的感受,先是听后感到惧,再是感到怠,最后进入惑的感觉。他因是问黄帝自己缘何而得此感受。黄帝向他解释这三种审美感觉的关键在于心境与天地的相合。因为相合的阶段与境界不同,所以感觉也不同: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女故惧也。”
黄帝向北成门解释道,真正的天乐应是调和阴阳,先应之于人事,再顺之以天理,行之于五德,应之于自然。也就是从人籁进入天籁。而刚开始的音乐则没有达到天人相合的境地,对象与主体不合,所以使人产生了畏惧的感觉。康德说过,崇高感主要是对象与主体不合,使主体形成了畏惧而第二种乐境虽然使人感受到对象的磅礴与自然的魅力,但是人还没有进入其中,主体还无法解读对象,于是乎感受到“怠”即似解非解的境致: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只有到了第三种境地,主体与对象开始融化一体,道与人、物与我开始宛转关切,新的审美境界才产生了: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这是说到了咸池之乐的最高境界时,北成门这样的凡人开始感到困惑,而这时候正是音乐的境界形成之时。由惑到愚,由愚到道,这正是审美境界的提升。这段对话体文字,层层深入。魏晋时嵇康《声无哀乐论》中采用的也是对话体,从而使复杂的音乐美学问题能够层层展开,让人们了解此中音乐境界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