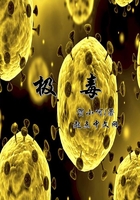锦瑟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一首令人沉醉的诗,它飘忽不定的忧伤中,却有着极为深沉的感动。可是,在诗人“惘然”叹息的背后,到底掩藏了什么秘密呢?诗人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这又是一首使人倍感失落的诗。古往今来,多少人在它的字里行间、诗里诗外,进行着艰难的追寻,但除了那股浓浓的忧伤和朦胧的感动外,我们仍然什么都不知道。也许,那些飘忽不定、了无着落的虚幻,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如果确是如此的话,我今天所写下的文字,只能又是一个“惘然”。
前人殚精竭虑的研究,大多数是着眼于诗歌的事实部分,虽然未必确凿,但从诗歌理解的角度而言,它们都是一条条试图接近诗歌的小径,通与不通,都负载了研究者对这首诗的领悟,因此也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将前人的观点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是寄托说。张采田云:
“庄生晓梦”,状时局之变迁;“望帝春心”,叹文章之空托……“沧海”、“蓝田”二句,则谓卫公毅魄,久已与珠海同枯;令狐相业,方且如玉田不老。卫公贬珠崖而卒,而令狐秉钧赫赫,用“蓝田”喻之,即“节彼南山”意也……可望而不可前,非令狐不足当之,借喻显然。(《玉溪生年谱会笺》)说这首诗是感于牛李党争时局而作。其中的卫公指李德裕,李党首领,曾被李商隐称为“万古之良相”;而令狐即令狐绹,是牛党的重要成员,曾提携李商隐,又因不满李商隐另投李党而颇有怨意。这个解释,体谅的是李商隐夹在牛李党争中的尴尬处境,并认为正是那些无法摆脱的是是非非的纠缠,使得李商隐产生了虚幻的感觉。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又过于实在了,事实和诗歌的联系有些牵强,而且诗中明说为“追忆”,则不可能是因感于“时局”而作。
第二种是悼亡说。朱彝尊曰:
此悼亡诗也。意亡者善弹此,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五十弦矣,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思华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殁也。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葬之也,犹言埋香瘗玉也。此情岂待今日追忆乎?只是当时生存之日,已常忧其至此而预为之惘然,意其人必婉弱多病,故云然也。(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引)这个说法以断弦暗喻亡故,诗中所抒发者乃是对某个情人或一段情感经历的追忆。我们的确能从诗中感受到那种散不尽的哀伤之情。李商隐妻子早逝,漂泊江湖中,又有过多次没有结局的情感经历,并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说诗歌表达了对某人的悼亡之情,亦有可能。但此“二十五而殁”者为谁?李商隐《无题》诗中往往隐去感情相关者的姓字,或以朦胧意象写其思念之情,但像这样连人之有无、死亡之事实一并隐去者,可谓绝无仅有。因此,悼亡一说,并无根据。
第三种是自伤说。何焯云:
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庄生”句言付之梦寐,“望帝”句言待之来世,“沧海”、“蓝田”言埋而不得自见,“月明”、“日暖”则清时而独为不遇之人,尤可悲也。”(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引)认为诗歌咏叹了自己的怀才不遇。李商隐少时即因才高而为世所瞩目,壮时诗文皆精,却蹭蹬官场,长期逐幕。所以,内心怫郁的愁闷之情,可想而知。这一说法以“沧海”、“蓝田”句为内美未见赏识,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以“月明”、“日暖”句喻世道清明,就属牵强了。而且,怀才不遇古者多有,所抒发者往往悲愤交加,不似本诗只是忧伤,而且也难以和“此情”两字贴合。所以,这一说法也难坐实。
其实,关于《锦瑟》诗本事的解读,还远不止以上这些。差不多所有文人的艰难处境,都曾被用来解释这首诗,却无一被证实。那么,这首无蛛丝马迹可寻的诗歌,要么就包括了所有文人的悲伤境遇,要么就什么事实也没有,这可能吗?这不可能,李商隐虽然说“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毕竟有个“当时”存在,特定的时间里一定有特定的事件。但是这句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李商隐主动否定了“当时”和此刻在事件上的关联,就只让那种起于过去的忧伤而朦胧的情绪,作为一种“曾有过的情境”再现在生命里,并一直在生命里延续着。那么,我们也就不必非得追寻“当时”的故事,最妥当的做法,就是让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认领这个优美而伤感的情境吧。如此说来,对这首诗的解读不但是一件多余的事,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所能做的不过是沿着“自伤说”的路子,尽量虚化其实,强作解人而已。
“锦瑟无端五十弦”,通常的瑟只是二十五弦,而此说五十,其典出《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朱彝尊从这个关于音乐的传说中看到了“破”字,并从断弦推出亡故之意。但就典故本身而论,则“五十弦”之不同于二十五弦者,在其“悲”。就诗歌本身而论,“五十弦”与“思华年”相呼应,只能是指所咏者的年龄。“一弦一柱”,逐年逐岁地回味平生,大约也只有到了五十岁左右才比较合适。显然,这两句诗说的就是人到五十,检点平生,唯有悲伤。所谓“无端”即是难以把握缘由、无所依凭、难以理解,它可能只是就典故而论,素女何以如此悲伤,难以知晓;也可以就“思华年”而论,指人生如梭,忽焉已是五十,却踪迹全无。也就是说,这一句最平实的解释,就是指检点人生,半生如梦,生平事无所列举,唯有深深的悲伤,萦绕心间。
蝴蝶之梦,见于《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当庄周梦为蝴蝶的时候,翩翩然而飞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庄周。庄子的意思是人不必为飘忽无定的身份所限制,应该安于当下的处境,才能体会到安逸。而李商隐则从梦蝶者不知为庄周一事中,感受到了人生不定、自我难觅的迷惑,表达的是人生无常的悲哀。“望帝”句,古有男子名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后失位于奸臣,“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太平寰宇记》),“至春则啼,闻者凄恻”(《蜀志》)。李商隐不可能感受到失位之痛,他所钟情的,是那只总是在春光中泣血悲啼的鸟。那无处不在的啼叫声中,寄托了一个生命的全部哀怨,这其中也能透露出清点平生的况味。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写景如画,前者色调幽冷而清晰,后者色调温和而朦胧,且每句内部自成对比。大海无垠,月光如泻,天地之间一片明澈而又如此宁静。珠乃大海之宝,晶莹剔透。古人以为月盈则珠圆,月亏则珠缺,所以诗人将月与珠相并而提。张华《博物志》云:“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则集天水之灵的珍珠,乃凝结了鲛人之悲伤而成。鲛人何以流泪,古籍无载。但李商隐将其置于沧海月明的背景下,则苍茫之中的孤独之感,是如此地骇人心目。这不是失侣无朋的孤独,这是微小而渺茫的生命之于无边的天地的大孤独,是生命被遗弃的大悲哀。古人以为玉有灵气,蕴埋着宝玉的蓝田,在晴暖的日光下,当有轻烟缕缕,上接于天。唐人司空图《与极浦书》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令李商隐着迷的正是这可望而不可及的迷离。这份迷离中有着无限的牵挂,那是来自玉的温润的诱惑;又有着无从把握的悲哀,那是来自烟的渺茫的慨叹。就是在这恍恍惚惚之中,诗人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又有什么是虚幻的。这种“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七月二十八日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的感受,像梦寐一样常常纠缠着李商隐,使他难以摆脱,也使他在反复的体悟中沉迷不止。李商隐是迷上了这份迷离。
以上四句,是李商隐一生的感受:庄生梦蝶般的恍惚,杜鹃啼血般的哀婉,明月珠泪般的孤寂,暖玉生烟般的迷离。所有的意象都是那么迷茫忧伤,都有着无限的惆怅忧郁,它是诗人对自己平生的真切感受,是一种情绪上的体验。它们前后呼应。庄生梦蝶和玉暖生烟都是说人生迷离,前者关于生命自身,后者则关于人生中的种种境遇;望帝啼春和月下珠泪都是说人生悲凉,前者凄厉而后者寂寥,结构精妙而意境参差,有着无限的意味。“此情可待成追忆”之“情”,即是指这些缠绕在一起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是何以产生的,又有哪些具体的家国情事让他不能忘怀呢?“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在朦胧之中,什么都不记得了。也许是不愿意回忆吧,那些无从把握的纷纭事实,已经无法追究它是为何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了。它们是构成人生悲凉的内在原因吗?还只是悲凉人生的外在体现呢?一个回首平生的年老的诗人,已经开始明白了生命的真正内涵,他所体会到的就只是巨大的迷离和无限的孤独,他已经知道所有那些经历过的事,它们如此存在的理由只是由于命运,它们无论如何存在,结果也只是一场空虚。
这首诗充满了朦胧幽怨的情调,但这又确实是一首无比优美的诗。那些忧伤本身是迷人的,不但充满了情感和智慧的魅力,而且醇厚、浓郁,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命最为自然、最为本真的吟唱,它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悠然回响。诗中的所有意象都是优美的,它们是如此的精致而巧妙:轻灵的蝴蝶,悲鸣的杜鹃,碧海上晶莹的月,晴空下袅袅的烟,它们显得如此和谐而又错落有致。没有用心沉湎过的人是无法营造出这样的景致的,它显示了诗人对生命,即使是空虚的生命,也饱含着深情的留恋。由于这首诗表达的只是一种深沉的情绪,也就难以被传统的解诗方法所把握,后人感慨曰“一篇锦瑟解人难”(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但我们仍然要向前人的努力表示敬意和感激,因为他们的解释,增加了这首诗意蕴的厚度,使得这首诗更加迷离,也就更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