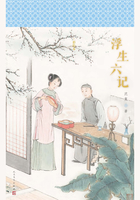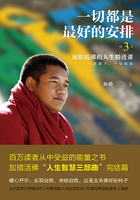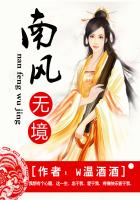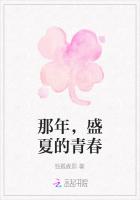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做临时工,但我在下班后,还是常去圆明园路《文汇报》新闻部看望张冠华,打听消息。
我在那里认识了王复初、姚柏生、洪作鹏等记者和编辑,他们告诉我,总编马达看到我写的来信很重视,他说一定帮忙登出来。
张冠华老师中午请我吃饭。
不久,张冠华老师给我看他写的《调查附记》的清样,打算登在“法庭内外”。
调查附记:
收到来信后,记者专程访问了孔祥骅及有关部门的同志。经了解,信中反映的情况属实。
孔祥骅同志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在痛苦而漫长的“监督改造”过程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阻力,阅读了大量革命导师的著作和《中国通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纲鉴易知录》《史纲评要》《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文钞》等大量书籍。为了学习《左传》,他还向当时处境困难的复旦大学老教授朱东润求教,并建立了通信关系。他坚信人们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们祖国是多么需要知识。粉碎“四人帮”后,他曾戴着“反革命”帽子,两次报考过研究生,虽未被录取,但更坚定了自学成才的信心。
平反之后,孔祥骅怀着为国效力的迫切心情,希望早日分配工作,好好干一番,以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四化建设服务。然而,他奔波了九个多月,至今工作和生活问题仍未得到落实。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曾亲笔写信推荐他到古籍出版社寻找工作,但由于人事制度的限制,难以解决,他仅为该社印刷厂校对了两本集子,共获得三十六元报酬。目前,他仍然只能依靠母亲的退休工资艰难地维持生活。
据了解,有关劳动部门为解决孔祥骅的工作安排问题,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市劳动局的有关干部为此专门到古籍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去联系,请他们为孔祥骅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或经过考试后录用。但两个单位的人事部门都说:目前人员超编,无法再接收。市劳动局只好请南市区劳动局安排。南市区劳动局一时又难以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因此,目前只能安排孔祥骅参加临时劳动,但根据孔的具体情况,他又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因而,南市区劳动部门也感到十分为难。
孔祥骅同志因错案获得平反,而又有一定业务能力,有关部门应该切实帮助他得到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的机会。
张冠华老师是《文汇报》新闻部主任,他本来准备在3月份发表,但是还要先将清样寄给市委书记胡立教,我坐在张冠华老师的桌子旁,对他说:“我是度日如年。”
他劝我:“如果不能发表,争取个别解决,你就耐心等待吧!”
5月初,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流通部接到张冠华老师的一封信,他说:“孔祥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你到高安路去,市人事局领导同志要亲自和你见面,谈话。”
下班后,我就赶回母亲住处,把市人事局领导要见我的消息告诉她,母亲说:“你要把胡子刮刮干净,把头发剃一剃,要穿整齐些,给人以干部形象,态度要大方、稳重。这样有利于安排工作。”
这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穿了一套蓝色的中山装,脚穿黑皮鞋,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了高安路,时间还早,我在马路上慢慢地走着,到了指定地点,看见有人在门口站岗,我乘电梯到三楼局长办公室,只见一位中等个子,皮肤呈青铜色,很有军人气派的老同志正与人说话。
他见我就问:“你找谁?”我讲述了《文汇报》记者通知我来的事。
他说:“你就是孔祥骅吧,你先等一等……”
过了一会,他与人讲完话,拨了个电话,同时对我说:“你先坐!”
我坐在沙发上,一会儿,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一进来就称那位颇为英武的老年人:“顾局长!”
他就是市人事局的顾副局长,还有一位年轻秃发的是干部调配处的杨处长,由他作记录,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谈了出来。顾局长温和地说:“孔祥骅同志,你吃了许多苦,我们对你是有责任的,你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出来,市委领导已经对你的问题作了批示,而且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杨处长拿出胡立教的批示,《文汇报》稿子的校样、报告、信,都在他那儿,他说:“我们考虑给你一个编制,一个名额,你想干什么事情?”
我说:“目前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当临时工,现在走投无路没饭吃,我只要有个饭碗就可以了。”
局长说:“我们不仅要解决你的吃饭问题,我们希望你平反以后为四化作出贡献,发挥自己的才能,你想去上海辞书出版社还是去古籍出版社呢?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杨处长讲:“古籍出版社我们已去联系过,那里的编制已满了。”我说:“在你们没找我以前,华东师大图书馆已决定给我打报告,要求争取一个编制,但转正报告学校里还没有报上来。”
我希望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因为华东师大图书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首先要我,再说,在大学工作与我的志向、兴趣吻合,也是我母亲的心愿。
杨处长说:“我们可以联系,如果华东师大要你,那么你就在华东师大,如不要你,我们再联系其他单位。” 局长说:“你有什么事,可随时来找我,我们会在很短时间里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一定给你安排工作,让你在后半生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临走时,我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