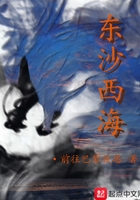1979年7月1日,农场里开大会,宣布摘掉一大批人的反革命帽子,我也在其中,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但就是摘不掉这顶帽子,现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全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四类分子、专政对象都摘帽了,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也一下子被三中全会的落帽风吹掉了。
8月份,印着复旦大学红字的通知单来了,拿着这张通知单我手发抖了,我以为是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
孔祥骅同志,根据我校招收研究生的要求,你未被录取,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转给第二志愿的其他学校,这次你能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刻苦地复习功课,愉快地接受祖国的挑选,这种精神是好的,希望你今后在工作,学习岗位上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学好本领,搞好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下面一看分数,《中国古代史》80分,《中国文学史》76分,《政治理论》60分,《文艺理论》61分,《古文阅读》69分,《俄文》不及格。
我一下子瘫倒,受到一次很沉重的打击,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讲,躺在床上半天,想到最后我一下子爬起来,我想古文绝对不会只有69分,是不是搞错了。
夜晚,瓢泼大雨,我冒着雨赶到分场,浑身淋得象只落汤鸡,我对分场管教干部说,我的成绩单下来了,我感到分数不对,要求到上海去查分数。
他们说不会错,要我相信学校,因为农忙,他们不批准我去上海。
为了查分数我准备豁出去了,那天晚上我逃跑了,我在农场那么多年,在最苦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人逃跑,我没动心,每次探亲按时回来,这次我不得不逃跑了。
半夜里我拿着一张分数单,两件衣服,摸着黑从郎溪出来,一路漆黑,天亮到社渚,再到溧阳,下午五点从无锡上车,晚上九点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本想去复旦大学查分数,结果有位朋友劝我不必这样做。
我又去了朱东润先生那里,他一见到我说:“这次复旦没给你一个位置,实在是因为名额有限,加上你外语成绩较低。”
他安慰我:“你不要对复旦大学太迷信,真正的学问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心里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农场看我成绩考得不错,把我借到分场小学当代课教师,我终于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可以埋头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