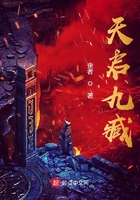这一天已是十一月十四,精精儿走了不过两个时辰,山下探子便来报,五湖四海的各大匪帮已陆续到达空桑镇上,将如约明日午时前来拜山会盟。可等到了酉时,空空儿仍是未得着任何景公子与梼兀师徒的消息,反到不见了兕的踪影。他发出这会盟之邀,不得不身在明处,而强敌却暗中窥伺,虽已在山上布下各种厉害的机关陷阱严阵以待,可心中对明日的成败却毫无把握,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也只得走一步是一步。而天浩几人则是养精蓄锐,坐等着看这恶虎相争的好戏。当夜,明月高悬,各人的心中都是忐忑不安,静观待变。子夜时分,山下入口跌跌撞撞来了个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主儿,守门的寨主上前一瞧,乃是空空儿随身带来的亲信,上月被遣去递送会盟请柬,今日回来竟已成了这般模样,喽啰们不敢怠慢,忙将其送去议事厅急报。此人见了空空儿,勉力凑在其耳边嘀咕些什么,他伤势过重,说了只言片语便晕了过去。空空听其所言,大惊失色,忙吩咐耿大彪召集了全山大小头目。众山匪见这向来盛气凌人的小子此时神色间竟也有些慌乱,到是颇感以外。短短片刻,他下了两道严令,一是全山上下严加戒备,未得其号令,不得放入半个闲杂人等。
二是抽调十名最精壮的寨主,立时前往山下大冢之坡接应。安排已毕便匆忙起身,甩下那接应的十人先行而去。天浩三人自是混在了厅外喽啰中探知了一切,商议片刻,萧绰执意要先从那报信的亲信的口中问出详情。天浩雪静皆是不解道:“事有缓急,为何不追踪空空儿而去?”萧绰道:“传闻空空儿与精精儿兄弟连心,今日看来哥哥的情意果真不假。这厮平日里稳如泰山,现如此慌张,定是得知精精儿有了危险。昨日他们离别之时你可曾听见他所言,若其全力奔赴他那宝贝弟弟设下的圈套,又怎是我等能追上的。你二人也不必担心,此事多半乃景公子之计,而非我哥哥和你大师兄所为。我们又何必急着凑这热闹,不如先将来龙去脉都打探清楚了,也好有备无患。”雪静听她说的在理,只是有一点尚且不明,问道:“那报信的已奄奄一息,姐姐又怎有把握让其开口?”萧绰自信满满道:“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姐姐自有法子让他乖乖交代。”三人商议已定,便悄悄前往报信人所在的客房。可到了窗前,却见烛影中血光闪烁。天浩忙点破窗棂纸往里偷窥。地上已倒了三具尸体,都是被安排留在此处照料喽啰。再看那重伤的报信人,竟变成了个娇小的女子,正手持长剑擦拭血迹。
萧绰见了此情景也是大出所料。三人索性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这诈伤的女子将尸体堆于床下,脱去自己原先满是血迹外衣,背后竟露出条两寸来长的尾巴来。天浩雪静见了都是啧啧称奇。也不知其从哪里找出了套与空空儿一摸一样白色袍子,穿上后便即起身,出门之时再瞧她面貌气色,却是活脱脱又一个空空儿。待其走远,萧绰叹道:“不想景公子竟能找得封狐一族前来相助。”天浩雪静皆是奇道:“这又是何方神圣?”萧绰道:“此说来话长。”原来千年之前封狐一族乃是魔界显贵,其族长九尾狐狸更是号称万妖之主,位列魔界四王之一,便有如今日三巨头一般。不过后来混世魔王现世,据传九尾狐为其所杀,族中显赫人物也被屠殆尽,从此一蹶不振,只留下极少数残余隐匿深山不出,难觅其消息。窫窳也曾数次寻访,想收为己所用,可却是求而不得。雪静听完,好奇道:“原是个狐狸精,莫非是个厉害角色?我瞧她变换容颜得本事可不输于姐姐你呀。”萧绰一笑道:“大劫之后未曾听闻封狐一族再有过杰出人物,多厉害到是不见得。但妹妹你所言不错,狐妖与生俱来就有变人的本事,这可是连三巨头都望尘莫及的。
姐姐的易容术不过只能找些材料在人脸上修修补补,对身形气质却毫无办法,又怎能与其相提并论。据传只要是她们瞧过的人都可记在心里,变化之后高矮胖瘦,言谈举止与原主儿绝无半分差别,刚才那娇小的妖女既是扮成我那高大的哥哥,只怕姐姐一时也难辨真假。此外更有传言这一族还有种厉害的法术,若是他们吃了对手的心肝,便可拥有其全部的神识与技艺。不过万幸你我打巧得知了这狐妖的底细,也好早作防备。”天浩道:“那此时还不宜打草惊蛇,且看其下步干些什么,你我再做决断。”三人远远跟着狐妖,见其大摇大摆走入了议事厅,要耿大彪召集了众寨主再次议事,山贼心中不满空空儿,那选出的十人此时正磨磨蹭蹭要待启程,却见这狂妄的小子不知为何竟又回来了,心中也是惶惶,怕其怪罪。假空空儿厅中正襟危坐,待匪首们到齐,大声宣布道:“大敌已去,今夜不必再遣人下山,明日事务繁多,且将各关口的兄弟全撤回来,都好好歇息吧。”言语神色,气质谈吐果真与正主儿分毫不差。众匪听了此言都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无人敢质询其权威,见是他下令休息,即便将来出事也错不在己,自是乐得享这个清闲。
假空空儿吩咐完毕,也不理山贼们是何反应,径直出了大厅,一个人去了。早在殿外守候的三人自是远远尾随。这狐妖虽走的甚急,但轻功平平,天浩萧绰自是不费吹灰之力便跟上了,雪静大半年来刻苦修炼踏空望月之术,她天资聪颖,此时已有小成,也轻易追上了。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已近大冢之坡,远远来了数个黑衣人上前接应。妖狐似颇是关切地问道:“如何了?”为首的答道:“这大鱼狡猾的狠,公子爷耗了大半个时辰,他却仍不入瓮,还是要辛苦姐姐了。”说罢边上几个喽啰推来辆黑漆漆的囚车,狐妖换上件精精儿所穿的黄色大袄,又在身上泼了些鲜血,便钻入囚车,由黑衣人推往大冢之丘。萧绰躲在近处桑林中看的明白,那为首的姓徐,原是北海群盗的二当家,素有取代萧尽忠的野心,看来是依靠着景公子如愿以偿了,如此推断这伙海盗已精锐尽出,要靠着新主子来抢鬼盗盟主之位了。又行了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古桑密林中忽出现一片难得一见的开阔坡地。一黑衣公子伫立中央,而一白衣人则在边缘游走,正是商臣与空空儿。这二人互知底细,一强一快,谁都不能轻易制住对手,因而虽已耗了大半个时辰,未有把握之前都不愿贸然动手。
此时为首的黑衣人高声道:“启禀公子,人已押到。”就见月下景公子身影徒然伸长,到那坡地边缘卷住了囚车拖了过去。而狐妖则装腔大喊道:“哥哥救我,哥哥救我。”空空儿微微一愣,知已是事不迟疑,忽身形一晃,化作一道白光射向那囚笼。天浩躲在密林中瞧的明白,此人昨日并非信口开河,如此神速便是恩师南仙翁也远远不及,恐只有风狸那畜生方才能胜过,心中也是好生佩服。白光撞上囚车,只听咣当一声响,定睛在看,空空儿站在笼旁,手中长剑已断,原来这笼子乃是金钢所造,可比普通的刀剑坚硬多了。景公子飞身赶去,那原先拉着囚车的黑影则迅速化为利剑排山倒海搬的猛刺猛砍。白光闪闪,影剑阵却是连对手衣袖都不曾沾着半分。忽听一声巨响,空空儿断剑顶端青芒一闪,这金钢囚笼被一斩为二,剑气在大地之上劈开一条数十丈长的口子,好不厉害。他原以为已然得逞,但不想车底之下忽漫天飞出无数飞镖铁刺,饶是其身法卓绝,方才不曾被打中。待避过暗器,忙拉住笼中人之手便要逃走,可哪知这精精儿竟是一把拽住了他,却不动身。此一来可露了陷,狐妖虽外貌言语上扮的分毫不差,武功法术却是做不得假的。
这对孪生子从小同吃同住,同修一门法术,哥哥对弟弟的功夫再是了解不过,可这眼前之人拉自己的这一手无论招式还是内力,哪有半分九婴家功夫的影子。他顿时惊觉,又回想起先前手下报信之时,就疑其所受之伤似假,但因此人乃自己极信赖的心腹,又事关亲生弟弟,情况紧急,方才不曾细察,此时看来却是中了圈套。空空儿大怒,目露凶光吼道:“奸贼安敢诳我。”挣脱其手,抬掌便要致她于死地。但只这微微一耽搁,景公子已到了跟前,身后一阵厉风袭来,空空儿心知不好,只得收招躲避。再定睛一看,周遭黑影已画下一个大圈,将自己困在中央。景公子站在一丈开外也不急于强攻。而那假精精儿则一步步悠悠的躲出了圈外,用满是娇媚的女声呵呵调戏道:“哥哥你好绝情,怎舍得对亲弟弟下毒手?”景公子得意道:“空空儿,本座念你也是难得的才俊,现给你条生路,只要交出蛟鳞令符,今后效忠于我,便饶你不死,还保你将来荣华富贵。”空空儿心下恼怒,却也临危不惧,冷冷道:“别高兴的太早,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要令符,给你便是。”说罢取出一小琐片,在月下发出冷冷蓝光,朝着假精精儿掷了过去。
狐妖见这琐片飞射而来,可不敢托大,忙往边上闪避,那徐姓的海盗头子正在她身旁,知鬼盗令符极为重要,这正是主子面前一展身手的大好机会,怎愿放过,忙身形一晃,一招探云手干净利落,将其接住。只是此物来速太急,手掌上还是被微微划开了条小口子,正得意之时,忽见空空儿飞身而来,虽离的还远,却也有些慌乱,忙抽钢刀护身。景公子怎容入了网的鱼儿逃脱,空空儿刚一触着影圈,地上便立时化出无数黑色利剑斩在其双腿之上,可怎想他只是微微一顿,却丝毫不为所伤,反听那手持蛟鳞令符的海盗头子声声惨叫,定睛再一看其双腿竟已成肉酱。景公子知自己中计,急忙追空空儿而去,可怎又能赶上他。海盗头子瘫坐在地,见一道白光已至身前,忙挺钢刀刺了过去,空空儿避也不避,正中腰间。海盗头子刚要得意,却觉腹部剧痛,低头一看血如泉涌。他身边的手下何曾见过这般古怪之事,明明大哥刺中敌人,伤的却是自己,一时都吓呆了,只那狐妖在空空儿奔来之时便晓得不妙,早已远远逃开。天浩雪静隐在远处密林中瞧的明白,对此突如其来的怪事都诧异不已。
萧绰却知这乃是九婴的一种极厉害的密术,名“李代桃僵”,中了此术之人不知不觉便成了蛊主的傀儡,若不解咒,将以身代伤,至死方休。空空儿习得了这奥秘的法术,危急之时将咒语施在令符之上掷了出去,刚好有个蠢材不知好歹接下了,就此中咒。既有了替死鬼,他便毫无顾忌的直闯影圈法阵。景公子虽机关算尽,却也一个不慎,不仅放走了对头,更伤了自己手下。空空儿知时机一闪即逝,毫不犹豫,右掌挥舞,使隔山打牛之术,瞬间便将身边一干黑衣人全数击毙。左手则直取鬼盗令符,眼看就要得逞,地上海盗头子的影子忽化作只黑色大手,一把摁住了令符。空空儿见成功在即,怎肯放弃,集真力于左掌,探入那影子要争夺蛟鳞琐片。可虽抓到令符,却也被黑影缠上了手臂。便在此时,背后厉风又至,空空儿知大事不好,被拉住了躲闪不得,只能聚全身真力于后背,硬接了景公子一掌。待挨过一招,忙以右手为剑,向着缠在自己左臂上的黑影砍了下去,同时急速起身远逃。再次站定,已是三丈开外了,他左掌已被自己斩成重伤,虽仍连在手腕上,却是鲜血淋漓,骨断筋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