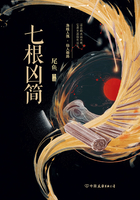我曾和奶奶来到爷爷的坟前,栽种了一些风信子草。那天春光明媚。奶奶用大剪刀把草修齐,使墓碑上的名字不被遮住。她用匈牙利语轻轻地对爷爷说着什么,然后又低声为他祈祷。
我帮奶奶除去杂草。我问奶奶,墓碑上可否坐得。她说用不着客气,那是爷爷的家,有一天也会是她的家。她的名字——珀珥——早已刻在了那块花岗石上。奶奶是位虔敬之人,她已身心疲惫,她说自己正等着上帝召唤。
我们在父母亲离婚之后都跟着奶奶生活。每当夏夜降临,奶奶总是坐在前面走廊上的一张摇椅里,听蟋蟀呜叫。她会一边用钩针编织手巾,一边讲蟋蟀在说什么话,那些故事使我和妹妹十分开心。
我们在屋里睡觉时总要用匈牙利语一起背诵一段祷词,遇到我不会发音的词语,奶奶就耐心地重说。奶奶性格坚强,但很慈善,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她早就腿脚不便,用上了拐杖,步履维艰,走路时总是小心地望着脚下。
那年春天祭扫墓地的时候我才六岁,因为我们先去过教堂,所以我穿的是礼拜服——一件带圆点花纹的裙子,后面打着蝴蝶结,脚穿白色短裤、外着亮黑的皮鞋。我故意拖着脚,鞋尖踢着鞋跟,在低矮灰暗的墓石间走动,“脚下留神!”奶奶告诫我。我确实需要训斥,因为我总是在前头乱跑,根本不在意脚下的障碍物,这就难免跌跤,膝盖和肘上的绷带便常常是我心不在焉的明证。
奶奶告诉我的时候总是一字一顿,不厌其烦,那深沉之语,仿佛是人生之旅的灯塔。但我则以为那是大人在故意管小孩,所以常常装着没听见,依旧在前头跑着耍着,不过我通常还是要转回她身边的,就像那天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走路,才使得奶奶格外能发现一些小钱币。
就在那个不寻常的礼拜日。奶奶发现了一枚硬币,那是在一座坟前刚割下的草里发现的。钱与泥土、草混在一起,已失去光泽,变得灰暗,要不是奶奶提醒,我就从它旁边踏步而过了。奶奶停下来,用拐杖轻叩着说:“看看那儿!”那语气好像我们遇上了宝贝似的。“这是一枚幸运币,把它捡起来。”
那时我很小,非常迷信神魔,于是就捡了起来。
那天是我头回听说“幸运币”,说“幸运”是因为只有你发现了它们而别人从未发觉。它们仿佛是些小小的礼品,是天赐之物,奶奶这样认为;当你捡到一枚幸运币的时候,你应该这样说:“幸运幸运,降我好运;我心之诚,此物为证。”
奶奶低声祈祷,她的声音柔和悦耳——这种和悦之声过去常常是一种轻吟低唱,使人蜷缩在奶奶的怀里进入梦乡。听着奶奶的教导,我觉得奶奶仿佛是感应到了天地万物之奥秘。
“许个愿吧,”我俯拾幸运币时奶奶说,她还叫我把自己的愿望保密——好像你吹灭生日蜡烛或对着星星许愿时所做的一样,“把幸运币收好,总有一天会心愿成真。”
我看着手里的魔物,重复着那些咒语,心潮立刻涌向那些我所渴望的事情上:我想学会骑两轮车,我想扔掉挂在衣橱里的带圆点花纹的裙子,我想在礼拜日穿旅游鞋而不穿那亮黑的皮鞋。奶奶笑了,好像她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要保证那是你真诚的愿望。”
春日融融,我在墓地里默默祈祷——寿比南山松不老,奶奶“幸运币要久留,”奶奶说,“因为有的愿望要过好久才能实现。”尽管那样,我知道奶奶的话仍有道理。我把幸运币塞到鞋坑里,这样就万无一失;回家时则放在枕头下,安然无恙。
那年九月,奶奶去世了。那天晚上,屋里似有异常之兆,我轻轻爬下床,拿出那枚和奶奶一起发现的幸运币。它珍藏完好。我把它紧紧握在手里,我知道过去对它寄托的愿望将难实现;我知道从那一天——去墓地的那个礼拜日起,也将有一天会去祭拜奶奶。
举行葬礼那天,我发现了另一枚幸运币。“这样的日子我能交好运?”我心中茫然,想不去捡它,但我想起了那天在墓地里奶奶用拐杖叩着幸运币的情景,我记得,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新割下来的草清香四溢,花岗石嵌在墓前。现在,这就是奶奶的家了。
我捡起幸运币,塞进我的黑皮鞋里,收藏了一天,从墓地回家后,我把奶奶的茶杯从碗橱里取出,把幸运币放在茶杯里,然后把茶杯置于我的床头柜上。
现在,幸运币仍珍藏在我身边,其实,我已收藏了数千枚。我能发现它们,是继承了奶奶的第六感觉,这些幸运币,装满了我的花瓶、首饰箱、塑料袋和钱包,装满了食品罐、饼干盒、咖啡杯和瓷杯。
我甚至用幸运币作为处事依据。通常在我遇到麻烦或有要事定夺之际,幸运币预示着我祈求的小小奇迹。它们使我深信:我无力企及的目标也终将如愿。
奶奶说,幸运币是天赐之物,而我则觉得,幸运币是奶奶的馈赠。奶奶仿佛在注视着我的生活,仿佛在鼓励我:“很好。艾琳!”她用匈牙利语叫我的名字:“你会通过它获得成功。”
或许我寄予幸运币的第一个愿望确已成真——奶奶并不曾离去,每次我捡起幸运币的时候,我都想起她;我看见奶奶斜依拐杖,老态龙钟,目视双足;我听见了奶奶的声音,那是她唤我入睡的催眠曲,还有在静夜里清晰可辨的匈牙利语的祈祷声。
“幸运幸运,降我好运,我心之诚,此物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