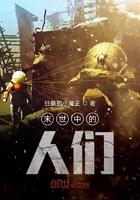约翰·范西1931年秋与埃尔茜结婚不久,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反抗侵略者,范西于1935年加入了英国空军。由于他患色盲而无法成为驾驶员,只好做了一名引航员。
1940年夏的一个傍晚,范西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女儿即将出生,这让他欣喜万分。正准备给妻子回信庆贺,却接到前往法国色当市附近执行轰炸德国兵营的任务,他立即放下手中的笔,迅速和战友驾机出发。不幸的是,当飞机接近目标时,遭到德军防空炮火的猛烈袭击,飞机被击落,战友当场死亡。范西跳伞逃生,降落伞刚到地面,就被一拥而上的德军俘虏。从此,他开始了长达5年的战俘生涯。
范西绝不甘心束手就擒,为了心爱的女儿,他决心要逃出魔窟。刚被俘虏时,他被关押在德国巴尔特的第一战俘营,进去后不久,就用狱友从厨房“借来”的一把铁铲从牢房往外挖掘地道,快挖好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致使地道进水从内部坍塌,只好被迫中途放弃。
范西没有气馁,又选择了另一个地方重新挖掘。糟糕的是,即将挖通时,却被看守发现,他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德国人怕他利用这里熟悉的地形再次逃跑,把他转移到第十一战俘营,并加强了对他的监管力度。表面上看,范西好像老实了许多,实际上,他逃跑的欲望比先前更加强烈。他瞄上了“仁慈”的德国人提供的金属餐刀,开始了新的挖地道行动。他后来回忆说:“金属餐刀让我能加快速度,我把土弄松,然后铲出去……这是一项大的改进。”
遗憾的是,和上次的结果一样,当地道即将“竣工”时,还是被德国人发现了。这次,他受到比前次更残酷的惩罚,德国人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放在似火的太阳底下暴晒了整整3天。虽然他已经奄奄一息,但当德国人问他还逃不逃时,他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答复。这让德国人恼羞成怒,又把他吊起来狠狠鞭打,但他依然缄口不语。
德国人本想杀一儆百,不知道为什么在即将对他执行枪决时,又忽然改变了主意。1942年5月,他被转移到波兰萨甘的第三战俘营继续服苦役。不管遭受多么残酷的折磨,但范西心中的信念始终没有熄灭:只要活一天,就要想办法逃出去,与妻子和女儿团聚。
他又开始实施新的逃跑计划,并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决定联合其它狱友一起干。他利用出工的机会,详细查看了外面的地形,然后精心设计了3条挖掘路线,并把3条地道分别命名为“汤姆”、“迪克”和“哈里”,然后组织狱友利用晚上的时间轮流作业。
为防止被德军发现,此次挖掘的地道深9米,高宽仅为0,6米。两个月后,3条地道成功挖通。就在准备逃跑时,那条“汤姆”地道还是被发现了,好在还有“迪克”和“哈里”做备用,大家只能等待时机,从这两条地道逃出去。
1942年10月,在范西的带领下,76名战俘通过“迪克”逃了出去,但很快就被德军发现。逃跑中,50人被残忍枪杀,仅有3人成功逃过围追,其余23人被抓回,其中包括范西。
范西理所当然要遭到比其它人更凶残的惩罚,他先被剥光全身鞭挞,之后又被关进潮湿阴暗的地牢,连续5天不提供水和食物。那些天,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冥冥中,女儿的呼喊又将他拽了回来。他对自己说:“你绝不能就这样死去,你一定要活着出去见心爱的女儿!”范西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纳粹从未见过如此顽冥不化的俘虏,决定和他继续把猫捉老鼠的游戏玩下去。1943年4月,他又被转往立陶宛海德克鲁格的第六战俘营。在那里,他表现得异常积极,曾一度被树为其它战俘的“楷模”。但他内心却一刻也未放弃过逃生的希望,他在窥视,在等待,一旦时机成熟,就去实现心中的那个信念。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他看准了一条德军运送给养的船只,乘哨兵不备藏到船底,满以为这次能顺利逃生,但开船时间却因故被推迟到第二天,看守清查人数时发现少了范西,立即进行大规模搜查,很快就把他从船底抓了回来。
范西在被德国纳粹关押的5年期间,共换了4处战俘营,挖掘了8条地道,5次试图逃跑。那段时期,他被德军“高度”评价为“最坚定的逃跑者”。
1945年,范西被盟军从战俘营中救出,当时他的体重只有36公斤,而且浑身长满了虱子。当医生要为他检查身体时,他急促地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马上见到我的女儿,为了这个愿望,我已经努力了5年时间。”范西在战俘营逃生的经历曾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拍成电影《胜利大逃亡》,一时轰动全世界。
前不久,95岁的范西因病去世。他的女儿珍妮特·范西撰文悼念:“父亲是个非比寻常的人,他正是知道了自己要当爸爸的消息支持他生存下来,并促使他不断试图逃跑。他的信念在别人看来也许非常渺小,但在他心中却是无比神圣的,而且为了实现信念,他一直奋斗不止。父亲的努力,最终让他的敌人也由衷地肃然起敬,这种信念的力量,无疑是伟大的和值得敬仰的!”
卖报纸的父亲
刘晓峰
霎那间,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眶噙满了泪水,终于明白了父亲以前说过的那句话。
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蒸好的两个馒头和装满冷开水的塑料瓶子悄悄放进绿色的挎包里,背起匆匆离开了家。
父亲卖报有几年了。我多次劝他别去卖报,退休了就在家里享享清福吧!他总是说:“等你成家以后,我就不卖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这样说。
报纸批发站距家很远,父亲总是风雨无阻地第一个到达。
送报车一到,早已等候的报贩就蜂拥而上,将一摞摞的报纸争先恐后地抢着往自己的挎包里塞。他们当中有下岗工人、进城打工的农民、辍学的小孩。父亲挤不过他们,只好站在一边。批发报纸的老板挺照顾父亲,每次都给父亲留着一摞。
拿到报纸后,报贩们就迅速四散开去,在大街上吆喝起来。父亲通常不在大街上卖报,因为街上的报贩太多,而是把报纸拿到在市区和市郊间往返的铁路通勤列车上去卖——父亲是铁路退休工人。
车上报贩不多,只有两三个,比起大街上来说报纸要好卖得多。父亲左手腕托着一张硬纸壳,上面交错迭放着各种报纸,在上下班的职工和旅客当中不停地来回穿梭和吆喝叫卖。
通勤车比起正式旅客列车来说,既破旧又肮脏。冬天车厢里直灌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父亲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裂开了冰口;夏天车厢被烈日烤得发烫,父亲的衬衣上是一圈圈泛黄的汗渍,豆大的汗珠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下来。
列车沿途有六个站。为了多卖几份报纸,每次列车徐徐进站还未停稳,父亲就从车上跳到站台上,趁停车的几分钟,向站台上候车的旅客和列检所、信号楼、候车室正在当班的铁路员工卖报。
通勤车经常停车不靠站台,健壮敏捷的年青人上下车都感费劲,何况象父亲这样上了年纪、手腕托着报纸、肩上背着挎包的老人。下了车跨过钢轨还得爬高高的站台。父亲站在路基上爬不上去,就只好先把托着的报纸和挎包推上站台,然后用双手支撑在站台的水泥地面上,抬起右腿颤巍巍撩上去,接着埋下头伛偻着腰,身子向左微倾,几乎贴在地上,使尽全身的力气慢慢地爬上站台。
若遇列车交会,父亲还得在站台上等着其它列车进站后,向刚刚下车的旅客匆匆兜售。有时,为了从一个站台转到另一个站台,争抢时间,父亲还得从一节节车厢腹部底下钻越。当列车重新启动时,又笨拙地跳上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弄不好身子就会卷入车体底下,被滚动的车轮碾成齑粉……
父亲的早餐都是在车厢里忙里偷闲吃的。我每天也要乘通勤车上班,时常在车厢中遇见父亲。有几次我看见父亲气喘嘘嘘地坐在一旮旯椅子上,左手捏着干冷的馒头,右手握着塑料瓶,一口馒头一口水,艰难地咀嚼着,不时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珠。看见父亲疲乏的模样,我心里酸酸的,就对父亲说:“我来帮你卖吧。”父亲摇了摇头,慈爱地说:“好好去上你的班吧!别耽误工作。”
父亲每天早上天不亮出门,中午回到家里随便刨几口饭后小憩一会,下午又出门卖报,直到暮色苍茫才蹒跚回到家里。天天如此来回奔波着,似乎不知疲惫。
有一天,我告诉父亲我准备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他从旧柜子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包裹,一层层打开,拿出一张存折郑重地递给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我和你妈妈都已经老了,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这里有三万块钱,是用我的退休工资和多年卖报纸的钱积攒下来的,你拿去用吧!再加上你自己存的钱,到单位上去买一套房子。今后你们小两口好好生生地过日子吧!”霎那间,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止不住自己的伤感,眼眶噙满了泪水,转过头悄悄拭干——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以前说过的那句话。
自从我结婚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卖报了。
无以为报的父爱
金光
“爸,您为什么如此倔强,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为什么不给儿子一次报答您的机会。”
这一次,儿子已经是第三次催促父亲进城了。父亲站在地头望着田里的麦苗说:“把这一茬麦子收了就走。”儿子说:“这一次可是真的了,麦收完咱就到城里住。”父亲没说什么,只点了点头。
父亲就这么一个儿子,上了大学留在城里工作了。一切都没有让他操心,儿子工作三年,找了个城里的俊姑娘结了婚,到了第七个年头又给他添了一个孙女儿,还分上了一套房子,儿子像生活在天堂里。
儿子生活好了,就想报答父亲。娘死得早,是父亲把他拉扯大的,又供他上了大学。父亲已是七十有二的人了,劳作了一辈子,可整日还是离不开那块责任田。一年四季耕了耙,种了收,总没有到头的日子。儿子心疼父亲,要接父亲到城里来住。小两口商量好了,单位集资建房,他们专门报了160平米的一个大套,说是父亲在乡下宽敞惯了,不能让他到了城里有压抑感。可回家两次和父亲商量,他就是不愿离开,总说还能干的了,不需要他们操心,等干不了活了就跟他们到城里享清福。儿子没招儿,只好由着父亲。近段时间,父亲的身体突然急转直下,先是两腿肿胀,后来血压也一个劲地往上蹿。儿子想,这回可不能再由他了,说啥也得让他来城里住。儿子回去接父亲的时候,父亲已从乡卫生院回到了家。他说,人老了毛病多,也没什么大病,吃点药就好了。
儿子在家里缠磨了两天,父亲还是那句话:“把这茬麦子收完就走。”儿子只好先回了城,临走的时候,他看着脸色腊黄的父亲说:“爸,今年收麦我也回来帮你。”父亲说:“你有你的工作,我能干得了,不要因为这些麦子影响了你的工作。”儿子坚持说:“也就几天时间,没事儿的。”
儿子说话算话,麦稍一发黄他就出现在了父亲的地头。这时候,父亲仍旧站在那儿望着田里黄灿灿的麦子。见儿子回来了,父亲的眼里露出灿烂的笑,一会那表情又凝重起来。儿子看出了父亲的心思,说:“这几天我们什么也不说,只管收麦子,成吗?”父亲没有回答他,而是顺手掐了一穗麦子,递到儿子的面前说:“你看,今年雨水好,这麦子长得粒儿多大!”儿子接过那麦穗看了看说:“下镰刀吧?”父亲说:“别急,让我再看看。”说着,就走进田里,顺着麦行像小孩似的来回走着,眼里透着莹莹的光,走了一会儿,又站在田头掏出一支烟慢慢地抽起来。抽完了,父亲就把那烟蒂狠狠地在地上一摁,再用脚踩了两下,果断地说:“开镰!”话音未落,把一把沉甸甸的麦子往怀里一捋,就下了镰。
儿子跟在父亲后面,弯腰辛苦地割着麦子,不时在脸上抹着汗水。歇息的时候,儿子征求意见:“爸,你年纪大了,我去镇上雇两个人吧?”父亲的脸一怒:“雇人做什么?就是收到明年我也愿意!”儿子不敢吭声了,默默地坐了一会,又拿起镰刀割起来。
这几天,天气也特别的好,四亩麦子父子俩用三天时间割完了,然后他们把麦子一捆捆运到了麦场上脱粒。父亲干得很慢,儿子有点纳闷儿:记得往年麦收的时候父亲总嫌收得慢,吆喝说,抢收抢收,就得和天气抢着收!今年却一反常态,不知为什么。
新麦子脱了粒,父亲精心地用筛子筛去灰土,又摊场上晒了两天日头,这才装进一个个蛇皮袋里让儿子往家里扛。只半晌时间,旧屋的脚地上,就堆起了小山一样的新麦子。立刻,满屋就有了新麦子散发出来的香味儿。
父亲坐在屋檐下,点起一支烟,眯着眼睛欣赏着那个小山。
晚饭吃得很晚,父子俩一起吃着唠着。父亲说:“明早你去找个卡车把麦子拉到城里。”儿子说:“好的,明日一早我就去。”父亲说:“这房子没人住就锁起来,什么时间想家了就回来看看,住几天。”儿子说:“好的,房子就锁起来。”父亲看没什么交代了,就催儿子睡觉,自己也进屋睡了。
第二天早晨,儿子起得很早。他没敢惊动熟睡的父亲,而是到乡里雇了辆卡车,准备把新收的麦子装上车,和父亲一起进城。车装好了,却不见父亲起来,儿子就到父亲的屋里叫他。
儿子走进父亲的屋里叫了几声没人应,儿子就去摇父亲,一摇,吃了一惊: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去世了。儿子的两腿一软,跪在了父亲的床前,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爸——”眼泪刷刷地顺脸而下……
“爸,您为什么如此倔强,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为什么不给儿子一次报答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