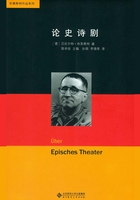2006年夏的一个下午,天热得要命,突然一阵狂风,毫无征兆的大雨劈天盖地。我本来在一间小阳台里无所事事,结果不知怎么竟被反锁在里面,只能拄着下巴看雨。这场雨,爆发出它最大的能量和生命力,先是在地表涓涓地流淌,然后就汇成了开锅状,雨点射进水面激起无穷尽的水泡儿,它们拥挤着,欢乐地、冲浪似的跌跌撞撞向远处游开,中途破灭,然后新的力量再次萌生、融入、消弭……在它们短暂的疯狂中,自动升格的视觉引领我得到了一种全新的快乐。独自待在一个干爽和温暖的环境里,看着外面雷雨大作,那种安全感里面似乎夹杂着不知指向的窃喜,看着生生灭灭的水泡儿就像是上帝在俯视子民,我知道它们诞生的开始,也欣赏着它们短暂的舞蹈般的欢愉,转瞬间毁灭——此刻即便是末日,我也绝不会感到恐惧。
那种生生灭灭一眼望穿,穿脱于另一种生灭序列的快感让我铭记了很多年。也让我执拗地相信,雨水里面发生的故事都跟美好相关,电视剧里面一旦下雨,男女主人公注定会找到属于他们的一间破庙,带来了二位制造肌肤相亲的借口。像是某年央视内部晚会敬一丹大姐说的那样:“这样的夜晚,除了制造人类,我们(停顿)还有什么别的追求!”我相信,停靠在“夜晚”之前的“这样”,是大姐内心深处的隐秘情境。安详,脱离了人群的窥视,在一个逼仄的得天独厚的境遇里,无需借口便能放纵得心安理得的一个“这样”。
如果单纯爱盯着水泡儿看,你们一定会以为我是弱智。我要说,在任何转瞬即逝的一瞥当中,都可能诞生一个让人觉悟的此时此刻。譬如,我对女孩子是好东西的念想的开化,并不是由一张张五官搭配绝妙的脸庞开始。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以腰为中线,背部和腿部有对折趋势的女孩。她就“这样”对着书架站着,一副眼镜从光滑的小鼻梁上滑下一点。她的唇好像带着个小小的尖儿,微微翘着,像你的嘴唇离开冰激凌时随意制造出来的尖儿,形状写意又带着动人樱桃味。那一幕的时间概念我已然不清晰了,但是作为写小说的人,我愿意把这个时间设定为一个黄昏之前。当时被震撼得麻酥酥、无以言表的我走出图书馆,一定见到的是云从远山的背后涌来,红彤彤地引向学生食堂。下课的姑娘小伙子们从身边走过,有的人的自行车后面是一个穿裙子的女孩,有的是一本计算机教材,不论是什么,它们全部指向此时此刻我的欢愉、刚刚目睹了宝藏沉甸甸的内心!太美的东西,沾染了一切。
我想是这样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建构了我们对世界奇妙的认知,我们开始有了挣命于天地间的个性,有了徒劳与欢笑,有了夏日蝉鸣的联想、秋天净水旁的忧伤。知道了香蕉大则香蕉皮大的道理。
此生消遣的事
在美好的书中,写出的误解也是美好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
裹着皮夹克坐在出租车里,我经常会要求司机把电台广播的声音放大一些,这像是一个习惯,司机不是我的陪伴,我们之间如果想建立起交谈,要费一番周章,对于厌恶繁琐的我来说,听一听广播来排遣路上的暇余,算是再好不过的了。
也可以看路人,观察他们走路的样子,穿着,色彩;打几个电话,解决一些工作上没完的事。打给母亲,说些天气、饱暖的话。家里在装修房子,我的房间装成什么样,母亲总是要再来请示,书房的玻璃到底是毛糙的还是精细的花纹,要能摆下多少本书的书柜。我一一回答,我为她能尊重我唯一在意的一点事感到满意。
客人来时,我们可能坐在一起,如果是花园里,常常会套上一件舒服的衣衫,坐在一角的精挑细选的椅子上,倒一点点喝的——不需要特别昂贵的饮料,沉郁时可以喝啤酒和咖啡,宁静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南方春茶。很可能,话题会涉及文学和建筑,这不是一个标榜教养的习惯,却变成了生活里的必须,就像诗歌对现在的人来讲,用途越来越少,非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定期读一些诗,就只能含糊其辞,诗是必须。
需要一些见识渊博的朋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一般选择沉默,偶尔会点一下头,笑两声,不需要恭维对方的见识,这不过是礼貌。我跟朋友们都不常相见,相约一些纸醉金迷之所就更加的不合自己的胃口,我们保持神交、神秘和对彼此的敬仰,就像普鲁斯特描述的那样,“不乏殷勤交好之情,但是只要说出冷冰冰的再见,那种亲密殷勤就会告一段落”。
我只要出发去一个目的地,哪怕是赴一个约会,也常常不合时宜地带上一本书。精装简装都无所谓,只要不过重,过分花俏,变成一个耀眼的累赘。常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两个人,在北京这样大的城市里相约一个目的地,谁早到半个钟头是平常的事情。一本书恐怕是就像有人出门要照一照镜子那样的,算作一个偏执的必要吧。我只要去到大学的校园里,一定找个安静的地方抽根烟,到自习室坐会儿,甚至跑到课堂,坐在后排听上一节……做时尚杂志,常遇到男人如何消遣的问题。抽好烟、喝好酒、开好车、抠好女,这样的堆积起来的男人像是相互之间可以随意拼贴的模板。朱光潜感慨过,消遣就是娱乐,无可消遣当然就是苦闷。世间喜欢消遣的人,无论他们的嗜好如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强旺生命力。依我看,这境界小了。消遣是人生的构成的全部。纪录这些消遣,就像书页上的细微得容不下一粒灰尘的小孔,吸进数不清的记忆。它们本身与生俱来,没有意味,积攒成厚厚的一本时,就变成昨日昨日、昨日之事了。
舒适人生的长宽高
“有人从我身边跑过
问我是不是个平静的人,我说不
我说不,人们的命运已种上了水稻”
——AT《回答》
罗永浩同志的一句话,我很有共鸣:“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常在黑夜的时候走来走去,为中国的命运苦苦思索。”还有一句来自一个写作却开了一间粥店的朋友经年不变的MSN签名,“三岁时,我很忧郁,经常,在河边丢小石头。”两句话同时流行甚广,它们像中国传统简笔画那样,通过两根细细地线条,几乎概括了我生命至今的全部神采。
追溯起自己的生命轨迹,我常用唏嘘两个字来形容。唏嘘的风,唏嘘的落日,唏嘘的背影。甚至在电话里跟多年未见的友人聊天结束,总要彼此点评一下,太他妈唏嘘了!
采访时,受访者常常爱从自己的小时候谈起。谈他沉湎于某一项事业(他今天坐在这里受访的事业),谈他为此吃了多少苦,绕着弯夸耀自己是怎么样顶住常人所不能的压力和困苦最终到达了成功的彼岸。其实人与人的成功都差不多,就像每一个面对我端坐的女艺人都会像透露隐私一样,告诉我她们是怎样面对潜规则不受利诱的,先为自己的人格树一座丰碑。人生惊人的一致性,让人类的生命时间变短了。人与人之间的度过的口唇期、肛门期、生殖器期和生殖期的大同小异让我对记者的工作充满了怜悯。受访者的重复,同时让记者的生命长度也随之缩短。
如果非要让我从人类自己编织出来的游戏中选一种最无聊的,我一定会选高尔夫球:一只球,被打飞,飞呀飞,落在用望远镜才能看得见的地方,然后一票人呼呼啦啦地跑过去,再打飞,飞呀飞……我不止一次见过富豪同志在不合时宜的谈话场合,站在人群中眼睑低垂,手臂垂直于地面,臀部翘起,浑身的筋肉绷直,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是羊角风发作自己在拼命控制。他乐此不疲的潜台词恐怕是在昭告自己的身份,他是一项贵族运动的一分子了。在一次高尔夫品牌的活动上,主办方送给我一支球杆,我婉言谢绝,假笑道:我很忙!我偏执地带着仇富情绪看待高尔夫,以及不断在各种场合赞叹它让生命变得漫长的功能。
演技派巨星克里斯托弗·沃肯说:“拍摄了《猎鹿人》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已经在娱乐行业干了30年,而在这之前,我几乎默默无闻,我是说,从辛勤耕耘到接拍了这部电影,突然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像是染了流行病,我变得忙于聚会了,成了社交狂。真想不到,这竟然持续了10年。”老沃肯已经有唏嘘之态了。这种唏嘘从18岁开始就在我的生命里常常出现。如今,一组大片的拍摄现场,我看着疲于奔命,不断为自己、为电影宣传、为演唱会摆出各种姿态的艺人们,他们平静、没有怨言,像度过自己的生活一样(其实就是在生活啊)度过与化妆刷、灯光和机器一起的每一天。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常常为之扼腕。香港的配角之王“大傻”成奎安去世了,明星的陨落最近像结伴的流星雨。生命的长度对于某些职业来说,是那么短暂。上一次荧幕上见面还是后生有为,下一次见面已经是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