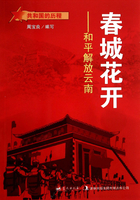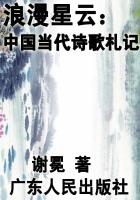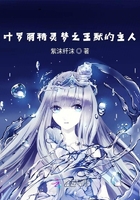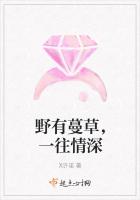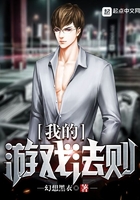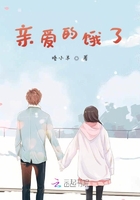在市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一位去春从台湾归来的老先生告诉我,离开营口已经半个世纪了,踏上二十里长街一看,样样都感到熟悉、亲切,又样样觉得生疏、新鲜,触目兴怀,真有隔世之感。我问他故乡风物,哪一样最使您动情呢?”
老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街道两旁的绿柳。”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怔,继而有所领悟:先生当日含泪辞别乡关的时候,这座日伪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城市,兵连祸结,疮痍满目,漫空卷着黄尘,遍地泛着白碱,萧索破败得很而今头白归来,登车入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饱绽着春意的青青垂柳。它们像亲人般笑立在东风里,轻摇着翠发,漫闪着青睐,频频招手致意又好似无数绿色甲兵,排成长长的仪仗队,等候着远道归来的主人的检阅。五代诗人孙光宪就写过这样的咏柳佳句恰似有人长检点,着行排立向春风。”它们隽美的风姿,给游子以归乡的慰藉,给劳人以亲切的慰安,给远方来客以清新的美感和多方面的联想。这一切,自然要使老人心旌摇荡,欣然色喜了。
其实,不要说一别五十寒暑的天涯倦客,即使一直生活在市区内的人,当看到那满城新绿时,又何尝不为之动情呢?
提起城市的路树人们自然会想起福州的如云似盖、根须垂挂的古榕,伊宁的直耸云天、葱葱郁郁的白杨,羊城的红花似锦的英雄树,上海的枝叶扶疏的法国梧桐……这些无疑都是颇饶韵致、多彩多姿的。但是,正如一首民歌中讲的天是故乡的蓝,水是故乡的甜,山是故乡的青,月是故乡的圆。”我总觉得,美化、绿化了辽滨之城的行行路柳,是更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一排排的垂柳,清荫黯日翠带牵风,着实给熙熙攘攘的闹市创造了一种清新秀雅的气氛。特别是营口街头,由于靠海低洼盐碱度高,莫说参天的林木,就是铺地的绿草,也一向很少。近年随着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市区主要街道两旁全部栽植了翠柳背后映衬着整齐的楼房,也称得上是“风景如画”“杨柳非花树,依楼自觉春。”梁元帝萧绎的这两句诗用在这里倒也贴切。
柳是报春的使者。当寒威退却、冰雪消溶的时节,痴情浓重的春风朝朝暮暮奏着催绿的曲子鼓动得万里郊原生意葱茏。花丛草簇从酣睡中醒来,急忙抽芽吐叶点染春光顿时大地现出了层层新绿。然而,这一切与高楼栉比、车辆穿梭的城内是不相干的。那么,是谁最先把“春之消息”报告给十丈红尘中奔走道途之人的?正是街头的翠柳。
溽暑炎蒸,骄阳喷火,行行路柳为过往行人撑起遮天绿伞,清凉凉的略带咸味的海风扑到脸上你会感到燥气潜消,无异入清凉国。清晨起来你尽可以沿着柳林穿行过了这棵迎来那棵满路清荫伴着几声清脆的鸟鸣,偶尔会有一两滴露珠滚落下来,凉生颈际,于恬适、惬意中不觉走出了很远很远。
秋宵漫步,清爽宜人。在城市住房尚较紧张,许多人家还是三世同堂的情况下,这长长的林荫路便成了翩翩情侣的“爱的长廊”。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挽手并肩徜徉其间悄声地交流着浓情蜜意,一任多事的柳丝在鬓发间撩来荡去。有人调侃地把它比作欧洲的谈情胜地一“维也纳森林”,这当然是过分的夸张。
即使是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严冬,家家紧闭着门窗,地面上满铺着积雪,这行行垂柳也不显衰颓、沮丧之态,依旧温存地摆荡着枝条,似向行人问候,使人们记起往日撩人的春色,憧憬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柳在森林王国中平凡得很,登不上名贵树种的殿堂。但以其特有的风姿和功用,一向受人青睐。柳树是个大家族,世界各地约有五百多种,仅我国就拥有一百九十多个品种。举凡垂柳、龙爪柳、观音柳、馒头柳、长叶柳、小叶柳、白柳、紫柳、旱柳、水柳、沙柳、杞柳等等,都是比较好的绿化品种。它们适应性强,生命力旺盛,容易栽植,生长快寿命长。其优胜之处,白乐天在《东涧种柳》一诗中描述得清清楚楚广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榧楠固难移。不如种此树,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荫况非迟,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
柳是生机的象征。相传黄巢起义时,曾规定戴柳为号,就是取其生机旺盛,易得成功的寓意。古时清明节民间有头上簪柳的习俗。“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头上插柳意味着严冬遁去,春天来临。柳与苍松、古槐不同,给人的印象是清丽、活泼的。本来,营口就是个比较年轻的城市,街市的形成不过百余年历史。市区绝大多数楼房又都是在1975年强烈地震后新建的,年轻的城市衬上这活泼、清丽的夹道垂柳,就更显得生气勃勃、欣欣向荣了。
在一般人心目中,夭桃艳李自是佳丽无比的春色。可是那位写过《陋室铭》的很有些辩证思想的刘禹锡,却说:“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尽时!”在诗人的笔下,柳色是十分秀美的。陆放翁说:“杨柳春风绿万条,凭鞍一望已魂销。”孙鲂说:“春来绿树遍天涯,未见垂杨未可夸。”足见其推崇之至。
也许是这些原因吧,自古以来,从皇家到民户,从军营到田庄,灞桥、粱苑、隋堤、沈园,到处都喜欢栽植柳树。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临行时还珍重地带上一株长安的翠柳,栽在大昭寺内,繁衍至今,许多去拉萨观光的人,都愿意一瞻“唐柳”的风采。清末爱国将领左宗棠率部西征,“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后人记着他的“遗爱”,亲昵地称之为“左公柳”。
当然,就营口人来说,酷爱街头绿柳,不仅仅是珍惜春光、珍惜绿荫,也是珍视自己的茧花汗水、劳动果实。如果说,在其他地方是“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那么,在这盐碱低洼的辽滨之城,栽活养大一株翠柳却绝非易事。这满城路柳的荣滋,不知要费去几载光阴,消耗多少人、财、物力。单是每年从外地运进城里来的植树用土,即当以数万吨计。换土、栽培之后,还要细心培护一缠裹草绳,围上木障,或护以石栏,定期灌水、喷药认真照管。
去年秋天,我曾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黄昏时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举着浸过煤油的火把,烧烤窗前路柳的枝干。年轻的爸爸在楼上看到了,慌忙地跑下来,将火把夺过去踩灭,并厉声斥责着:“再不许你糟蹋树!”小男孩一面委屈地辩解着,一面用脚踩杀熏烤下来的毛虫。爸爸低头一看,知道错怪了孩子,不好意思地重新点燃起火把,和儿子一道继续捕烧其他树干上的害虫。
我还听人们讲述过两个青年教师结婚植树的故事:在新婚蜜月里,小两口商定在院里栽几棵柳树作为纪念。丈夫喜爱陶诗,仰慕“五柳先生”,提议栽五株垂柳;妻子是现代史教员,主张栽植六棵理由是:当年贺龙同志趁战争空隙,在晋西北蔡家崖建立过“六柳亭”。正当这对小夫妻含笑争执时,老祖母出来打了“圆场”,说也别吆五,也别喝六,我说栽它九棵。九柳——“久留,取个吉利。”就这样,九株新柳绿化了整个庭院,一时传为美谈。
面对着鹅黄嫩绿、老紫娇红的千般花木,人们总喜欢把它们人格化,赋予一定的主观意念。其实,花木本身何尝有什么自觉的抱负、理想,无非是物竞天择的生存规律使然。但是,由于它们独具的形象、素质,确确实实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寄托。苍松使人想起坚贞不屈的志士,古榕使人想起胸前飘着长髯的智慧老人,芭蕉使人想起浓妆艳抹的姝丽,而辽滨之城的翠柳,则使人想起具有高尚情怀和献身精神,“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孺子牛”。
辽滨翠柳,植根于贫瘠的盐渍土壤,自从绽出第一片嫩叶,便开始吸吮着苦咸的乳汁,应该说,生计是艰难的。但它们自甘清苦,乐观向上,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尽心竭力装点着大地母亲,把满路清荫托献给过往行人。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同一些教师、医生、作家、记者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也熟悉他们的属性。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一片片一行行从异地移来,在辽滨之城成活长大的绿柳,都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身旁这些可敬可爱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海、北、天、南”,告别了繁华、绮丽的家乡,扎根在这座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差,暂时还有许多困难的中小城市,为四化建设倾洒着汗水,所取者少,所予者多。这种风格,不正像那些辽滨翠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