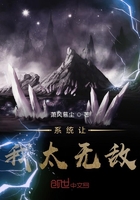陈致庸一听到事情惹到刘主席的身上,脸色煞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楚河就不停给副官说好话,言辞诚恳,还偷偷塞了准备好的钱财给副官。
副官喝了好几杯酒,才松了口,“这事还有一点希望,就是把陈家少爷带的那批货,转到我们军队上,说是我们军队的货物。这样的话,还有点余地可谈。”
楚河和陈致庸马上点头称是。
“但是这事孙旅长要担不小风险……”
“让孙旅长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我们那里过意得去。”陈致庸明白副官的意思,“什么都好商量。”
副官见陈致庸是个明白人,把陈致庸的手牵过来,指头在他手心比划了两下。然后告辞走了。
“这世道……这世道……”陈致庸在副官走了之后,不停摇头。
“多少钱?”
“一万大洋。”陈致庸说道,“那里是孙旅长不在,他就是指派他副官跟我谈价钱的。”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楚河说道,“我还以为跟他有过交情,没想到这些丘八,都是认钱不认人的土匪。”
“现在没什么好说,”陈致庸说道,“我们马上回江油筹钱。”
“可惜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财。”楚河恨恨说道,“早知道当初就不该那么大手大脚花钱,结交江油的商人。”
“多说无益。你在绵阳等我,先托人,不要让那个忤逆子受太多的苦。”陈致庸说道,“我快去快回。早日把他从牢里救出来,我一辈子为人诚恳,老来被这个不孝子给把脸丢尽了。”
“这一万大洋,绝不能让您来拿。”楚河说道,“我在江油还有几块翡翠,我尽快折了钱,用来就哥哥。”
“不行,还是我先回去。”
楚河拗不过陈致庸,立即雇了一辆骡车,可是楚河送陈致庸上车的时候,陈致庸一脚踏空,摔了下来,楚河见他面如金纸,连忙揉了半天胸口,陈致庸一口浓痰吐了出来,慢悠悠的说道,“我算是被这个小子气死了。老了,不中用了。”
陈致庸无法回江油,楚河把他安排在客栈,找了郎中来查看。郎中开了一剂药,嘱咐陈致庸不能心情焦虑。楚河对陈致庸说道,“您就在这边先照顾着哥哥,我回去就来。”
陈致庸勉强坐起,想了又想,最后给陈淑和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让她找账房取了钱财,交给林家少爷,自己不在家,就让林家少爷做主。
楚河拿了信,安顿好了陈致庸,坐上骡车,想着江油行去。一路上,楚河身体瑟瑟发抖,这是复仇前的兴奋。
陈淑和自从被父兄做主许配给那个面貌狰狞的林朝幕之后,陈淑和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已经绝望。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在下人口中,满口称赞林朝幕少爷的为人斯文正直,也不拿大户人家的架子,和老爷一样都是满腹诗书,但是比起老爷,脾气却好得多,虽然脸上看起来凶恶,说话却客气得很。
下人都在说林朝幕的好,父亲和兄长更是看重林朝幕。陈淑和知道哥哥是个眼光短浅的人,但是父亲一生阅人无数,而且性格耿直,能看中的人,品行和身世绝对是上佳人选。于是偷偷见了林朝幕两面,一看到林朝幕的刀疤脸,心里就慌乱的很,躲了开来。
昨日在房里,听到院内一阵慌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半响,陈淑和出来吃饭,才发现父亲已经走了,听下人说,是哥哥在绵阳惹了官司。林朝幕和父亲已经去搭救。陈淑和一弱女子,那里有什么主意,只能等在家中,惴惴不安。陈淑和一夜没睡,等着消息。白天又等了一天,到了半夜才听到院子里有动静,也顾不上身份,披了衣服出来。看到林朝幕和管家边往中厅里走,边急切交谈。
管家和楚河正在中厅说话,看见小姐过来了,连忙说:“小姐来的正好,家里有事让你做主。”
“我能做什么主?”陈淑和慌的手足无措。
楚河连忙把管家手上的信递过来给陈淑和看。陈淑和问道:“我哥哥怎么样了,爹怎么不回来?”
“岳父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两头跑。”楚河说道,“嘱咐我回来筹钱去绵阳打点。”
陈淑和匆匆看了信,“那马上筹钱,我们找账房先生去。”
“账房先生住得远,来了也没用。”楚河对管家问道,“账房能支出这么多钱吗?”
“肯定没有这么多。要到钱庄去兑换银票。”
“那只能明日再说了,”楚河说道,“我也回去,把寄放在向家的那几块翡翠给折成钱,如果够了,你们就不用去钱庄。”
三人说了一阵子,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么办。
楚河告辞走后。陈淑和回到房里,刚才和这个未来的夫婿交谈了许久,这是第一次。刚才心里惦记父兄,也就没在意他的相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林朝幕一门心思的想救哥哥,把这事当做自家的事情操心,心里好感顿生,想着林朝幕的相貌,也不是那么可怖。
第二日中午,楚河又到了陈家,陈淑和与管家和账房先生正在等候,账房的钱财平日都是陈致庸亲自送到钱庄,账房里只有少许银两。现在陈家家人只有陈淑和,账房先生很担心,钱庄不会把大笔的钱财交给陈淑和,三人只能等待林朝幕过来出主意。看见楚河来了,都像看到了救星。
楚河匆匆走了进来,忙不迭的说道:“还好都在。你们筹钱怎么样了。”
陈淑和三人都默不作声。
“我手上只有这么多钱。”楚河把一个小布包放到管家的手上,“四千大洋,现在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带着钱去绵阳,我和小姐在家里再想办法去钱庄。”
管家已经看过陈致庸的家信,信里说了让林朝幕做主。马上就不耽误,拿着钱向绵阳去了。
剩下楚河陈淑和与账房先生,立即去了街上钱庄,果然钱庄的老板犹豫不绝,不敢轻易把钱支给他们。
“这么多年来,都是陈老爷亲自兑付。”钱庄老板说道,“他专门叮嘱过,一定要他亲自来。”
“现在我岳父在绵阳,等着钱救命,那里过得来。”楚河焦急说道。
“那我就爱莫能助。”钱庄老板说道,“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
陈淑和于账房现身面面相觑。
“陈家又不是与你一家钱庄来往。”楚河拉着账房先生走出钱庄,“我们快去下一家。”
不了连续去了几家钱庄,说法都是一样,陈老爷不亲自来,就不兑付。
“这下如何是好。”账房先生急得跺脚。陈淑和更是一点主意都无,楚河想了一会,对陈淑和说道,“那个玉簪,我要先拿回来当了,等我家里的钱来了,再想办法赎回来给你。”
陈淑和那里敢怠慢,连忙回家去拿玉簪。磨蹭了半日,到了下午,楚河和陈淑和到了向家,楚河把玉簪加上自己随身佩戴的玉佩给了向家掌柜,楚河问这两件翡翠,抵押给向家掌柜,先拿六千大洋,等陈老爷回来了,就赎回来。
向家掌柜本就对陈致庸暗度陈仓,用自家女儿做饵,把林朝幕这个大生意人给拉拢过去,这些日子,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看到林朝幕和陈淑和站在自己面前恳求,心里更是愤愤不平。
向家掌柜打了半天哈哈,就是不给个实话。陈淑和向着向家掌柜跪下,向家掌柜连忙躲避,不肯受陈淑和跪拜。最后才说了声,“这两块翡翠价值不菲,自己要请个人好好查看,明日再等消息。”
无论陈淑和如何求情,楚河软硬兼施,向家掌柜就是不松口。
无奈,三人只好回到陈家,再等一日,明日去听消息。
账房先生向二人告辞,走的时候叹了口气,“老爷平日太严厉苛刻,得罪人不少,现在他们一定是想看着老爷落难,不知道明日能不能筹到钱。”
楚河与陈淑和回到中厅,两人面对面坐着,都一时无话。
做了良久,楚河看到天色渐晚,对着陈淑和说道,“先吃饭吧。明日再想办法,看你脸色不好,这两天一定没吃什么东西。”
陈淑和叫了厨娘,吩咐去厨房做了酒菜。楚河忙了一日,确实饿了,坐下来饮酒。陈淑和站在一旁。楚河扬头说道:“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你何必那么拘谨,一起吃饭吧。”
“我从不和爹与哥哥同桌吃饭。”陈淑和低声说道,“我爹说了女人要有家教。”
“今后我娶了你,就不必理会这些破规矩。”楚河摆摆手,“一起吃吧。”
厨娘做好饭菜,说家里小孩病了,要赶着回家。陈淑和答应她去了。
现在整个陈宅,除了守夜的家丁,远远住在偏房,家里没了任何下人。陈淑和心里焦虑,天色渐渐黑下来,家里就只有林朝幕在,两人孤男寡女,若是让父亲知道,岂不是要大发雷霆。虽然和林朝幕有了媒妁之言,但是没成亲,父亲是不愿意两人单独见面的,更何况,现在是两人共处一室。
陈淑和不肯坐下来吃饭,就等着自己的未婚夫林朝幕快点吃完了告辞。
谁知楚河稳坐不动,慢慢饮酒,左一杯,右一杯,喝了一个时辰,还没有走的意思。陈淑和既不好逐客,也不好自己先行回房,只能陪着楚河,看着楚河吃饭。
楚河连续喝了十几杯酒,酒劲上来,苍白的脸变得通红,那些伤疤突兀出来,如同蚯蚓一样,在脸上蔓延。现在陈淑看到楚河的眼睛越来越冷,自己对楚河的惧怕又升起来。
陈淑和眼见自己的夫婿喝得醉了,却仍旧不肯停杯,心里暗自猜测,他一定也是被父亲和哥哥的事情,扰乱了心神,故心情烦躁,才会喝酒。陈致庸自己喝酒很有节制,陈淑和从未见过父亲喝醉过。倒是哥哥陈良茂经常大醉而归,被父亲责骂。陈淑和也不知道如何服侍醉汉。看着楚河越喝越醉,连筷子都掉在地上,心里更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