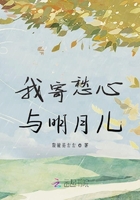夫秦皇一世万世之说,至今人笑其愚。莽之此言,不尤可笑乎!又因叛者日众,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此与村妪之诅祝何异?又刘歆、王涉自杀后,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郎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忧兵火。”莽曰:“小儿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既云莽佞邪,则其容止何其愚也!假六艺以文奸言,事固有之,假神仙以欺天下,其愚恐不至此。
《史通?曲笔篇》言:“《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鲜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在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余谓草莽之人,初登帝位,羞愧流汗,事所恒有。
《史记?高祖本纪》言诸侯将相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观此一语,当时局促不安之状,居然如画。又袁项城洪宪元年元旦,命妇人贺,项城起立,曰:“不敢当,不敢当!”夫以汉高、项城之雄鸷,骤当尊位,犹有此惶愧之状,则无怪乎更始之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矣。
《后汉书》又称:“更始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此又一事也。夫羞愧刮席,事或有之,问虏掠几何,恐不可信。此盖与王莽之愚,同为东汉人所缘饰耳。《通鉴考异》凡事有异同,则于本事之下,明注得失,若无异说,无从考校,则仍而录之,王莽、更始之事是也。
唐太宗之事,《新唐书》、《旧唐书》之外,有温大雅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在。温书称建成为大郎,太宗为二郎,据所载二人功业相等,不若《新唐书》、《旧唐书》归功于太宗一人也。案唐高祖在太原,裴寂、刘文静劝高祖起事,太宗赞成之,时建成在河东。击西河时,建成、太宗同时被命进军贾胡堡。天雨粮尽,高祖欲还,建成、太宗苦谏,乃止。在长安攻伐,二人之功亦相等。
后太宗出关,平王世充,擒窦建德,建成不安于位,王珪、魏徵劝立功以自封,时刘黑闼尽有窦建德之地,建成率众破灭之。创业之功,彼此既堪为伯仲,自非夷、齐,其谁克让?若玄宗讨平韦氏,宋王宪固辞储副,此因玄宗有定国之功,宋王毫无建树,故涕泣固让,与建成、太宗功业相等者绝异。温公乃谓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则乱何自而生?不司建成自视功业不让太宗,岂肯遽为吴泰伯乎?且唐初本染胡俗,未必信守立嫡以长之说,但监于隋文之废太子勇而立炀帝(炀帝亦有平陈之功),卒召祸乱,而建成、太宗之功又无高下,所以迟迟不肯废太子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