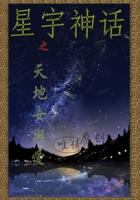餐桌好声音
清朝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有一章名为“戒单”,其中有一戒是“戒耳餐”。袁枚所指的耳餐是:“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
我倒是想把“耳餐”这个概念延伸一下,那些讲究形式、触动听觉的热热闹闹的菜品可以称为“耳餐”。美食从来不单纯是一个味觉概念,还涵盖着视觉、嗅觉,当然还应该有听觉。如果你在中国大饭店的夏宫吃饭,厨师长侯新庆可能会为你做一款鸡粥,这是吃鸡不见鸡的典型菜品,犹如川菜之中的鸡豆花。鸡肉打成蓉,做成粥,洁白清雅,犹如临水照花。妙的是搭配在旁边的馓子,酥脆,咀嚼在口,就是一阵一阵的酥麻,我喜欢吃馓子那种簌簌的声音,远胜其味道。
类似馓子这种食物,早而有之。在古时候,这叫“寒具”,寒食节禁烟火,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充饥。古时候南京的寒具很是有名,传说“嚼着惊动十里人”,可见其酥脆。我一边吃馓子,一边喝鸡粥,如果你在旁边贱嗖嗖地问我:脆吗?我也会贱嗖嗖地再咀嚼几下,说:你听。
类似的菜品有许多,传说慈禧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炸猪皮,别有称号是“响铃”,形容其酥脆。到后来,“响铃”这个词慢慢从猪皮上脱落,被安放在豆腐皮之上。如今江南有道名菜就是炸响铃。炸响铃要用油豆皮,在里面裹上馅,炸好之后,放在嘴里,犹如含着一颗铃铛,在牙床上叮当作响。
我喜欢松鹤楼出品的一道响油鳝糊,也是此中高手。鳝糊端上桌来,搭配着热油,当着食客的面,把热油浇在鳝糊之上,顿时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那种声响犹如一种呼唤,唤醒体内的馋虫。这道菜需要大量的胡椒和蒜头,算是重口味,而热油的功效是激发出鳝糊的香味。这也如同英雄登场的放礼炮撒花的过程,噼噼啪啪声中,我们行注目礼,然后拿起筷子,吃好喝好。
如果说响油鳝糊的声响是空山鸟语,那么三鲜锅巴的声响就是排山倒海。在眉州东坡酒楼,依然还有这道传统的川菜,锅巴用油炸酥,再用鸡汤将虾仁、番茄烧好,连汤带汁倒入其中,那种清脆的响声叫人食欲大增。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许多餐厅里都有这道三鲜锅巴,可是给它换了个名字——轰炸东京。每当热汤浇在锅巴上的时候,大家都要起立给这道菜鼓掌。一道菜有时候不仅仅是一道菜,也是大众心理的一个映射。抗战时期的“轰炸东京”,更古远的“油炸桧”皆如是。锅巴之美,不仅仅在于其声响动听,还有其味道合适,混合了各种料汁的鲜香,那种入口酥脆的缠绵,犹如一个法式长吻。
而在粤菜之中,也有如此浓墨重彩的美味,那就是各种啫啫煲。我平时爱去的是一家名为煲煲好的小店,专做各种啫啫煲,这种煲类菜品先将瓦煲重火烧热,然后放油,之后下主料,再放葱姜等配料,加入花雕,原煲上桌,揭盖之后,依然嘶嘶作响,盛况空前。尤其是里面的主料是田鸡、鱼头、肥肠,那种开盖之后的噼啪声,简直如同中彩票一般惊喜。
在美食传统中,煲是慢工,而啫则是急活。许多北方人见到“啫”这个字都有点吃不准,其实念ze,本身就是一个象声词,那是一种急促的、催人上劲、赶快吃两口的象声词,吃啫啫煲一定要争先恐后,借着那股锅气和声响,迅速吃下。不然只消一会儿工夫,那响声不在,口感顿时疲软了几分。
如果说那些餐桌上清脆的声响都是”少壮派”,也有一种美妙的声音是“遗老派”。这种声音就是:咕嘟咕嘟。小火慢炖的一道汤,滚开的火锅,一道腌笃鲜,都冒出这种孤独的咕嘟声,下面是文火,汤汁里面不停升起一些小泡,带来一些翻滚声,这种声音不适合群居,而是一个人的午夜,伴随着饥肠辘辘,肚子里发出咕咕声,锅里带着咕嘟声,两者配合着,完成着一次孤独的美食之旅。
在一个周五晚上,许多人都在看《中国好声音》,随便刷一下微博,就能看到各种评论和吐槽,诸如李代沫不该被徐海星PK下去,如何留恋王乃恩。那时我正在北京郊区的影棚里录制一档叫《中国味道》的美食节目,我装模作样地跟几个烹饪大师坐在评委席上,看着各路草根选手在台上煎炒烹炸,心中不由得想起了那些在餐桌上依然欢唱的美食,已经是凌晨,肚子饿得咕咕叫,那时我眉头微蹙,别人以为我在细心看选手烹饪,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正在心中默念:响油鳝糊、炸响铃、三鲜锅巴、啫啫肥肠……对那时的我来说,那些食物上桌迸发出来的美妙声音,简直比“中国好声音”还好声音。
口福如东海
话说吃无止境,接触的东西越多,越明白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不免有战战兢兢之感。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只有三顿饭,我掐着手指头算那些吃吃喝喝的放纵生涯,也不免有春宵苦短之遗憾。
另外一个心得是,别在饭桌上侃侃而谈。当你吃下一口豆腐,信心满满地说,这是云南建水豆腐的时候,旁边会有人提醒你,其实这是贵州青岩豆腐;当你笃定嘴里咀嚼的是产自洪湖的莲藕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一个声音默默地说:这是安徽当涂的塘藕,脆爽甘甜,可以生吃。这就如同一个自以为熟稔时尚大牌的买手,看到前面走着一个人,你确认他穿的衣服从款型到设计都是Dior2012年春夏新款,等他转过身,胸前的logo赫然印着Baleno。
前些日子在金融街洲际酒店地下一层的新荣记吃饭,我嘴里咀嚼着类似墨鱼仔的玩意儿,边吃边赞美:“这是我吃过的最鲜嫩的墨鱼仔了。”旁边的厨师长迅速地指正:“这是望潮,学名长蛸,属章鱼科,以东海出产品质最高,这是台州做法,名字叫盐水煮望潮。”
接着又上了一道菜,硕大一锅,里面有红笤粉,炖着某种说不上名字的海产品,这是台州土菜的做法,红笤粉筋道软糯,味道很厚,“不知名的海产品”也鲜美异常,我有点犹豫,“这是不是海葵?”我问厨师长。厨师长迅速回应:“这个叫沙蒜,学名叫海葵,也是台州做法,沙蒜难熟,以煨吃为宜。”
接着又上来一份鱼,柔弱无骨,颜色几乎微微透明,吃起来鲜嫩异常,只有一根主刺,其余的刺如胡须般柔软,放到嘴里轻轻一抿,就灰飞烟灭。我还是叫不上名字,只记得温州台州一带有一种鱼叫龙头鱼,生长在浅海,吹弹可破。我试着说:“这是不是龙头鱼?”厨师长面露欣喜:“这的确是龙头鱼,但是在我们当地,这叫水潺。”
最后一道大菜,家烧野生大黄鱼,我自然晓得这条鱼的尊贵,一斤价值数千,我的一个朋友20世纪80年代去上海,在餐厅点了一条红烧黄鱼,以为就是北方常见的便宜的黄花鱼,最后结账,200元,相当于他四个月的工资,最后几个人凑钱才出了餐馆。厨师长说:“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北方的小黄花鱼,其实味道口感天壤之别,不信你尝尝。”果然入口爽滑、鲜美,如同在舌尖涌入一片大海,肉质成蒜瓣状,洁白如同台州姑娘。
北方人往往用简单的几个味觉词汇归纳南方的吃食。提及江浙菜,第一印象往往是江南、柔软、清淡。烟雨朦胧的江南菜只是臆想中的江南,许多江南菜浓墨重彩,端的是油锤灌顶的温柔。
望京的一家宴稼厨房做的是江浙菜,其中主打的一款柴火猪手焖鸭简直是“胸口碎大石”的温柔。这道菜来源于金华与义乌交叉地带的一家人气小店,浙西擅长制肉,此菜非常简洁地将专供火腿制作的金华地区土猪手轻度腌制后,与壮年农家鸭同煲,加入各种调料和酱汁,以文火慢炖。开煲时,浙西农家饭菜的浓烈香味立马充斥整个空间。
我也喜欢这里出品的醉蟹,醉蟹这道菜不罕见,江浙菜馆常见,但是常见的都是小海蟹或者毛蟹,个小膏薄,而这里用的是台州三门青蟹,硕大,膏丰满滑腻,带着微微的酒香,吃到嘴里浓稠得化不开,似乎嘴巴都要黏上。
而在朝阳门外悠唐新开的松鹤楼则是苏帮菜的传统老店,苏帮菜也是“火星撞地球”的温柔,在松鹤楼流传着乾隆和松鼠鳜鱼的传说,但是我更钟爱这里的响油鳝糊,这道菜的胡椒与蒜末多多益善,最妙的是上桌前浇热油,鳝鱼在盘子里滋滋直响,微微抽搐,这道菜才算完结。浓香,带着胡椒与蒜香,响油鳝糊往往是最下饭的苏帮大菜。
北京虽然说容纳各方美味,但是罕见奥灶面,在松鹤楼我吃到了北京最靠谱的奥灶面,堪比苏州的胥城酒店。奥灶,算是吴地方言,意在“不干净,不清爽”,往往形容心情或者天气。在这碗面里,奥灶形容的是汤。这奥灶面讲究汤头,用青鱼的鳞、鳃、肉及其黏液(据说还包括鱼血)漫溃入味,曲酒解腥,再加葱、姜、冰糖煎煮而成。关键的秘方是投入黄鳝骨,将汤内种种杂质吸附干净。如此一碗好汤,还要讲究碗热、汤热、油热、面热、浇头热,错综复杂的口感容纳在一碗之内,心情未免澎湃。
这里介绍的许多食物与食材都是源于东海,俗话说,福如东海,而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则是“口福如东海”,如此这般,必然会“想瘦比登山难”了。
艺术饭
我的朋友巫昂搬去了宋庄,租了一个大房子,三层楼,有大画室,有大院子可以种菜,顶层有露台可以做“仰望星空状”,能养狗,能养猫,冬天有地暖,工作台有好几个,早上在东边,迎着朝霞,下午在西边,送走晚霞,房租便宜,也就是在城里租个两居室的价钱,还不能是精装的那种。
我去找她玩,顺便观摩一下宋庄的艺术产业,满眼的艺术馆,造型各异的房子,壮观场面快赶上“大跃进”时候的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了。满大街都能见到艺术家模样的人,他们或者光头,或者长发,或者穿着个性,其醒目程度超过一盘宫保鸡丁里的鸡丁,小炒肉里的肉片。
据说常年在此驻扎的各类艺术家诗人有3000人,有人想到这3000人的作品能卖多少钱,我想的是:得有多少餐馆才能满足这3000个挑剔的胃呀。依据我的经验,艺术家扎堆的地方必然是吃货扎堆的地方,艺术家走南闯北,吃吃喝喝,艺术有优劣,吃货无真伪,我寻思着,这群艺术家聚会聊天的主题也无非是:吃喝、挣钱、姑娘……巫昂进庄半年,俨然已经是庄内人了,她知道哪里好吃,哪里蒙事。宋庄虽小,也阶级分明,小堡村相当于富人区,许多有名的艺术家居住在此,对于外地刚来宋庄的新人来说,这里就是“革命圣地”,方力钧、栗宪庭的住处就相当于杨家岭。而在餐馆吃饭,能去米娜餐厅,苹果树下吃大餐喝咖啡的,也已经事业小有成,而刚来的落魄分子,只能和批发画板画布的打工仔混迹在驴肉火烧、桂林米粉处填饱肚子。
米娜餐厅开了不少年了,算是宋庄情调餐厅的元老级别,这里的老板是一对艺术家夫妇,米娜是老板娘的名字,一个简朴的院子,弄得有情有调,有菜地,有竹林,一个玻璃做的大屋顶,阳光可以洒下来。服务员是聋哑人,点菜的时候只需用手指指点点即可,他们都聪明能干。许多造型各异的艺术人士中午来,吃一碗燃面,再悄然远走。这里做川菜,地道的川菜,巫昂和我推荐这里的毛血旺,我觉得孜然焗兔腿更妙,口感筋道,上面洒满花生碎,辣,但是过瘾。麻辣水人参,其实就是泥鳅。在中国的西南片区,做泥鳅是厨师的拿手菜,肥硕的泥鳅,去头,混以仔姜,泡菜,辣椒,再用黄瓜片打底,泥鳅入味,肉质细滑,也可以尝尝里面的姜片,是一种动情的酸辣,有点冲,好吃;打底的黄瓜微微脆,其实我觉得如果在里面再加入一点魔芋也是不错。
好吃,但是总觉得太“宋庄”了。类似“宋庄style”的馆子还有苹果树下,艺术的劲头太足了,有点像放了鸡精的汤,鲜是鲜,吃多了容易口渴。我想找的是那种“给你一下子”的小馆子。
看电影我喜欢看“全片无尿点”的那种,吃小馆子我喜欢吃“菜单可以点一本”的那种,我又偏好重口味,巫昂跟我很对路,马上领着我去了另外一家,叫湘菜香。有点不好找,小馆子旁边都是卖画框画布的小店,算是艺术家们的配套工种。巫昂还在一家装裱店停了一下,原来她是取自己的画。原来这个女诗人、专栏作家、笔迹分析者、心灵鸡汤调配师,现在又多了一个职业——画家。
小馆不大,生意火爆,晚上要是晚来一会儿,排队是注定的。具体来说,这里的菜是湖南浏阳菜,出品貌似粗糙,一份份盛放在瓷碗里,实则锅气十足。北京有太多注重盘式的“瞎讲究菜”,这里的犹如在土地上野蛮生长的植物,带着烟火气。
真的几乎每一道都好吃,简简单单一款煎豆腐,已经灭掉大多数餐厅的豆腐菜,浑然味厚,里面软嫩,吃完这口豆腐,玛丽莲·梦露的豆腐我都不想吃。最妙的是金钱蛋炒拆骨肉,金钱蛋算是湖南乡间的做法,把鸡蛋蒸熟,裹上一点糊,炸至金黄。拆骨肉则是骨头上踢下来的肉,貌似散碎,其实最香。两者合一,几乎平趟宋庄。人说湘女多情,这道菜也如湘女,浓烈、香艳、下酒、下饭。据说宋庄许多餐馆现在都有金钱蛋,毫无疑问,这是溯源地,是宋庄的“庄蛋”。
在“庄蛋”的映衬下,巫昂也显露出吃货本色。她边吃边四处寻找,我问她在找什么。她说在找一个服务员。“是一个臭脸服务员,对客人冷嘲热讽,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每次来都得她拌嘴,几天不见还真想。”
我说,是不是嫁给艺术家了,有的艺术家也属于这种“受型人格”,喜欢这个套路。巫昂怅然说:“没有这个臭脸服务员,我都觉得这顿饭吃的有点寡味。”她说着挑起一片金钱蛋。这勾起了我对臭脸服务员的万千联想:她需要多么粗壮的灵魂,才能绝然面对3000名艺术家,面对5000名打工仔,300名美发学院的学生?我准备过两天再来一次宋庄,不为“庄蛋”,只为“装蒜”。
大嚼西班牙
作为一个资深伪球迷,西班牙足球并不会比西班牙美食更令我心动。我当然会深夜醒来,迷糊着打开电视,看欧洲杯决赛,看西班牙如何4∶0屠杀意大利,可要是有一条上好的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摆在我面前,再有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你叫我把电视机砸了我也心甘情愿。
如果欧洲杯有美食比赛,我最喜欢的两个国家是西班牙与意大利,这刚好也是欧洲杯决赛的两支球队。西班牙美食有着斗牛士版的奔放,过瘾,并且平民,属于高开低走的套路;意大利美食则有一种乡土的随意,他们随便拿点香肠烩蚕豆或者豌豆,做一个辣味的番茄果酱,甚至会拿番茄搭配上鸡蛋,这不就是中国人人会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嘛,我总觉得意大利美食是中国菜流落海外的表妹。
如果西班牙厨师也组织一个世界阵容的队伍,队长肯定不是门卫出身的卡西利亚斯,而是西班牙大厨费兰·阿德里亚,他在场上也将是主力前锋,冲锋陷阵,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