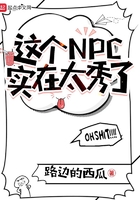急救室的门再度关上,唐珈叶丢了魂似的摇头趔趄着向后退,眼泪断线珠子一样的滚落,悲伤地把脸埋进手臂里,闻到衣袖上的血腥味。
手指紧紧攥成拳头哽咽,慢慢缩到角落里,不敢大声哭,“都是我,都是我,妈说得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他的身体出现状况我这个做妻子的没有第一时间发觉……是我不好……”
“大嫂。”听到唐珈叶自责的声音,温若娴心里也难过,“不是,不能完全怪你,其实我大哥早就有流鼻血的毛病,是他一直隐瞒不说……”
“若若。”立刻传来温母冷冰冰的声音,“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帮着她找理由,你有没有分清楚事情的状况?这个女人最会演戏,是演什么象什么!你别上了她的当!”
现在大叔躺在急救室里,都这种关键时候了,妈还在这里指责你指责他,温若娴实在忍受不了温母无故的尖锐嗓音,“妈,什么上当不上当?大嫂不是这样的人。我说的也全都是事实,易也可以作证。我哥流鼻血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事真的不能怪大嫂,是我哥隐瞒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知道!”
什么?大叔以前就有这流鼻血的老毛病?唐珈叶哆哆嗦嗦,听不真切,但温若娴的话还回响在脑海里,反复放了几遍。
见眼瞒不下去了,温若娴觉得这件事非常严重,索性全说了,“大约在五年前,我哥就经常流鼻血,流得最凶的是大概在四年前,也就是大嫂和我哥闹离婚的那阵子。有一次他把车开撞上了街边的大树,是我刚好路边,然后把我哥送进医院。当时他的情况很不好,坚持要我和易隐瞒不说,那一次他在医院住了好长一阵子……”
唐珈叶呆若木鸡,有什么东西从心尖上划过,泛出无可抑制的疼。如果她的记忆力没有错,那应该是她正式向他提出离婚后发生的事,她被仇恨占据了整颗心,一心想要离婚,摆脱他,于是打出一套组合拳,字字真击他的要害,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面色难看的离开。那之后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不,不是好几天,是二十多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天他出现在别墅,他乞求她,一次次低声下气,可她铁了心要离婚,她看不到他的痛苦、挣扎,看不到他的面孔变成可疑的惨白,只一味地嘲讽他,刺伤他,那时候她就是个疯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听了温若娴的话,她想明白了,原来那二十多天没见他是因为他病了,是被她气病的。
闭了闭眼,胸口犹如被钝刀绞动,唐珈叶恍惚着喃喃,摇头,“我不知道……我真的一点不知道……”
看着唐珈叶如此懊悔,又想想生死未卜躺在手术台上的大哥,温若娴也快要站不住了,摇摇晃晃的身体被简君易从身后搂住,稳了口气困难地说,“真的不怪你,大嫂,你不要太自责,既然你们又重新在一起,这说明无论经历了哪些,你和我哥的心永远爱着对方!有了爱,所有的一切都不算什么,只有爱是永恒的,不管你们身处何方,你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我相信,我哥的心里有你,他会坚持下去,不会轻易放弃。”
唐珈叶浑身发软又瑟瑟发抖,抬起沉重的脑袋,吸了吸鼻子,抹掉脸上的泪水。
若娴说得对,会的,一定会的,大叔一定会从手术台上下来,因为他有牵挂,不管是家庭还是温氏都需要他,他不会那么轻易放弃,他一定会完好无损地从里面出来,一定会的!
等待是煎熬的,也是痛苦的,急救室的红灯整整亮了五个小时,一点没有要灭的意思,眼看着不断有医生从急救室里进出,再不察觉事态的严重可真成了傻瓜。
大叔怎么样了?怎么会这么严重?不就是流鼻血吗?怎么会演变到要急救几个小时?大叔,大叔,你不会有事,你不能有事……唐珈叶啜泣着,她的心有如被架在火上烤。
“医生,医生,他怎么样了……护士,求你告诉我,就告诉我一点好不好……”
每从门里经过一个医护人员,唐珈叶总要这样连求而哭地问,可对方不是摆手,就是摇头,显然是不肯说。
抢救的时间过于漫长,温母和温若娴面露焦急,毕竟体力有限,纷纷支撑不住,在走廊边上的休息椅上坐下来。
温若娴扶着温母坐下,不由抬头向唐珈叶张望,那张白皙精致的小脸上布满了焦灼之色,流泻的黑色微卷长发稍有凌乱地遮掩着额头,唐珈叶还寸步不离地守在急救室门口。
与唐珈叶的坐立难安比起来,她这个做妹妹的也少不到哪里去,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罢,温若娴咽下难受,哽咽着对简君易说,“易,去劝劝大嫂,她这样还没见到我哥自己就先倒下了。”
简君易颌首,紧了紧温若娴的手,随即静静起身走到唐珈叶面前,看了眼急救室的门,“大嫂,不要担心,医生们会尽全力,你这样干耗着也于事无补,不如坐下来保持休力,等他出来你才有精力去照顾。”
他说得很对,不能大叔出来后她反而倒下了,唐珈叶犹豫着点点头,低头跟在简君易身后走过去,在温若娴留好的椅子上坐下。
闭上眼睛垂下头,颤抖的双手放在胸前,不断地祈祷,向上帝,菩萨,甚至向各个信仰的神乞求,求他们救救大叔。
倘若大叔能从急救室里平平安安出来,她愿意用自己二十年的寿命去换,如果觉得不够,甚至可以把她所有的寿命全拿去。
只求能延续大叔的命,他太苦了,真的太苦了,是她不对,是她自私,只管自己,把当年两个人的失败婚姻全部怪罪在他一个人的头上,是她把他气得病倒,是她残忍,只顾自己跳出那段婚姻,完全没有留意到他当时身体的异常与不适。
这时候的时间慢到仿佛是静止的,唐珈叶整个人快要被折磨得疯掉,好象除了干急,除了哭,除了祈祷之外便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假如不是听了温若娴说大叔多年前就有流鼻血的老毛病,她也不会这么慌,隐隐的有个预感在提醒她大叔的身体不象平常看到的那样健康。
那么,大叔为什么要瞒着?
为什么不告诉她?
如果她知道,肯定会一早让他去医治,不会拖到现在。
她怕,真的好怕好怕,她不敢想象没有大叔的日子,不敢想象她以后的人生缺了他会是什么样?
或许……
或许他会就此离开?唐珈叶陡然意识到这一点,急忙把心里这个不应该有的念头挥掉,可越是不想去想,这个念头越是缠着她。
胸口的地方好疼,好疼好疼,她蜷成一团,眼睛里有饱含的热泪,一滴滴地滑落,她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由之前的急促到现在的微弱,面前不断有医护人员走来走去,外面的阳光仿佛照不进这阴森的充满了消毒水的走廊,四周的空气冷得象冰,她感觉到冷,铺天盖地透进骨子里的冷。
她在打抖,在发寒,在哆嗦,她突然在想这可能是梦,对,是梦。大叔长年练拳击,大冬天穿得那么少居然一点不感冒,他的身体那么强壮,所以不可能会突然进急救室,这是梦,这一定是梦。
唐珈叶,你醒醒,你一定是在做梦,你赶紧醒醒,醒来就是大叔温暖的怀抱,他会啄着你的小嘴,宠溺地低笑着说,“小乖,你又做噩梦了。”
是的,噩梦,这是噩梦,唐珈叶你赶紧醒来,赶紧醒来。
啜泣着用力去掐自己的大腿,悲凉地发觉好痛,这种痛在提醒她不是在做梦。
她醒着,大叔在手术台上,这是事实,真的是事实。
就在唐珈叶伤心欲绝的时候,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休息的温母陡然睁开,转头看到哭泣的唐珈叶气不打一处来,不耐烦地瞪起眼,“唐珈叶,你能不能安静点?你这样弄得人心慌慌的知不知道?我儿子没事的人都被你哭出事来,要是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看我怎么收拾你!”
温母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温若娴与简君易对视一眼,实在无语,可又不想看到唐珈叶被温母这样无故指责,温若娴低声劝着,“妈,别说了,算我求你了成吗?我哥在里面一直不出来,大嫂她过于担心而已,又不是有意要把大家的心情弄得不好。”
温家掌上明珠的话对温母来说起到一定的效果,温母冷哼着别开脸,暂时不把矛头对准了唐珈叶。
此时,唐珈叶已经完全不在意温母的责骂,只要大叔能平安,要她怎么样都行,哪怕以后要她天天听婆婆的骂也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与即将要与大叔生死离别比起来,她宁愿时常看婆婆的脸色,就算……看一辈子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