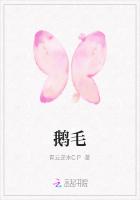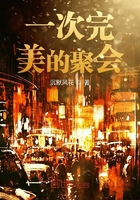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摩根索的理论的区别在于,立论基础已经不再是任何具体的或者抽象的人性为主,而是霍布斯创造的心理感觉说为主;不再单纯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国家间冲突的原因,而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中来寻求冲突的原因和国际秩序与稳定的途径。因此,沃尔兹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或新现实主义理论)。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中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既有人和国家的作用因素,也有国际结构的作用因素;而国际结构的因素是国际政治中基本的、相对持久的作用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应该加以解释的关键。沃尔兹认为政治结构有三个部分:结构的组织原则、单元的能力和单元的功能。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只有两个部分:单元的组织原则是无政府性,单元(国家)能力(权力)分布;由于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功能是相同的,所以在国际体系中可以不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家间相互竞争和冲突根源。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国家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和“安全困境”之中,这样国家间在安全方面处于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状态下,这导致了千百年来世界上战争连绵不绝,此起彼伏。而国际体系中力量分布状况是决定国际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在沃尔兹看来,两极的力量分布是维持世界和平的较好的单元力量分布,两个大国世界权力结构可以相对容易保持力量的平衡。
2.理性主义观
理性主义又称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尽管后者名称不太确切)。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类的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理性能使人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其固有的群体特性,即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且组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在国际政治方面,持理性主义观的思想家一般也认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但他们基于对世界和人类的乐观态度,强调与无政府性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起着或必将起首要作用。
由此他们认为正是这些纽带保证了国际社会的存在,并使之具有和谐性的本质,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采用各种方法(包括经济商业的、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等)发掘人类的潜力和能力,弘扬人类的理性,进行社会改革,增强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加强国际社会的共同规范的作用,以此来促进国际的合作、稳定、安全与和平。
理性主义观是西方国际政治观的主流,它思想渊源可以追朔到中世纪晚期神学家阿奎那。阿奎那试图建立一种把天主教信仰、道德、理性和行为融为一体的政治思想体系。在他看来,体现上帝对人类意志的政治意味着一种道德义务,它借助人的理性,在所有社会活动中谨慎地指导着人的意志;人有上帝赋予的感知善的本能,人的堕落不会使人的理性消失,但会损坏人的意志,政治的深谋远虑在于帮助人们正确地选择实现道德目的即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善的手段,改造人的意志。这种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神学理性主义到了近代被逐步改造成一种世俗的、没有宗教色彩的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理性最为可靠,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即“先天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与之相反,认为知识来源观察与经验,但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的先验自然理性的政治理论相互矛盾。这一矛盾经过边泌和詹姆斯·穆勒的解释被调和起来了,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为认识和行动的基本依据。
作为社会政治的核心概念——理性,在洛克的自由主义和边泌的功利主义思想中已经发生了变化。理性的原意是“具有健全的判断力;明智的、合理的”意思。洛克与边泌的理性概念虽然都与自然法观念联系在一起,但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然法观念来源于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后来经过中世纪的不断变化,到17世纪经过格老秀斯发展,成为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是合理的最根本的规定。它是衡量人的生存、幸福权利和尊重他人的生存与幸福权利以及人的行为的超越时代的尺度。人之所以有理性是因为他认识了自然法、并且按照它来行事。洛克的理性观是建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基础上的。洛克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这时人类是依照理性(对先验的天然代理的认识)生活在一起的。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下所有人依据理性所产生的契约,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所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而边泌完全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达到最大多数人的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惟一目的。这样边泌的理性已经不再像洛克那样抽象了,先验性的了,而是较具体性的,具有平常的世俗理性。
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到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者再到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都是秉承洛克所建立的理性主义传统,视国际社会为洛克式的自然状态,即虽无最高权威,但有理性的交往和共同的规范,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步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性因素。尽管各个理性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对实现这种目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经济手段,有的强调民主制度和舆论的作用,有的重视国际组织约束等等,但从根本上说,是强调理性在国际政治中促进合作与和平的作用。
战后理性主义理论较典型的代表是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和相互依存理论。海德莱·布尔是国际政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作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的秩序研究》。布尔国际社会学说主要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何存在以及如何维持国际秩序。布尔认为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际体系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其存在要求国家间有足够频繁的交往,以至一国的行为可能成为别国对外事务交往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机制的国家群体,由于这些共同因素的存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并非霍布斯式的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类似洛克那种有共同社会纽带和理性规范的自然状态。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础在于国际社会成员在维持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目标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们都需要安全,免受任意的暴力攻击,都期望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使得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有起码的可预料性和连续性,都需要保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共同利益之所以能得以大体维持取决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各国都对上述最基本有相似的认识或解释,即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便于各国间相互交流、理解和合作。
第二,各国间形成了规范国际行为的共同行为的共同规则,并且依靠一些共同机制得到大致的遵守。
相互依存理论是近年来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日趋加强而产生的结果,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以此现象来研究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变化。相互依存理论有各种各样的分支,这里以在西方较有代表性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相互依存理论为例。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两位学者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相互依存的时代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的性质,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研究范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于正在变化的世界政治的现实。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得现实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部分失效,这三种假设是:第一,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武力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有效的政策工具;第三,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其中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军事安全这种“高级政治”支配着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基欧汉和奈认为,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复合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它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各种社会存在着多渠道的联系,这一特点使得国家的内外政策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与外交有关的问题大大增加了;第二,军事安全不再是首要问题,国家间关系中的议题无等级之分,这一局面使得国家没有突出的外交优先考虑的目标,对外政策中出现妥协的可能更大;第三,在越来越多情况下,军事力量的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了或者代价昂贵了,这使得国家的政策手段复杂化。这三个特点产生了与以往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政治过程不同的政治过程。因为控制结果的权力资源有所变化。首先,国家目标将因问题领域而异,跨政府政治使目标难以确定,跨国行为者将追求自己的目标。第二,适用专门领域的权力资源才是最有用的,操纵国际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者将是主要的手段。第三,国际政治的议题受到问题领域中权力资源分配状况的变化、跨国行为者重要性的变化、来自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以及敏感性相互依存增加所导致的政治化的影响。第四,由于武力的失效,强国将难以实行联系的战略,弱国通过国际组织所实行的联系战略将瓦解而不是加强国际等级制度。第五,国际组织将确定议题,促使联盟的建立和作为弱国政治活动的场所,为一问题选择组织论坛和争取支持票的能力,也将成为一种重要资源。由于此,相互依存现实正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基欧汉后来在《霸权之后》一书又进一步论述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加强与改革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3.革命主义观
国际政治本质的革命主义观(由于右翼激进主义的反动性,在此书不对其进行评述)与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想有着极大的联系。一般而言,激进主义是对现存国际社会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是强烈不满的,并且已经不满足于对世界进行渐进式的变革,而倾向于激烈地、即时地对社会进行革命式的改造。因为激进主义者根本反对现存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认为这种体制少有合理之处,倾向于把现存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视为统治者维持其对不合理控制的手段。激进主义者也有强度之分,强烈的激进主义者比温和激进主义者更主张用暴力手段,更快捷的速度进行社会的根本性的变革。这种政治激进主义思想在国际政治上的另一反映就是强调世界主义(univealism)。从世界主义角度把国际政治立足点定为人类社会,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在于超越国家分野的人和人的关系。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信仰或者经过启迪必能成为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上帝选民或者好人,另一边是阻碍人类共同体实现的异教徒或坏人。人有权利,也有责任推翻邪恶的现状。革命主义者往往把自己视为人类普遍利益的惟一代表和正义原则的惟一化身,并致力于实现被现状所压抑、所扭曲的人类共同体。他们不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强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惟一行为者,也不像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是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关注对象,而是强调经过一定标准划分的人类集团或团体,如阶级、革命者或保皇派、上帝意志执行者和异端等等。
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本质就是代表进步的社会集团为了人类更美好的前途或命运反对落后社会集团统治的斗争。
根据英国学者马丁·怀特的划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三次革命主义的浪潮。第一次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第二次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革命运动(主要是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第三次是20世纪的革命运动。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以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其中加尔文的思想不论从神学还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都具有革命主义的色彩。他认为现实世界腐败堕落,必须彻底改造,主张应完全推翻教阶制,建立基于民主共和原则的教会组织;政治上,加尔文强调上帝是万主之王,只有上帝才具有最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必须服从政治统治者,但条件是统治者必须贯彻上帝的意志,否则臣民有天赋的权利与责任来反抗甚至废黜他们。加尔文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尼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加尔文的思想本质上仍然是“君权神授”的翻版,与以后的人民主权论仍有一定的距离。
在16、17世纪之交德意志的加尔文主义者阿尔塔修和后来的洛克的政治契约理论的基础上,卢梭在18世纪后期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和人民革命权的观念。法国革命者继承了卢梭的主张并付诸于实践。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是卢梭学说的忠实信仰者和实践者。在《革命法制和审判》中,他尖锐批判了专制制度和专制法律,要求代之以人民的主权。关于革命权,他认为“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全体人民和一部分人民的最神圣义务就是起义”。他还创立了最高主宰(领袖)的崇拜,以这一宗教形式来宣传自由、正义等信条,力图为共和国提供绝对的道德标准和保持狂热的革命激情。
20世纪革命浪潮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前往的革命主义不同,它不再以道德原则为出发点,而是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来论证旧制度的不合理性与落后性和革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自有成文历史以来,由于经济的原因,社会的组织形态是阶级社会,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是阶级关系,社会(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特征是阶级斗争,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未来是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实现没有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是这一历史使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当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思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