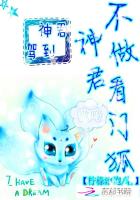1986年,冬,天地间一片枯黄,半空中满是铅云,冷风呼啸.
一个三十来岁的微胖的妇人,用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衣裹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坐在高高的田埂上,对底下荸荠田里挥动铁锹的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骂着!
“刘传陆,你个杀千刀的枯心鬼,虎毒还不食子啊!你连自家的孩儿也下得去毒手,你个挨枪子的,你不得好死!你要长疮生蛆烂死的你,呜!呜~!”
男人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任妇人痛骂,一下又一下用力的掀开泥块,狠狠的从里面抠出荸荠扔在竹筐里!
这两口子结婚十年多了,平日里也少不了磕磕碰碰,却从来没这样红过脸,张达梅为人虽然泼辣些,也没如此恶毒的骂过自家男人,这次事出必有因.
秋上,刘传陆从城里回家,一回来,差点没被儿子刘淇给气死.
先是,刘淇溜进山塘冲的供销社的库房里拿作业本,被人当场给抓住了,被抽了两个大耳刮子不说,还被扭到学校去了,学生们回家一传,全山塘冲的人都晓得了,刘家出了个小偷.
两口子气恼不已,平日里,他要买作业本,家里从来就没少过他一分钱,他还偏偏要去偷,把一屋人的脸都丢尽了,走在村里抬不起头,说不起大话!
当年刘传陆在山塘冲供销社还当过半年多的临时会计,供销社里有哪个不认得他的?可偏偏自家的崽就被供销社的人打得脸上又红又肿,一双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看得叫人心疼,还给他姓刘的一点脸面不?
平日里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汉子,也当了回滚刀肉,腰里面别把柴刀,跑到山塘冲供销社里找贾主任扯皮去了,三句话不投机,他一把将将个圆鼓鼓的贾主任举过头顶上,吓得贾主任苦胆都快破了,脸白得吓人,生怕他一把将自己摔地上,那不得也得半残,好在边上看热闹的七脚八手的拉了下来.
刘传陆拍拍腰间的柴刀道:“说吧,这事怎么了结,不赔医药费,哼哼...”,贾主任没了奈何,自掏腰包出了刘淇的医药费,谁让打人的是他亲外甥。
回到家,把刘淇狠狠收拾了一顿,可心里头还是憋气恼火得很,接下来,更恼火的事在后头,到期末考试完了发通知书,刘传陆两口子一看成绩,气得直翻白眼。在一年级,二年级还是全班前两三名的刘淇,这回滑到班上倒数五名以内了,语文才七十来分,数学成绩更离谱,竟然只有34分,这还不如养头猪来得划算.
对着孩子又是一顿好打,心头上的气是愈加的大了,正赶上两个老人被接到小妹妹家过年去了,没个人看着这闯祸精,他们在田里干活也不放心,如果玩一把火将屋里烧成了一片白地,一家人还不得去讨米呀?下田也把他带上,不准远离视线.
刚开始两天,刘淇老老实实的坐着,时间久点天性好动的他又哪里坐得住,屁股象是有针扎一样,刚吃了两顿好打,不敢跑远,只能无聊的捏泥巴!这一天,他看到田里有一块白色的泥巴,想也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穿着一双新换不久的棉布鞋直直就下到泥糊糊的田里.
“你个小爹爹呢!跑下来搞么鬼,还不快上去!三天不打,你皮痒了是不是??”达姐恨得咬牙切齿,起了高腔,他搞得一身泥糊泥汤的回去,受累的还是她,大冷天的,一盆衣服洗下来,手冻得胡萝卜一样红肿,难过得不得了,本来事就多,哪里有那么多空!
被骂了,慢慢转过身走回田埂上去,眼中满是不舍,没有拿到想要的东西,怎么甘心,一会儿,看父母又弯下腰去翻泥巴,没再留心自己,又悄悄的下了田,掏了一手白泥巴就往回跑.
一而再,再而三被儿子气昏了头的父亲,悖然大怒,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起,暴喝一声,顺手就把手里的铁锹向他甩了过去,中间转了方向,锹把子重重的砸在刘淇的后脑勺上,把他打得晕死了过去,如若铁锹没在空中转那么一下,雪亮的锹口飞过去,只怕是要脑壳落地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开头的一幕.
烈性的达姐抱着刘淇,哭天抹泪骂得刘传陆头都抬不起来,如果真是地下有灵的话,刘家的先人也要被骂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达姐看刘淇的头上只是肿了个鸡蛋大的包,血也没流多少,以为没什么事,只顾痛骂男人,也忘了把他送到医院那去看看,哪想到一记重击,远不止把刘淇打得晕死过去那么简单,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说起了.
达姐温热的眼泪滴在孩子的小脸上,那孩子微微抖动了一下眼皮,却没睁开.
“下雨了吗??”刘淇感到脸上有温温的水珠落下,想要睁开眼睛,眼皮有如千斤之重,怎么也张不开,他微微一抬头,脑袋里“轰”的一下,象是有千万头野牛奔腾而过,天地也在震动,不停的旋转倒置,胃里面翻腾欲呕,却又吐不出来!难受之极!
一个隐约有点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哭腔“***的刘传陆,你娘***..”.
“老头子,他怎么了被人这么骂?”刘淇有点糊迷,刚想到这里,后脑勺尖利的疼了起来,黑暗中一波波的金光如潮水般向他涌来,耳中听得心跳声如擂鼓一样,气也喘不上来了,昏沉沉的睡去了.
昏迷的人是不晓得时间的,不知过了多久,刘淇迷迷糊糊间醒来,感到身上有千斤重,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用力的挣了几下,后脑又是一阵剧痛,张开眼来,黑漆漆的一片!
“人死了就是这副模样吗?”他这样想着,伸手摸去,身上好象是一床又厚又重的棉被,再摸得几下,有衣服,不知是上衣还是裤子,每动一下,后脑就抽动着疼痛起来,一波波的象潮水一样涌来,伴随着阵阵眩晕,他咬牙忍着,又伸出手来四处摸,意识越来越迷糊!
手不知碰到了什么,打翻了,骨碌碌的滚动起来,摔在地上发出一声玻璃的脆响,在宁静的黑夜中很是刺耳,还有一股煤油的臭味,!
“达姐,达姐,六儿醒来了.”男人听到声响惊醒过来,接着传来悉悉索索的穿衣声.
六儿?我不叫六儿很多年了!谁还这么叫我呢?他在几个堂兄弟中排行第六,小名就叫六儿,这本没有什么,可他爹的小名叫山鹿,南平这里六和鹿的读音差不多,先前还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
上了学,有些懂事了,老是有同学架秧起哄,笑他爹是大鹿儿,他是小鹿儿,有时还伸手假做要摸摸他头上不存在的"鹿角",搞得他很没面子,为了这个,不知和人打了多少架,被别家大人上门告了多少状,为了不让家里人再"六儿六儿"的叫,发了好几次脾气,甚至绝食过一顿,这才渐渐的没人叫他六儿,而取而代之是大名刘淇!
“嚓!”火柴点着了,一团火光亮起,迷糊中,一盏煤油伸到床前来,微胖的妇人披着一件棉袄出现在昏黄的灯光里!
“六儿,你还好不?脑壳还疼不疼?”刘淇微张的眼睛看到这张陌生而熟悉的脸庞,心中很安宁,发出低低的声音“娘!我要喝水!”迷迷糊糊的闭上了眼,恍惚间,感觉那妇人抱着他喂了水,温润的水从口中流下去,又沉沉睡去,朦胧间的,听到妇人的低骂和男人的低叹声!
“这个梦做的奇怪,不知是些什么!”刘淇这样想着,睡去了.
耳边有人在轻轻的叫他"六儿,六儿,快起来,起来吃蛋了!”是那个妇人的声音,还伴随着摇晃,
“干什么.”刘淇微张开眼来,一阵眩晕,剌眼的白光里,一个久违了多时的身影,“娘!”刘淇叫了一声,又觉得不对,娘的样子好年轻呀,体形也不对,一点也不胖,不过,后脑传来的一阵阵眩晕让他有一种灵魂要飞起来的感觉,也想不了那么多!
"嗯!乖!快起来吃蛋!要冷了!"达姐拿过一件棉衣对刘淇说“先穿衣,莫感冒了!”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刘淇挣扎着坐了起来,从妇人手里抢过衣服。“这么小,怎么穿?”昏头转向中,也能看出这件衣服明显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穿的,自己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能穿得了嘛.
“先凑合穿两天,过年就买新衣服,我拆了那个挨枪子的一件旧毛衣,正给你织呢!这两天不是没空嘛,过两天织好就有穿的了!”达姐笑骂道:“你也是,长得那么快,几个月衣服就小了,哪能做那么多衣服,下回给你做大些的,穿个两三年的!”
“可这也太小....”刘淇拿着土气的厚棉衣在身上比比,怪了,自己的身体怎么这么小了,两块鼓鼓的胸肌也没了,只有内衣也掩不住的排骨架子,这是做的什么梦?也太真了吧!
反正是在梦里,费话也没用,刘淇痛快的披上棉衣,后脑不可避免的又一抽一抽的痛了起来,他只以为是做梦,也懒得理它.
坐在被窝里,刘淇三口两口把一碗荷包蛋干掉了,意犹示尽的他又呼呼的把一碗加了不少红糖的蛋汤也报销了!
"老娘做的荷包蛋这么美呀!以前怎么没发觉"刘淇暗想着,打个饱嗝,嘴里喷出一股混合着猪油和荷包蛋的香味.
小的时侯家里穷,买盐都得靠鸡屁股,来了贵客、稀客达姐才会煮糖水荷包蛋,刘淇能跟着沾点光,,平日里那是想也不要想.
家里开了餐馆后,大鱼大肉吃了几年,见着加了肥油的菜都发腻,荷包蛋?加了N多红糖,一汤匙猪油,看都不想看一眼,哪里还想吃。后来,考学出了远门,毕业了又一直在外地,想吃老娘做的荷包蛋,不容易了!
这回在梦里,那得要好好吃吃,也不枉了做了这么个梦.
“吃饱了??”达姐笑笑问道!
“嗯哪!”刘淇答道!
“乖!先睡会儿,那个挨枪子的开党员会去了,等他回来,背你到菊珍婶娘那里换药.”达姐说道!
“菊珍婶娘不是死好几年了么?还从哪里来个菊珍婶娘?”刘淇这么想,心里更肯定这是一个梦了,反正这么坐着后脑一阵阵的抽痛,还一阵阵的发晕,也顺从的钻进了温暖的被窝.
后脑一阵阵的疼痛让他想起小时候被父亲一锹把砸得晕死过去的事,他记得很牢,一直以来后脑上都有一条长长的疤痕,总会无意间摸到的,没法不牢,只差一点就要了小命了!
脖子下顶着一个高高的方枕,刘淇无聊的看着帐子顶上被雨水浸出黄渍悠悠想道,“你就是再相信“棍棒出好子,娇养忤逆儿”这一套,也不能把我往死里打呀!”
迷糊间又睡了过去,"梦里也能睡觉,天下少有!”他坠入黑暗的梦乡前最后的一丝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