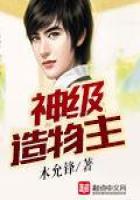还有一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机场内人流熙熙攘攘,拖着拉杆箱的老外,打扮地精致的女人,步履匆忙的男人,还有一些或者白雪般可爱或者颜色各异的小孩子们,大家都在忙什么?为什么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这些看不出身份,看不出国籍,看不过年龄人们,灿烂笑容的背后都有着怎样的人生?或是平淡?或者是诡异?或是精彩?还是像他一样无奈?不过,这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像是被蒙着双眼放到世界的某一角的空间里,命运像是在捉迷藏般得蹦来跳去,谁都看不到它真正的面目。也许大部分都懒得去管顾命运这个硕大得有点夸张的课题,把生活生活成什么样,多数人都不会在乎,好也罢,坏也罢,不至于绝望就好。
边南捷打了个哈欠,浑身觉得酸痛,精神极度萎靡,像一只战斗了一万年的公鸡,终于再无任何力气去蹦跳。胜利或者失败,对于一只疲惫的老公鸡来说,是没有任何诱惑力了的。
范贝金果然是神通广大,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没消几天的时间,就帮边南捷办好了一切手续,只等飞机到点起飞。
这些天来,他们朝夕相处,没有了电话,边南捷仿佛一个空心人一般地。为了防止边南捷会逃跑,范贝金甚至连上厕所,都会在边南捷睡着之后,其实范贝金实在没有必要那么担忧,此刻的边南捷,已经毫无斗志去逃跑了。当然,值得欣喜的是,范贝金很快又恢复了她原来的模样,笑容可掬,一丝不苟,精致体面,像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包装完美的女人一样无懈可击,爱恨情愁,万千心计,都被隐瞒在无限近乎透明的笑容中。
比起那个凶悍恐怖的她,边南捷更愿意看到现在的她,或者说一直的她,那天的对话就像一场恶梦,对,那就是一场恶梦,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欺骗,没有圈套,很多真相,知道不如不知道,蒙昧的快乐大过于清楚的痛苦,快乐当然是难以获得的,为什么要拿好奇来摧毁它呢?
边南捷闭上了眼睛,脑子飞速地转动,他想,就这样——时间拉回去,一切应该是这样的,他去找卫四告别,他们彼此都说了很多伤感的话,但是他始终没有讲出来最重要的一句,也就是:"卫四,你是我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当然,边南捷一定不会讲出这样的话,这些肉麻和感性不属于他这个隐藏高深,无人能懂的复杂的人。他与卫四愉快地告别之后,去见久违的范贝金,范贝金软弱而忧伤地跟他倾诉了这些年来对他的思念,然后她的深情打动了他——对,他应该是这样的,稍微软弱一些,他会被被抛弃的一个女人苦等多年的深情所打动,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熟悉他到如此,能够容忍他到如此,一个人孤苦地去流浪当然不如两个人浪漫地旅行好,因为——他能去哪里?这些年他一无所有,边南捷笑笑,他一直像一直软弱的蚱蜢,自以为可以飞得更高,但是即使是用尽了力气的跳跃,也跳不出方圆那几里地,这便是他的命运,他又该如何向命运去争取些什么呢?于是,这便是故事的最好的结局。
想到这里,边南捷看了机票——他们的目的地是香港。
很意外,也不是很意外。
记得很多年前,范贝金就曾经流露过多次对香港的好感,她每年都会找时间去香港疯狂购物,香港的摩登令她疯狂,她甚至为了将来可以有机会去香港购物而特别报过一个班学习粤语。范贝金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那个学习班没学多久,她便可以自由变换着普通话和粤语了。
香港,多么具有讽刺性的字眼。边南捷连选择自己以后生活的城市的权利都没有。
香港啊,几多悲喜欢几多愁,那样一个复杂的城市,真适合范贝金,那不是偏执的西安,也不是迷乱的郑州,不是敞阔的北京,不是清冷的加拿大。那是一个陌生的,奇异的城市,其实一切如此看来,也不一定有什么不好,至少,一个崭新的城市,会让边南捷有着不同的感受——也许从此他就变成一个简单得像白痴,热爱生活的人来了,过上几年说不定还会有个一子半女,也可能就像自己想象中那样过起了与所有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与四面楚歌之中走到这一步,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想到这里,边南捷觉得有些好笑,他终于可以像阿Q一样了。
他看了看身边的范贝金,竟然也没什么可怨恨的了,是的,这真的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一转头,人群中边南捷看到一个影子,像是毕小桃,但是那面孔——更像是况菲菲!
一想到这个名字,边南捷就像是一下子被打满了气的超人一样,他几乎所有的毛孔都竖立了起来,所有的思想都没有了,是的,所有的被他用阿Q精神安抚好的思想全都没有了。
人群中,他像一只离弦的箭一样向那个模糊的身影跑去,身后是范贝金失控的大吼——
况菲菲,他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她,但是这个名字象一面旗帜一样,飘荡在边南捷苍茫的王国里,他感觉自己是疯了,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力度,他不确定自己冲上去见到的是不是12年前的那个女人,但是这个念头足以令他做最后的一次疯狂。
可是,眼前的况菲菲——就像他很多次的想象一样,即使在人海中看到他,也不见得能够认得出他了。
这真是残忍的现实。但是。这不是他早就预料到的结局吗?
她老了——虽然她的年纪并没有夸张到老的程度,但是她曾经在无数个夜里令他狂想不止的明媚无比的微笑和无懈可击的烂漫去了哪里。时光真像是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握住每个人在这封闭的拳里,当掌心摊开的时候,光景全变了。
于是回忆对于她这样的女人来说,显得尤其珍贵。
她是他这一辈子唯一能控制到他悲喜的人。
而对她来说,他是否仅仅是她流光逝去的见证人?
他真的不想那么庄严,可是他们却彼此贯穿。
可是,她变了,她竟然真的变了,如多年前在阳光底下做的疯狂臆想一样——那时候他是多么喜欢闭着眼睛做一个生活的预言者,虽然他从来把这些放肆的思绪放出来扰乱别人,他只允许那些奇怪的想法在自己的脑子里盘旋来回即可,那时候他做的最多的设想就是,他和她变成了完全陌生的人,一个他不熟悉的陌生人。
就像他几乎已经忘记她是怎么样地与他熟悉起来的。
多么戏剧,本以为再也见不到她的时候,她总会那样从时间的缝隙里跳出,毫无预兆毫无准备。在他无数次的自我告别里。她以恒远的姿态,凝固在他的脑海里。他曾经以为即使沧海泛滥,江湖突变,那也是与她无关的了,她所给予他的,就是那一年初见时候的那一张脸。尽管这些年她一直在改变,变成他渐渐无法接受的模样,他不愿接受的模样。
他并没有料定是否如她一样,就这样的,第一眼就认了出来,隔着那样多的人,那样多的风,那样多的颜色,那样多的感慨。
他站在那里,就连时间,都必须让出一个谦卑的小道,以容他的眼睛直达她的心脏——如此坚持而膨胀的感情为基础,那令人景仰的坚持。令到时光,都不得不退位。尽管它可以篡改他的容颜,却无法挪移他的勇敢。
任何超越极限的事物都势必会得到尊重,感情是不是也能算做一件。
只是,他已经被着疑似孽债的情感纠折了这么多年,甚至飘洋过海都无以躲避。
她有那样的魔力,将他即刻钉在那里,双腿如同被灌了铅水一样地难以跋涉,忘记了行走,直到如水人潮将他推进,他才恍惚地意识到应该退避到某个角落,平息一下自己。
毕竟,她再也不是那一年,面对着他的背影离去,哭得涕泪滂沱的小女生了。
谁还有这样的魔力,让他无论避到何处都无以遁形。
他看着她的影子随着人群渐渐隐去,就好像若干年前,若干次隐去一样地绝望而又充满希望地想: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她的生命里了吧。
他是这样地在意着她,一如既往地,孜孜不倦地。
他转身慢慢地往回家的方向行走,街上仍旧是人流穿往,他抬起头看了看天,却遇到了毒辣的阳光。顿时他的眼睛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他很尴尬而匆忙地低下了头,仿佛怕自己的身体就这样赤裸裸地展览在别人面前一样地。他不愿意别人注意到他,正如他不愿意参与任何人的人生,唯一那一次他愿意参与的她的人生,给了自己如此残酷的结局。
况菲菲啊……
南南"——
边南捷被一阵清脆的叫声喊醒,没有况菲菲,没有位小四,没有许南妮,没有毕小桃,没有时雷,谁都没有,只有自己和那一阵声音里所明确下来的范贝金。
早晨的阳光真好,透过窗户肆意地洒在他身体上,无视床帘的存在。对于其他的人来说,是不是又是美好一天的开始?为什么美好这俩字离自己那么遥远?他慢慢地恢复了意识,睁开了眼睛,却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床,陌生的窗帘,陌生的墙壁,陌生的气息和陌生的温度。
范贝金的笑容移转到了他的眼前,仿佛她一直这样微笑地存在于他的意识之中,从未稍离,从西安,到郑州,从北京再到香港——等一下,这里是香港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什么关系,只要是范贝金喜欢的地方,边南捷都没什么兴趣,她趾高气扬地笼罩着他,以不可一世的姿态控制着他,拖着他的身体和灵魂像她的行李一样飞来飞去,高空上的俯视,云端里的诡异,她不需要解释,更无须说明,所以,对于陌生的环境,边南捷不打算参与任何思维进来,他只想安静地,安静地纯粹的待着,什么也不想,仿佛世界与他从来没有打过交道,而他也一直透明在这熙熙攘攘的嘈杂之中,就如同他几年前看坛经中,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我们应该象世界一样地虚空,是的,虚空,视一切为透明,又无所谓参与到任何的行为中,反正灵魂早已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样想,是不是能够得到一点点偷笑的满足。想到这里,边南捷好像一下子就顿悟了,真正的出逃,并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流离失所,精神上的逃亡,悄然无声,谁都把握不住——边南捷在这样一个平常的早晨突然得到了自由的真正理解。
他总是太投入,无论是什么样场合,他都不合时宜地投入,却在夹缝中妄求拯救和解脱,可是,解脱和拯救,如果仅仅是对灵魂的麻痹和对信念的催绵,那么它总会有醒来的时候。
范贝金喊了一声"南南"后,让自己一丝不苟风度良好地出现在边南捷的面前,跟他说了一些什么话,他一句也没听到,原来只要这样简单,范贝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恍惚和心不在焉,反而对边南捷的平静感到开心,她一定很开心吧,她终于彻底地征服了他,是的,用尽了心计想得到的结果不就是这样吗?
范贝金在开心完了以后,又送上来了热情的香吻,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中间谁都没有出现过,她沉浸在自己精明设置的计谋所取得的成功中,她一定很满意,是的,她要的就是他的全面屈服,她并不在乎他的灵魂跑到哪里去,因为灵魂是唯一不受任何控制的东西,边南捷暗自得意起来。还好有灵魂。
边南捷看着一丝不苟的满意开心的范贝金拎着包满身香气的走出屋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扁扁的烟,对着阳光,他优雅地点着了其中的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这口烟在口腔中无限地蔓延,蔓延,然后吐了出去。
他看着烟雾里的自己,在烟雾的浸淫下失去了形状,又在烟雾的散去中逐渐恢复清晰的轮廓,再接着,他又吸进去一口,蔓延,吐出来,再看着烟雾包围了自己,然后散去,想着这滑稽的人生,忍不住嘿嘿地笑了起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