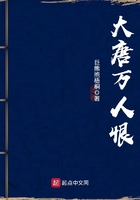对于自己来到定越所造成的影响,江寒也是万万料想不及的。接连几日的朝议,结果还是未作定夺。主和主战两大派相持不下,使得郓王尉无恤也是颇为头疼,结果招了江寒上殿一述,还是没有结果。江寒站在一边看那些朝臣们各抒己见,心下叹服。这种场面在朝余国内他是从未见过的,虽然有些非君非臣,但各自表达的意思反而更为直接了当且个个直逼主题。
尉无恤立在朝中,虽然并非坐在皇位之上,却显得雍容沉稳、隐隐几分霸气。他听着下面的议论,微微蹙起了眉,无奈地看向江寒,正好见江寒也用同样的神色看着他,两人互视一眼,各自都有几分苦笑。
“江大人,既然你是朝余的使臣,那么您认为如果我们按兵不动,天辉帝会给予我国怎样的好处呢?”大司马刘南问道。
江寒本是在走神,乍见风头转到了自己身上,还不由吓了一跳。他忙整了整神,答道:“皇上有言,只要定越国不出兵,待康梁攻打下来后,便割据一般的领土给定越国。”他笑容可据,但笑得连他本人都觉得假。刘南早知他会这样说,又问道:“割地不假,但朝余灭康后野心未灭又该当如何?这时候定越没有康梁挡在中间,便是需要和朝余正面相迎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场的贤人自然都想得通明,江寒心里佩服,表面上故意换上了一副为难的神色:“在下也只能说,我国确有诚意,至于贵国究竟作何决定,在下便不好多插口了。”虽然他是奉旨前来,但毕竟穆如是的命还捏在赵太后的手上,朝余和他非亲非故,他才懒得多耗口舌,倒不如让他们直接否决,让他带消息回去的好。这样一来,大不了是挨容辉的一顿骂,之后还是皆大欢喜的局面。自从赵太后和他亲近,容辉给他脸色看已经是常有的事,不知不觉他在那位皇帝面前时脸皮也渐渐厚了起来,江寒自己也有察觉,对此只能汗颜。
没见过比江寒还要“不善辞令”的使臣,周围的一些官员都换上了一抹鄙夷的神色,之后的讨论也只局限于内部,就仿若没有这个人存在一般。只有孙陆等几个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暗暗地看了他几眼。
乘无人注意,孙陆都到了江寒身边,问道:“江大人,恕老夫直言,现在单以朝余国的情形来看,似乎并不叫人满意。听闻大人精通玄门之术,选择在朝余为官,可是有何缘由?”江寒谦虚道:“说来惭愧,在下只不过是个江湖算命的,承蒙皇上厚爱,才得以入仕。”孙陆奇道:“难道不是因为当初突变的星相之中有何暗示吗?”
江寒偷眼看了看他。余光瞥过,但见尉无恤不时地正关注着这里,而一边杨蒙老奸巨猾的视线也一晃一晃地掠过他的身上。怎么之前不觉得自己在如此受人瞩目呢?江寒无奈地一扯嘴角,客套道:“那日在下睡得过早,结果漏看了那星相,后来听到传闻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在下的玄学,说起来也只够混口饭吃啊,既然看不透未来局势的发展,当然是混哪是哪,走一步算一步了。”
孙陆瞅了他半晌,笑眯眯道:“如此说来,江大人似乎对效忠哪位主上并不上心啊?”江寒看到那种笑就很是郁闷,更何况孙陆话中带话,有拉拢只意,恐怕是受了尉无恤的指使。他故意淡淡道:“孙大人是国之栋梁,当然有权选择主上,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自然是哪可以混日子就混哪。”其实自从朝余进入备战状态,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溜人的打算,他当然知道未来天下的发展,可是定越虽好,却有杨蒙在,并非他可以久留的地方,只是如果能借用一下他们之力来让他摆脱朝余,他还是很乐意的。
听出江寒话中之意,孙陆心下一喜,道:“不知江大人认为定越国该当如何?”
看了眼依众朝臣,江寒赞道:“定越国人杰地灵,能人异士辈出,实在是一富庶之地。”这句话可是由衷的,孙陆听出其中的真切,笑眯眯道:“看来江大人对定越还是颇为欢喜的,但愿有朝一日可以同朝为官。”这番话总算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江寒笑笑,却不再答话。
最后的结果在江寒预料之中,定越表达了同朝余的友好之情,却在军事问题上提议以和为贵。这就等同于表面上送了捧鲜花,实则手里拿了把刀子随时准备迎击。江寒在定越国的处境便显得有些尴尬。
看来是时候回去了。江寒伸了个懒腰,在一片明媚的阳光下感觉心情大好。虽然受足了白眼,不过到底可以换得个穆如是的安全。江寒一面走着一面估摸着回朝余后怎么样可以摆脱阻挠离开,完全没有留意到迎面而来的马车。
垂帘精修,檐木雕琢,悬几条翡翠明铛,拉车之马也是上好的良驹。车夫催促下一路疾驰,本来和江寒擦肩而过,在刚驰过几十米处又停了下来。江寒没有在意,本待顾自走去,只听有人叫了他一声“江先生”。这一句语调温婉,有几分夜莺呢喃之感。江寒回头看去,正好车上之人拉起了帘子,两人视线一触,江寒不由惊讶:“杨小姐?”
杨宛如邀了江寒上车,江寒本想推托,但看她神色坚决,预感似乎有什么事,他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车棚较为宽敞,但里面只有二人,互对而坐,就多少有几分暧mei和尴尬了。上次见杨宛如时,她在众人簇拥下,江寒并未看清。此时面对面坐了,只见她穿了身素色轻纱衫衣,粉黛轻施,双唇却朱艳欲出。虽然素丽但很好地显露了她雍容典雅之态,给人远观而不可亵玩之感。
一直无人说话,江寒尴尬地轻咳了两声,问道:“在下唐突,不知杨小姐找在下可有何事?”
看着眼前这个样貌清秀的书生,杨宛如有些羞涩地垂下了眼,声音却异常清晰:“上次见过先生之才,宛如心下已有敬意,本也想多留先生几日切磋学识,只是——还请先生早日离开定越为妙。”
江寒奇道:“早日离开?杨小姐何以这么说?”
杨宛如看了他一眼,道:“不知先生是否替使馆改了风水?”
江寒闻言有了些猜测,继续问道:“小姐怎会知道?在下所学本就是批命看相之术,既然与己有克,自然是需要做些修整的。”
杨宛如有万般话语,却是一时问不出,只能苦笑道:“家父怀疑先生是宛如一位故人,恐怕会暗中采取一些行动。”
江寒一愣:“故人?”
杨宛如回忆起儿时之事,微微一笑:“是的。是曾经我背着父亲偷跑出去所结识的一位哥哥,如果他仍活着,才学定当不输先生才是。他是神相江家的传人,只可惜,江家却遭了灭门……”她言语间有种眷恋和寂寞,却凝了眸子一瞬不动地看着江寒。
江寒没想到杨宛如竟然是自己小时认识的那个女孩,也被唬了一跳,但表面上只能故作惊讶道:“神相江家?在下的确是姓江,可以此便做了断定,不觉有些草率吗?不知杨丞相和江家,又有过什么过节?”
杨宛如看不出什么破绽,略有失望地摇头道:“这个先生就不便知道了,如果不希望见血光,还是乘早离开吧。”
待车到达使馆,江寒向杨宛如道了谢后便立刻让候在那的江乾几人收拾行囊。一辆马车悄无声息地渐渐消失在岳阳古道的滚滚尘土间,待不久后的一队士兵匆匆赶来,所谓的朝余使臣一行早已没了去向。
江寒在马车上一路颠簸,看着窗外微微出神。若要追溯起来,他同杨宛如相识那年,他才九岁,而她则仅七岁。那时他只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意思,明明只是那么小的年纪,说起话来却是一套一套的,而且很不认输,几乎每次来找他都喜欢出稀奇古怪的对联来刁难他,结果他对答如流,反而惹得她自己气得直瞪眼。但时间只持续了一年,江家便受杨蒙迫害而惨遭灭门。
如果那时知道她就是杨蒙的女儿杨宛如,自己会不会干脆挟持了她要挟杨蒙不要轻举妄动呢?江寒笑着摇了摇头,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函,打开翻看。信函是他上朝时柳莫拖江离转交他的。最近江离为了医治他的心病而从了柳莫学医,而柳莫倒是没了什么消息。看了这封信后江寒才知道他最近都在忙什么,将信收入怀中,他看着外面的浮云微微笑了笑——看来,又要变一次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