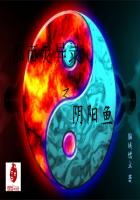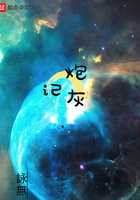我是被风刮醒的,睁开双眼时,一轮圆月当在沟谷之上。
借着月光,我看到被压在野猪身下的赵济宁,他的腿完全被野猪的尸体覆盖,这当头竟然还没醒,恐怕凶多吉少。
我揉揉后脑勺,整理一下头绪,赵济宁先前是被控制了才死掐我的脖子,就在快要把我掐死时,那头野猪冲了出来,撞上了赵济宁我才得以解脱,野猪这东西家猪比不得,性格猛烈,虽说同类是憨厚迟钝的猪,但其骨子里却透着灵性,加之猛烈的撞击,便把控制赵济宁的脏东西给撞出体外了,而且应该被这次撞击给消灭了,不然我现在怎么可能还活着。
现在是得了一时的安宁,可赵济宁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我现在虽然醒了,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并且稍微碰到脖子都会有一种痛感。
我离赵济宁和野猪其实没有一米,可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爬到野猪尸体旁,我试图把野猪尸体从赵济宁腿上推开,,可是试了几次,愣是丝毫没动,反而使自己更加劳累,全身的酸痛接踵而至,这当头肚子也叫了起来。
我索性抓起那把斧头,饥饿的我开始舔食斧头上的血迹,只是那猪血早已凝固,愈发舔的生涩,但心里却多了份馋意,竟有了写力气,于是没过多久,我就用斧头从野猪脖颈处砍了一块肉下来,直接生吃了。
在进行了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一次野蛮行径——茹毛饮血之后,我逐渐恢复了气力,于是去找了根较长的树枝和一块石头弄了个简易杠杆把野猪尸体从赵济宁大腿上撬到一边。
野猪尸体被撬起后,赵济宁的上半身一下直了起来,然后又躺到了,接着开始大口的喘粗气,我连忙上前为他顺气。好半天,赵济宁终于开口了,只是语言有些含糊不清。“我……我的腿……腿……”他说。
我这才注意到赵济宁那被压得变形的腿,这双腿被那野猪压得血液流转不周,并且时间很长,恐怕保不住了,我更是不敢去动他的腿,万一再弄出个好歹来可就不好办了,当务之急就是走出山林,赵济宁的伤势必须马上得到治疗,毕竟那头野猪冲出来有没有把赵济宁其他部位撞出问题都还不知道。
我把赵济宁扶到沟谷斜坡边的一颗树旁靠着,又在旁边生了架火,赵济宁逐渐清醒过来,他告诉我,他的双腿已经没了知觉,并且腰部很痛。
我烤了点野猪肉给赵济宁吃,没想到他见我如此这般竟然哭了,还撂下句话:“别管我了,你自己走吧!”这话听着倒是慷慨,可赵济宁被我骂了一番,他现在要无私了,可他把我带进这处境之前有没有为我想过,现在无私有什么用!
赵济宁被我的话触碰到了心底敏感的地方,决心和一同进退。我其实不怕什么累赘,如若老天真要把我命拿去,那还不是迟早的事。
如今已没有心思去寻思是哪个狗娘养的在这里设下的迷人的套,本来是给死者砍树来的,如今倒好,自己都快成死者了!
赵济宁在我的劝导下吃了些猪肉,我去沟谷里的水潭里弄了点水给他喝,自始至终我都没提他被控制险些把我掐死的人,叫他知道了,还不又向我展现他那变态的愧疚。
这一晚,过得很快,我把已经破损的外衣给赵济宁盖着,然后自己就在火堆旁蹲着睡了一夜,其实真心太累了,纵然是再来个牛鬼蛇神要取我性命我也管它了,真心累垮了。
很茫然,连做了个什么梦都记不清了,只知道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赵济宁的右脚当在我脸上,我特么竟还有这邪癖!
我和赵济宁分食了点猪肉就踏上了出林之行,准确的说是我踏上出林之行,而赵济宁被我背着。
我没有往来的路回去,只是往沟谷的那一头行进,因为按原路返回是那片密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从那里走出去。
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我竟背着赵济宁一路未歇,直到看见行进的路上出现了人的脚印,我们在那歇下了,之后发现了上山挖药的人,才终于放下心里,这出来后的一切未免太过顺利,让我不敢相信自己和赵济宁是不是真的走了出去。
采药的人把我俩带到了他们村子里,一问地名,竟然和赵大龙家所在的村子隔了三座山,之后我叫人把赵济宁给送到了镇上的医院,我自己则赶往赵大龙家所在的村子,也不知,这赵大龙的丧事怎样。
当我又回到那个村子时,已是第四天的事了,村里人都惊呆了,我这个从后山失踪的人突然从村口冒了出来,难免不会惊讶。
我向赵家人说了赵济宁所在的医院,他们也叫人去那照看,我把这两天发生的事向师傅道了个一干二净,他只丢给我一个字:命!我则苦笑,我本不信命的,走到哪算哪,读书时逍遥自在根本没想过今天的处境,当初跟了师傅只是想换个地方混吃等死,没曾想从第一次和师傅出活开始每一次几乎都与死亡擦边,那所谓的混吃等死也终于在我这淡然,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对未来的路更加迷茫了。
赵家人不相信是赵济宁把我带入了困境,以为是我这个外地人的拖累才导致了失踪,经赵济宁亲口证实,赵家人才改变了看我的观念。
师傅说村子里组织人上山寻找我和赵济宁,折腾了两一夜,我其实有些愕然,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当我们摆脱了困境时他们岂不是还在找我们。
虽然这期间出了我和赵济宁失踪的事,但丧事还是照常进行,赵大龙在我们被定为失踪第二天就送上了山。
和师傅回家之后睡的第三个安稳觉,第一个梦到的竟然是赵大龙!还有赵济宁我也梦到了,可在我的梦里赵济宁和赵大龙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并且是一个表情,他俩都冲着我笑,那种感觉,好像是我欠他俩什么,最后赵济宁冲我招了招手。
那是回师傅家后的第四天,门又被敲响了,来人面熟,仔细一望,是那天一道上山之后分道的小伙子之一,他也是赵家人,我问他怎么了,他面色急躁,“济宁,济宁没了!”
“什么济宁?”
只见这健壮的后生眼眶里留下一行浊泪,他说:“就是和你在山里迷路的那个济宁,赵济宁,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