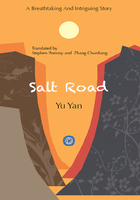我要见张家老大,这时他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身陷绝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苦无援,身无分文的我即使想回重庆也无可能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天晚上,张家办了几桌酒席,我和张旺财就算正式结婚了。后来才知道,因为贫穷,当地的姑娘大多嫁往外地,使这里男多女少,男人娶媳妇要送女方很大一笔聘礼,很多男人因此娶不上女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到南方贫困地区去骗女孩子甚至拐卖女孩子。几年后,一个四川省巫山县的女孩才16岁也被骗来这里。她长得非常清秀,常到我家玩。她想念父母多次闹着要回家,她男人把她看管得很严,走哪儿都有人跟着,直到她怀孕七个月后才稍稍放松看管。有一天她悄悄找到我,哭着要回老家。我给了她200元钱作路费,让她跑了,至今她男人都不知道是我把她送走的。
第二年初我就为张家生了一个儿子。临产时,没钱上医院,就请农村的接生婆接生。她竟然将手伸进产道将胎儿硬拉出来,造成我的宫颈撕裂,流了大量的血,差点死去。孩子出来后,按照当地的习惯做法,用高粱秆皮割断脐带。
张家见我为他们生了个儿子,非常高兴,尽量让我吃好有充足的奶水喂孩子。
此后几年,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七年间就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还人工流产两次。张旺财和北方其他汉子一样,身体强壮,性欲亢奋。尽管白天庄稼活很累,可到了夜晚他在床上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没完没了地折磨我。
我不堪忍受,偷偷跑到公社卫生所安节育环,可还是怀孕。后来医生检查后告诉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宫颈撕裂伤口恢复不好,宫颈口已变得嘴巴一样宽,根本安不稳,环是什么时候掉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几顿白面,其余时间就只能吃红苕。他们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然后磨成粉,吃的时候再加水调成面团,用手拍成饼或蒸或烙,就着缺盐少油的菜汤吞下肚完事,没有一颗大米吃。我真怀念老家的生活,那里有亲人,有白米饭,尽管也吃不饱。
但就是这样的苦日子老天爷也不让我平静度过。1999年底,我带四个孩子第一次回重庆探亲,张旺财和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勾搭上了,那女人竟然住进了我家。我探亲返回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事,气得差一点儿发疯。我为他付出了一生,他竟然这样回报我。我绝望中想吞农药自杀,是孩子们哀哭着劝阻了我。我向张旺财提出离婚,他坚决不同意,孩子们也苦苦哀求我,但我实在不愿意再延续这个噩梦。抗争几年后,张旺财终于让步了。
2006年5月,我孑然一身回到久别的重庆,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身患重病,大哥和弟妹们都已各自安家,境况也不大如意。
我离开重庆时是一个青春少女,现在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且一身伤病,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
我租了一间屋安身,撑着有病的身体去找工作。我当过清洁工,做过保姆,给药房守过夜,每月靠几百元工资养活自己。我不好意思去见过去的同学,他们也没人能认出我,我只想默默无闻地打发掉人生剩下的日子。
空闲的时候,我爱独自一人坐在三峡广场的石凳上,打量从身边走过的一对对欢乐的少男少女,从他们阳光般的笑脸上追忆我失去的青春年华。我真羡慕他们能自由恋爱,只要心心相印,而不会计较对方是什么家庭出身。他们升学、就业可以自由选择,再也没有人去追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辈曾经做过什么了。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啊!不知他们意识到这种幸福没有……听着玉英的讲述,我和妻子早已泪流满面。
高尔基曾说:人生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玉英因轻信别人而对婚姻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由此酿成了一生的悲剧。可这能全怪她吗?对别人而言,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而玉英做了一生的噩梦,她能醒吗?谁能回答她?
注:应文中女主人公要求,李玉英系化名。另鉴于隐私权方面的考虑,作者也用了笔名。
风垭林场四知妹
李忠公
我们邻水县风垭公社林场在达县地区的社办场中,恐怕要算规模最小的林场之一了。我们林场只有七个男知青、四个女知青。四个“知妹”下乡时都正值豆蔻年华,每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名字:韦素珍、向玲、洪忠萍、祝玉辉。她们的文化层次从初小、高小、初中直到高中。其中,韦素珍、向玲下乡时刚满15岁,洪忠萍才16岁,这三个小知妹年纪虽小,却都有着辛酸的童年。
个子瘦小的韦素珍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了高小就辍学在家,没有出路便报名下了乡。那时,她在我的眼里,还是一个未曾发育的小女孩儿,身体十分单薄,衣着十分简陋。
向玲比韦素珍高出一个帽帽,一双大黑眼睛忽闪忽闪,笑起来娃娃脸上挂着一对好看的小酒窝。几个“知妹”当中就数她的问题多,空闲时经常拿着一本书找我问这问那。
她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死得早,继父是重庆惠工机床厂的工人。她家里住宿条件差,一家人(父母、她和弟妹)挤在狭小的两间小屋里,生活极其困难。看着渐渐长大的女儿,继父居然起了歹心,母亲不得不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女儿,生怕她受到一点伤害。为此,向玲小学刚毕业便毅然决然地去了农村,发誓一辈子再也不跨进这家门。
“知妹”洪忠萍父亲是地主,新中国成立时被镇压,母亲把才学会走路的女儿从农村拖带到了城市。为了生存,母亲嫁给了重庆市第十七中学(原东方中学和辅仁中学合并的学校)老师洪传权。不幸母亲病逝,好在继父一直很喜欢她。后来继父认识了一个小学教师,成家后她们三个人的小家过着甜蜜的生活。洪老师是学美术的,当时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1957年,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收二十多名学生,一千多名考生中,十七中就考上了七个,我哥班考上四个,我家就考上三个(两个哥和五嫂),真是师高弟子强。然而灾难不期而至:1958年那年,洪老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抓去劳动改造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得以昭雪回到十七中学颐养天年),可怜的小忠萍又一次失去父爱。
后妈与继父离了婚,搬出十七中学的教师宿舍,住回了她小学的宿舍。几年后,后妈又同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学生结了婚。忠萍眼看就要中学毕业了,那个新家狭窄的空间哪里还能容下她安身?新的家庭关系、比自己年长不了几岁的男性长辈使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产生反感和恐惧。于是她常常在同学家里借住,巴望着中学毕业后考上高中,可以去住校继续她的学业。可是,幸运之星没来叩响她人生的大门,严酷的阶级路线让她落榜了。她需要尽快有一个安身之处,然而重庆这么大的城市,却没有她安身的地方。
到农村去──那里是广阔天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吃的,有住的──动员她上山下乡的人如是说,她便真下了乡。
我们乘坐着解放牌大卡车从重庆被装运到邻水,从九龙区到风垭公社天天受到夹道欢迎,天天受到宴请,不谙世事的知哥知妹们几天来一直处在亢奋情绪中。场长来公社迎接我们,有贫下中农送我们进山,我们打着甩手上了路。走进了荒凉的深山沟,转过两道大弯弯,爬过一匹光梁梁,走过两根窄田坎,沿山涧小溪边山道而上,跨过一壁乱石崖,眼前突兀见一土屋。屋后是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大山,屋前涓涓小溪水潺潺,溪上横躺着用松树棒棒捆成的只能一人经过的小桥。来公社接我们的场长笑道:“林场到了。”我们众知青的心,从离开公社那一刻起,跟着自己的脚步,一步比一步沉重,一步比一步紧缩,一步比一步寒冷。大家屏住了呼吸,没有谁说一句话,此时此刻,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
两间土屋加旁边一抹水的矮房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扎根一辈子的林场吗?房边小坝子上东歪西倒立着几个农村青年,面无表情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们看。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杨长路的胖罗汉,坛子似的肥肚顶开了邋遢破衫。另一个是生着一双金鱼眼,穿着一条短到“连二杆”的刷把裤叫叶四的人。几个小知妹不停地问:“这就是我们林场啊?”
“这啷个住得下恁多人?”这和想象中的林场完全是两码事,找不到一棵参天大树,看不到一片像样的松树林。我和她们一样,那一刻真是从头顶一直凉到了脚板心。
大家放下被盖卷和各自携带的东西,就赶忙“参观”我们共同的家了。
左边一间七柱房是男生寝室,门坎几乎平膝盖那么高,没开窗,无天花板。因为墙上只安了几根楼杄,没有楼板,仅有几片玻璃瓦透下几束日光照亮全屋。进门两边对排三架小木床,最里边安放一架,正好安顿我们七个知哥。
中间同样大小的屋用木板隔为两小间,前宽后窄,前后各开一扇门;后间上面铺了木板做楼,边墙矮得只有大半人高,从前屋有木梯上下。
右边一抹水的侧屋就是厨房了,里面做了一个石面的泥灶,上面安放着一口海锅,锅边生有锈,底部那一块黑里泛着光。这是用来给我们煮饭和煮猪食用的。
最恼火的是没有看到一个可以遮风蔽雨的厕所。我们问场长,他说接着就和猪圈一起修。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男生还好,急了还可以找个僻静角落方便,知妹们呢?场长说:好办好办,临时挖个凼凼、搭个棚棚不就解决了么?克服克服嘛。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哭笑不得!几个小知妹哇哇地叫起来:“早晓得是恁个样子该不来了!”
女生寝室被安排在后面那间小地屋。小知妹们的问题最多,向玲嘟着嘴说:“这屋天上墙上到处都是洞洞眼眼的,地下又潮湿得流水,咋个睡嘛?”几个知妹都不愿打开铺盖卷。还是大姐姐祝玉辉安慰她们说:“算了算了,来都来了,将将就就嘛,反正我们都带有蚊帐,那些缝缝叫场长派人糊一下就好了嘛!”四架小木床首尾相连安放到四墙边,祝玉辉只好睡靠隔墙那架床,向玲早准备好“抢”到了进门边那架床,就这样她们便安顿了下来。
知青们从城市真正来到荒山野岭,来到这两边是高山的“夹皮沟”,实实在在地摆在大家眼前的那幅生来还未见过的原始蒙昧景象,犹如当头一棒,让我们如坠五里云雾一样,不禁为前程担忧起来。只有我的几个小知妹,一阵想家哭闹之后,不久就笑逐颜开,让那“夹皮沟”里也溅出了清脆的欢声笑语。
光阴慢慢地在山沟里消磨,无可奈何之中,知青们烦躁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场管会建立了,团支部也建立起来协助场长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公社安排我当副场长,祝玉辉担任团支部书记。
到林场没几个月,场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让知青们都很气愤。
一天,我正在小溪边洗衣服,小知妹向玲从小晒坝朝我走过来,气冲冲的样子,“呃,给你说个事。”她嘟着嘴说。“又有啥事嘛!”她听出我有点不耐烦的口气,“好,不找你说,我们是小学生!”她赌气转身就想走,我连忙站起来,甩着滴水的手:“哟,脾气还不小,过来过来!”
我平时都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又没有多少龙门阵可摆,今天的样子恐怕是有点正事。
“你是副场长,领导噻,不跟你说又跟哪个说嘛!”
“废话少说,啥事?”
“我们那个寝室,”她回头看了看,“一点都不方便,烦死了!”
“呃,有啥事直说嘛!绕弯子做啥子。”我有点不耐烦。
“着啥子急,衣服我给你洗都要得。听我说嘛,我们那个楼板,恁宽的缝缝,楼上的老场员啥子都看得到,换件衣服都要躲到帐子里。”她低眉回首,似乎难以启齿。
此时,我才掂量到事情的分量。一阵沉默,我把视线移开,抬望眼,屋后小松林上的山岩,竟变成了怪石嵯峨,心情不可名状。
“你给祝玉辉讲过没有?”我沉思着低声问道。
“她都住在里面,啷个不晓得!跟她讲也没得用。”她抬起头来,望着我,面露愠色:
“昨天中午放了活路,我进屋正换衣服,刚把外衫脱了,无意间抬头一望,把我吓惨了!”
口齿伶俐的她,话语急切愤然。
“那个楼板缝缝里头露出两个黑眼睛,鼓起把我瞪着,发出两道凶光!我差点叫起来了,赶忙钻进了帐子里头,心怦怦直跳。”
我心沉重起来,为先前冷漠的态度而歉疚,为同命的知妹们徒生悲悯。面临险恶的环境,男子汉可以胆壮无畏;对女孩子来说,尤其是太稚嫩的她们身处危惧之中而无法自卫,突如其来的恐惧对敏感的向玲来说,无法承受,她来找我,显然是在寻求帮助。从她那求助的凄切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道义。“看清楚没有,像哪个?”“肯定是叶四!那双鼓眼睛烧成灰我都认得到!流氓!”她愤愤然,“还有那个杨长路,他两个经常故意大声讲些下流话让我们听,气死人了!”
“这事你不要到处讲了,又没有证据,他死不认账,把他也没法。”我再三叮嘱她说,我会找祝玉辉,找场长商量,向公社反映,要她们自己多加小心。
我找祝玉辉谈及此事。
“对头,背时的叶四和杨长路说些话牛都踩不烂,是气人。场长还不是听到的,有啥办法嘛!”她不急不躁,不瘟不火,甚至不会发脾气。但她能分清是非,天性善良。眼睛近视的她的确没看见,甚至连想也没想过她们头上那些粗俗原始的野性的欲火。
“啷个不把墙用报纸糊一下嘛!”我用责怪的口吻说。“糊了的,还是昌广宪(会计、本地场员)专门糊的,时间长了就飞起来了,手一顶就掉下来了。那两个家伙硬是怪,他要偷看有啥法,看得到,摸不到,他又犯得到好大一个法嘛。”
“向玲也爱吵,杨长路说下流话,你莫搭白就算了。”她平静而漠然地说。
我对场长讲起此事,他无可奈何:“农村人是恁个爱讲怪话,不理他就算了。”
我把此事和男知青们说了,大家愤愤然:“龟儿子叶四是个烂杂菜,找时间修理他!”
陈昌吾说:“叶四那家伙坏,我亲眼看见他在屋背后山坡上脱了裤儿耍他那个鸡巴,还经常在女生面前说骚话,是该修理修理才行!”
杨、叶二人,本是农村的孤儿,是世上最可怜的孩子。他们房无一间,衣无二件;没有父母的照顾和疼爱,没有家庭的管束和教育,从小放任自流养成一身恶习。安置到林场来与知青为伍,真是苦了我们的知妹啊!
一天,我看见叶四,给他一点警告:“叶四,过来!”他当着我们男生面装人样:“啥子嘛。”“你少在女生面前说怪话!你是不是在楼上偷看女生换衣服?”“没有,没有,哪里是偷看嘛,恁大的缝缝哪个都看得到。”他嬉皮笑脸不以为然地说。“你少打坏主意,谨防我们男生捶你!”“不敢,不敢,晓得你们知青受法律保护。”他竟装起乖来。这样一个瘪三,实在无法跟他讲道理。
我们还向公社管林场的陈书记反映了此事。有次陈书记来林场,知哥知妹们众口一词地给书记再次反映了女生寝室的事情。他认为是个问题,说等把女生寝室分开就好了。但他又说,眼前场里没有钱再修一间屋,只有过段时间再说。
于是,我们照旧在默然中打发沉闷的日子,而叶四和杨成路他们或偷鸡摸狗,或明目张胆地继续宣泄他们的欲火。
一天,我从老场员门前过,听到向玲在骂人:“看,看啥子,回去看你屋妈!咒死你个龟孙子!看看看,看瞎你那双狗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