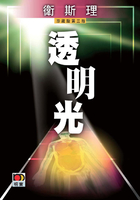水母潮很快过去了,也就八九天。听说普通水母的一生,不过就二十多天,而这八九天,本该是它们人生中最明亮的时期,从幽暗的海底或礁石那里出来,浮上水面,虽然有一部分落入我们的网中,但总还有许多,它们逃脱了,作为一只完整的水母过完短暂的一生,到最后,是安静地在海底化为海泥呢,还是被潮头带上来死在沙滩、泥涂或鹅卵石上,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总比三矾后又被碎尸万段的好。要是奶奶还在,她又要笑我了:小孩儿家家,知道啥死啊活啊的,听话,以后不许说了!
可怎么会不知道呢?奶奶,死了,爷爷,死了,隔一阵子,村里就有人死,死这事,近近地在身边啊。年老了的死是没办法的,年轻些的死在海上,也是没办法的,生病死的,也是没有办法,这些,都是我眼睁睁看着无法可想的事。好多老人,活到七老八十,到死了都没离开这岛半步,有一个婆婆,她愣是没出过村呢。这样,也是一生啊。我的一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摇橹的时候,我也在做白日梦,梦里,我到了外面的世界上,越长越高,高到半天上,又垂下头来看现在的我——我和我,在海天之间,温柔对望。
我能把橹摇得像点样子了,至于水母,每天看,竟觉得它们本该就在我们生活里一样,它那只有一副腔肠的身体,好像也是那么理所当然。阿虹是清林老师的干女儿,这个,好像也已经理所当然了。阿虹有了三四条连衣裙,淡粉淡蓝乳白米黄,她走到风中,太阳照着她鼓荡的裙摆,就是一只半透明的水母。大人们已经在预言,阿虹的未来必定是好的。那些预言家说,你看,她本就成绩好,可是家里被她爸爸的病拖穷了,现在好了,有了这样的干爹,不用愁学费了;这孩子啊,本就是会看眉高眼低的,这样八面玲珑,将来能不好吗?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前说时,我们总会挂上一副木然的表情。东山嘴的阿权叔就是预言家之一,有一回,他对着我们木乎乎的表情说:“看看你们俩这骄傲劲!我倒要看看,你们以后到底有多大出息!一个那么瘦来一个那么胖,也不知道能不能找个好婆家呢!”我真想朝他那阔嘴来上一拳。林英却不恼,她笑着说:“只要阿权叔你长命百岁,总看得到的。万一活不长,那就可惜了。”阿权叔笑了,说:“尖牙利齿的,将来当律师。”林英只当没听见,拉着我走得飞快,走得离开人群老远了,她才停下来恨声说:“我们靠我们自己,让他们看看。”她终究是生气了。
我们去防波堤的次数越来越少,碧水蓝天变得飘忽遥远,书包里的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真切。我们开始用功,熬夜熬得眼睛红红的,林英家里给她用的灯泡实在太昏暗了,我从家里偷了一个60瓦的给她,她妈妈又嫌她费电多,最后,干脆,她就在我家里学习了。我妈也节省,可她不会省到这个份上。复习完功课,我再打着手电送林英回家,那时候,我们岛上很安全,送她回去,不过是夜里出去走走的好借口。夜风清凉,夜海安静,对岸的灯光星星点点,有月亮的晚上暗些,没月亮的晚上亮些,总在那里。每天夜里,走过无遮无拦的半山腰时,我们总也要停下脚步,看一会儿这些灯光。
我们曾经有过的天南地北的瞎扯,如今不知不觉都换成背啊读啊,浪费一秒钟都觉得是可耻的。成绩是怎么好起来的,我们也有些模糊,反正,在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们的成绩一下子跃到了前两名,阿虹,是第三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为考得不好发愁过。考试比种地还要可靠,只要你努力读书,试卷上的成绩,就保准好。种地还要看天呢。林英的爸爸甚至开始为她的学费发愁,要是林英考上城里的高中,那他决计不可能一日吃两餐酒抽半包烟了,他得开始节省。我们家似乎也是,本来妈妈就只计划着准备妹妹高中大学一路读上去的费用——那就够她犯愁了,我呢,初中毕业以后就能赚钱补贴了,就像我这回去捞水母一样,我会很能干的。妈妈在念叨明年开春她要多养一头猪,再多养三只鸡,她想养鸭,可算来算去,帮忙的人手不够,“阿大也要读书的”。不知怎么,面对她的焦急,我竟有些愧疚,我本不应该这样瞎掺和的,何必去当好学生呢?可是,人一旦当上了好学生,是不大肯再退下来的,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些好学生读书都读得那么辛苦了。那一年,我们班上都是辛苦读书的人了,大概是觉得我这样傻傻呆呆的也能把书读好,为什么他们不能呢?我们就只有更加努力,才能保住好学生的位置。有些人折腾了一阵,就松劲了,读书毕竟不是种地,未必春播就有秋收,我们就更在乎我们这好不容易有的收成了。
听完了蛙鼓阵阵,又听过了秋虫唧唧,在我们的夜路上,只剩下松涛声了——海在小平原外,浪打礁石的声音,在半山上是听不到的。入冬了,对岸橘黄色的灯光,看起来就特别温暖。
那个晚上,没有月亮,半路上,林英说,我们从清林老师家那边走好吗?
去清林老师家的老楼,我们得绕点弯路。而且,干吗去呢?可我还是陪她去了。黯淡的星光下,说它老,才不是说它不好呢,而是说它精致。青石地面,雕花石窗,是我们岛上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座老楼了,在它的四周,是我们粗糙的旧石头屋子,还有更粗糙的青瓦顶新楼房。我们站在一处暗地里,盯着这老楼里的灯光,林英说:“她就要出来了,你看着吧。”果真,过了一会儿,大门悄没声儿地开了,阿虹闪了出来,张望了一下四周,走得飞快。她干吗那么慌张呢?这是她干爹的家啊?她满可以大声说告别的话,满可以把脚步声走得咚咚响的。林英说她知道怎么回事,可她没法把事情很清楚地说给我听。林英又说,你干吗要知道呢?我们好好读我们的书就是了。被我问急了,她说,这事情很复杂,等哪天有空了,我说给你听。
可我们一直都没空过,功课填满了我们所有的时间。而且,我好像也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更加不想叫林英说清楚了。
过度用功的结果,是林英越发的瘦,我越发的胖。我看着自己像气球那样吹起来,无能为力。起初纠结于心的那件事,真的像没发生过一样,试卷和题目让我们看不到除此之外的东西。
那天,阿虹来找我们时,我们正埋头背化学公式。林英说化学最好学了,而我总觉得云里雾里,林英一心要帮我拨云见日,连写带画,额角沁汗,那会儿正对我怒目而视,恨铁不成钢。阿虹就这样走进了林英怒火纷飞的视线里,这让林英更光火了,你知道,英雄都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吭哧吭哧练功的傻样。林英气呼呼地把我们面前的作业推到一边,大咧咧从书包里扯出一本《红楼梦》来,自顾自看了起来。
“你们在读《红楼梦》啊?”这就是阿虹,她永远知道该说什么。
她的话音落下,窗外正好响起一阵鞭炮声,年节前就是这样,东一家,西一家的,大家都在那里放鞭炮谢年送年。鞭炮声歇了,林英的怒气好像也消了,她放下《红楼梦》,把她的凳子让给阿虹坐,自己坐到我的床沿上。我赶忙跑到堂前去端来一碟香瓜子——年节是要招待客人的。
阿虹坐下了,一双穿着皮鞋的脚并得拢拢的,抓了几颗瓜子,说:“下学期我可能会转校。”
“转校?”我们俩问得异口同声。这个岛上,初中,可只有唯一的一所啊。
“是啊,转校,转到城里去读,我干爹联系的,说是那里的老师能把我教得更好一些。”说话间,阿虹微微抬起了下巴。
这样的啊。那么,是到“外面的世界”去了?我拧拧自己的胳膊,这一阵练了摇橹,我的胳膊结实多了,我是想摇着舢板到外面的世界去的呢。那是我们在防波堤上看了又看的“外面”啊,阿虹真的就这样穿着皮鞋要去那里了吗?
我不知道这话是怎样出口的,可我真的说了:“阿虹,你干爹有没有把你抱在膝盖上改错别字啊?”
“我不写错别字。”阿虹的头抬得更高了。
“我写。你干爹就这样把我抱着改,你干爹可真好。”林英说。
“你干爹也抱过我。”我说。
“你们这是……嫉妒。”
“是什么,你自己知道。”林英又打开了《红楼梦》,把自己的脸和我们隔了开来。
“瞧你们……”阿虹站起来,又坐下了,“我来和你们道别,你们……”她就趴在我的寒假作业本上哭了起来,没有声音,肩头一耸一耸。
我赶紧去关了门。这是我的习惯动作了,大凡我和妹妹吵架,第一反应就是关上门。小孩子的事,和大人无关。
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我清楚地记得阿虹的双肩耸动,也记得林英躲在《红楼梦》后面的抽泣,可我总是记不起,当时,我做了什么。我记得有一束阳光从窗口进来,打在阿虹的背上,光束里,尘粒如蝶,回旋飞舞。我久久地盯着它们,想着大概尘世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是的,我就盯着那束光,也不说,也不动,我只是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这一切过后,世界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阿虹拿出她的手绢,仔细地擦干了泪水,转过头来对我说:“我真没有办法。”我茫然地看着她红肿的眼皮,心里头品味着她这句话,什么叫“我真没有办法”呢?我真的不懂。在后来的后来的后来,命运竟然又给了我许多机会听人倾诉,他们说到最后,也是一句“我真没有办法”,这是一句自我宽恕的话吧?每退一步,都说着:“我真没有办法”?然后,就可以安心地一步一步再退下去?
我没法把我的诘问说出口去,就只有眼看着阿虹开门出去。她钉了铁掌的皮鞋先是在我家廊前的水泥地里响了一会儿,到柴门那里是泥地,就没声了。
今年农历正月十四,林英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一下阿虹吧,她,肝癌晚期了。”我说:“就是那个……干女儿吗?我去年才听说她过得好好的啊,听说又认了不少干爹呢。”电话线接触不好,嘶嘶响,林英的声音也跟着哆嗦:“是啊,就那个刺激我们俩发奋用功的阿虹啊,这样说起来,她倒是我们的命中贵人。”
“命中贵人吗?”我大声问。
“她教会我们好多东西啊。”嘶嘶声正好停了,林英的话就清清楚楚传入耳朵。
阿虹教过我们什么呢?我拿着听筒搜肠刮肚想了半天。林英嗤地笑了一声,说,还记得吗?是她现身说法教我们什么是“干女儿”的。
“好啊,那等你空了打电话给我吧,你比我忙啊,就凑你的时间吧。”挂电话前,我这样说。林英在公安局工作呢,先是户籍警,再到刑侦支队,这会儿到经侦支队了,还当了个支队长,一路有贵人相助,一路升迁上去,越来越忙,比我这个码字儿的不知道要忙多少。今天这样的电话,一下子说那么多和钱无关的话,真是这几年来的稀罕事呢。上一个电话是去年春天的事情吧,她要我给她一点钱,她帮我去做借贷,她说“来钱来得飞快啊”。她要去了我的信用卡号,每个月往我的户头上打钱。再上一个电话,是前年夏天的事,她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和她一起开养老院,拿地啊筹建啊经营啊都不用我操心,我只要往里面投点钱就是了。我照例又投了些钱。这是她的好意。我们身边的人都在找门路发财,我这样埋头写啊写啊,一点不理财,手里的那么几个钱马上就会被通胀吞没的。也亏得林英,这些年,我的小日子在旁人看来也还算滋润,买了楼,买了车,好像过上了我们小时候常念的一首歌谣里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有车,牛奶当茶。“你得睁眼看看这是个什么时代啊!没背景,没靠山,怎么行啊……”那个电话里,林英是这样结尾的。是的,我确实在努力睁大眼睛看这个时代啊,不过,也许得眯缝起眼睛才能看得更清楚吧?——这句话,我也就心里说说。
这回,也还是林英简洁利落地挂断了电话。我们俩通话,总是她决然地先挂断电话。咯噔,这一声,在我心里放大、回响。听筒里嘶嘶声又响起来了,里面盘着一条小蛇吗?我们在防波堤上坐着说话的年月,真看见过几回蛇,它们从我们身边不远处游过,青绿色的花纹一闪,又隐进草丛里了。我们俩屏住呼吸,小手攥得紧紧的,谁都不愿意先放开。
唉,想这些干什么呢?我们都长大了啊。我甩甩长头发,把委屈甩在脑后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打开电脑里的文档,坐下来写几段,累了,就起来做家务,这样,整一天都像活在我的虚构里一样。做饭的时候,开着煤气,人不敢走开,可还是会走神,一抬眼就看到我的人物在半空里看我,我也试着和他们说话,这样处得时间越长,我和我的人物就越有感情,他们就会来帮我写作:我只要奉命敲打键盘就是。可今天,我抬眼看去,却看到了阿虹,从前的那个阿虹。她在那里笑吟吟地看着我。一会儿,那脸又变成林英的,都还是我们十四五岁的样子。
原刊责编 李萌 本刊责编 郭蓓
【作者简介】 杨怡芬:女,1971年生于浙江舟山,中国作协会员,2010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发表小说多篇,小说集《披肩》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