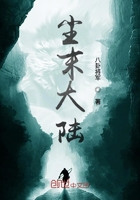1
那天没有雨,太阳清白白地照着,可许小雅总是感到,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以及这一整个大白天她都是在雨里走,歪歪斜斜地拖着箱子,水叽叽、没完没了地走。这箱子还是考上大学离开老家那一年买的,用了六年了,滑轮坏了一边,但也算方便,衣物什么的一塞就能走。
她竭力不去想前一天晚上的事,而是想想当晚及今后的住处,后两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想到答案,因为实际上她总在想前一晚的事。清晰地,她再一次看到自己轻手轻脚地打开门,为了临时取消的加班而想给杆子一个惊喜,手里还傻乎乎地拿着一盒白斩鸡与凉拌海带丝。然后就看到那个缺乏创意的画面,就在他们住了三年的小单间里,在他们凑钱买下才两个月的沙发上,光身子的杆子搂抱着另一个光身子,杆子眼角带泪,绝望而享受的表情,简直让小雅有些羡慕。
弥漫着烟雾般的黄昏中,被指定一般地,小雅反复想着这个不到一分钟的画面,它像是最后一坨黏糊糊的砝码,压在了她已经弯到地平线以下的耐心。她索性塌下来,听凭大脑里的黑墨汁四处流淌,她顺流而下地想到自己那同样恶心的广告文案活儿,没完没了的PS、调整字体、行间距、Ctrl+C加上Ctrl+V、居中或旋转90度。这就是她全部的出息了。城市好极了、爱情好极了、前途好极了,只是跟她统统都没有关系、永远都没有关系。你,许小雅,只有一条路好走、走到尽头,那是绝对轻松又快活的……这是今天第几次涌上这样的想法了,她没有数过,她只知道这想法越来越亲切了,像巨大的霓虹灯字幕一样在眼前闪烁。
就是在这个透不过气的被鬼缠住的时候,小雅看到了它,那张本来不可能看到的黄巴巴的旧信纸,它贴在公告栏里,几乎快被电器维修、钟点工、升学辅导、旺铺招租什么的给覆盖了,要不是她正倚在这个公告栏边歇口气,真是绝不可能看到的。有时就是这样,在错误的时间看到错误的东西,不,也许,是正确的东西吧。
“提供单间,零房租。黑头发,单身女性。绝无欺诈,详情面谈。”手写,线条有些歪扭,第一排字还蛮大,到后面越写越小。
这如果不是恶作剧,就肯定是个骗局,跟这张破信纸一样软乎乎的低级的骗局。可小雅一秒钟也没耽搁,飞快地在手机上按动起上面的联系号码。事后她多次回想,的确够衰的,自己是真的垮掉了吧,但她记得很清楚,拨出号码的那短短瞬间,心里头反而感到一股向危险逼近的高浓度快感。这很难解释,但就是这样吧,当事情恶劣到某个地步,反而像红布一样,会挑动起一股无谓的受虐般的武莽。
电话只响了一下就通了,是啊,好比浮子一动就提线。果然是个男人,烟嗓子,普通话,简单问了下小雅的年纪和姓氏,似乎感到满意,然后便说房子地点,让她去“面谈”。“黑头发吗?”挂电话前他又确认了下。
倒是一直想染个头发的,没闲钱。好,现在倒成全了。黑头发,这个变态为什么不喜欢黄头发呢。其实这时候小雅完全可以反悔,按下停止键。看哪,肮脏的黄昏已经过去了,多情的夜色取而代之,人们吃过晚饭都出来溜达了,一台小放录机响起来,激越的《荷塘月色》里,跳舞的老妈妈们像梦魇中的稻草人,她们机械地抬手、扭胯,一边不太在意、不以为然地瞥着小雅,她们准庆幸她不是她们的女儿。说实话小雅也庆幸她们不是她妈妈,要是妈妈真看到她这半死不活的蠢样子,看到可怜的箱子已经在外面被拖了一天一夜,她老人家准会难过死了吧,这箱子当初还是她替小雅挑的呢,她那么自豪地,脸颊上像开了两朵桃花,对每个营业员重复同样的话,说小雅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要到什么什么市去,了不起极了。她根本不会想到,毕业后的小雅只能混成这个死样子,惨得都很少回去了,她们成了一对“电话里”的母女。也许吧,妈妈乐意这样,这就是她所期望着的女儿的“出息了的”好生活。
是个老小区,墙皮剥落,楼道里堆着旧板凳、破箩筐、坏自行车。小雅还真有力气,带着一种自抛自弃的兴奋,冲刺般提着箱子一口气爬到四楼,对下门牌号,找到405室,防盗门与墙拐角处挂着蜘蛛网,像是少人进出。她挨着楼梯歇气,袖口上蹭了一层灰,她掸了掸,差点儿打个喷嚏。坏自行车、蜘蛛网与喷嚏,如同几个小人儿在不停地扯她后腿、给她发暗号。才不管哪,这些暗号真是棒极了,像迎面抽打来的棘条一样讨人喜爱,引诱着小雅往里面走。她就巴望着出点乱子,反正,这总比自我解决要合理多了。
只在按动门铃的时候,小雅闪过一丝怯弱与愤怒,想着该给谁写个短信,或发条微博,好歹让世界知道她在哪儿。仔细地、甚至带着善意地想了一圈,黑墨汁再次如伤花怒放,呸,难道真有人在乎她吗,包括她自己,说不定也包括妈妈。如果她知道女儿一直这么差劲、真还不如出点什么事呢——伤心总比失望要好,对吧。
跟电话一样,门才敲了一下就开了。楼道没灯,光线从里面射出来,看不清开门人的脸。“小许?”他上下打量小雅一番,似乎又考虑了一下,前后费了几分钟,然后侧身往里让:“请进。”
小雅小挎包的外侧口袋里一直有把折叠刀。她一直把手放在那儿,当然她不太喜欢这个动作。
看来这里只他一个人。他不高,也不胖,准确地说,有点干瘦。走到里面的灯光下,看清楚了。小雅的手离开包口袋,并突然感到很没劲。
其实不是烟嗓子,他根本就是个老头子。藏青色的套头毛衣塌在身上,下巴处青筋连着挂肉,天还没冷,都戴上线帽子了,正在倒水的身影明显佝偻。
小雅把箱子靠在门口,然后坐下来,接过他的水。这才发现自己多么不中用啊,哪怕这里是个火山口她也会一屁股坐下来的,哪怕老家伙端上来的是碗散魂汤她也会一口气喝光的。她是真累坏了,从整个五脏六腑一直累到十个脚趾头,这让她流失了一大半的冷酷斗志。
看看整个房子,还挺干净的,甚至有那么点儿讲究,电视机、藤椅、沙发、挂钟、茶几、冰箱、热水瓶、落地灯、大花瓶,还有个乐谱架什么的,任一样东西,都蒙着发黄的半透明的纱布或罩子,北墙有排书柜,里头高高矮矮的书也全都严严实实包着牛皮纸。
小雅扫了一眼,又扫了一眼,渐渐感到有点不对劲,却也说不清楚,大概就是封闭得厉害吧,极其地缺少人烟气,几有洞穴之感。整个房子,像是定格在好多年前的某一天,然后架空了,并罩上布套一直原样保持。她敢打赌,起码有五年以上,这房子没有外人进来过。小雅甚至感觉到,连她所呼吸着的空气也是很多年前的,她整个人就坐在一个褪色的过时的大罩子里。
小雅离大门只有五米远,箱子也就在门口,冲出去很方便。可是,有什么必要呢,难道还有什么好怕的,她有什么呀。再说,好不容易终于有地方坐下来了,老天爷知道她这两条腿有多重啊。
他在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小雅放下杯子,与这位可能的未来房东对视,并尽量露出笑容。可这一看,她又是一惊,这张脸,有点怪,活像是干巴巴的皮面具,谈不上恶意,但也绝没一丝和气,她迎面送出的笑像一碗水倒进沙漠里,他完完全全的、没有一丝儿的反馈。
小雅掉开眼睛,假装看茶几上的台历,看了一两眼,咦时间不对呀,今天明明是21号星期五,怎么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是周三?莫非今天真是累糊涂了,还是这个房子里本身就糊里糊涂呀。
老头轻咳了一声,语调平平地先开口:“广告贴了两天半,有五个电话骂我是神经病,有三个男的问我是不是做什么生意,其中一个是片儿警。也有五个来面谈的,我都不满意。你是第一个我请进门来谈的。” 小雅注意到他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像在揉丸子或数钱似的互相搓个不停。
他停下来,好像等小雅表示感谢,感谢他看中了她、愿意对她下手。
随便,他哪怕就真是个神经病、或是做黄色生意的。小雅点点头,把声音也控制得跟他一样平整,礼貌地交换她的境况,还是蛮对称的:“我今天一共看了四处房子,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都太贵了。我今天就得找到住处。嗯,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小雅连打掩护、留余地都懒得考虑了,她只是想弄明白:他的“零房租”是指什么,也就是说,她将要跳下的深渊可能会是哪一种类型的。
“先看房间。我姓胡,胡文伦。”胡文伦站起身,往里面走。小雅注意到,他四肢硬蹶蹶的,步调颇为奇特,碎碎步,快而不稳,好像慌里慌张似的。
房间不算小,挺干净,该有的都有,老实说比小雅以前租过的任何地方、包括跟小杆合住的那地方都强。除了同样的问题:令人不舒服的那种年深日久感——墙纸、门把手、五斗橱、写字桌、台灯、吊扇、百叶窗什么的,统统呈老旧的褐黄色,一碰就像要碎成齑粉。
“挺好。”小雅紧紧抿起嘴,注意不流露任何表情,一边看看床,床单和枕头也旧得厉害,老式被套上的绣花已经掉落了一半,但毫无疑问,很干净,以致非常非常地吸引她。“那个,您老,对我有什么要求?”她再次催问。重新看到床,小雅感到自己舌头都变大了,如力竭的落水者看到一只破船一样,哪怕睡一觉再翻掉也不管。小雅大概算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除了在小公园打过一个小盹,她有36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我的要求。”胡文伦看看她,眼睛像钉子,又黑又短,随后,他把眼光拉长,像衰老的猫把小房间的各个角落舔了一圈。“是的,我会有一点要求。”他迟疑地停下,随即显得愠怒。“我老了,万一夜里发病,你替我打120。就可以了。”
唉,可以打一百万个赌他根本没说实话。这跟女性、黑头发、零房租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收房租,任何一个房客也会这么做的,起码男房客还能背他下楼呢。
不过小雅一点不想戳破他。
“你放心,我睡觉很警醒的,手机24小时开机,紧急电话一键直拨。”小雅尽最后的力量表示了合作之意,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自我保护的生硬暗示。随后,她紧紧握住手机,一屁股坐到床上,随后就什么也记不清了。
2
再次醒来,耳边是窸窸窣窣之声,百叶窗投射进来的光线里,小雅注意到天花板上贴了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战斗机、歼灭机之类的东西,像是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还有手绘的云朵分布其间,有些纸片片快要掉落,又被透明胶带细心拉起,那些胶带已呈黄褐色,而其边缘则完全发黑,使得印刷飞机们看上去如同五花大绑。这简陋的科幻场景让她愣了几秒钟,并白痴一样地想到了童年、小床及其他无辜的东西,心里一阵发疼。她甚至想到妈妈,长达三四秒,随即这些想法像掐烟头一样给摁灭了。小雅重新闭上眼,装模作样在浑身上下尤其是裤子拉链等处摸索了一通,同时觉得这份自爱真他妈的奢侈,她就算给老头子怎么样了也是一万个活该。
翻身起来,感到体力又恢复了,同时也恢复了其他细微的感受——她尽量地麻木不仁,想了一下大致的境况,一边毛糙糙地决定:既然还活着,换个手机号吧,同时另找份零工。她不想再回去处理那些恶心人的文档了,而且也不想让杆子找到她,再说些狗屁不通的解释。至于“零房租”,反正都已这样了,爱怎样就怎样好了。
门与门框之间,有道小小的缝,小雅半蹲下去看,窸窸窣窣的小声音,是胡文伦在忙——他的姿态颇为滑稽,整个人非常笨重地前倾,在家具之间挪动,仍是慌张的小碎步,转身时尤其古怪,一小点一小点儿地转,像是切片动作组合。他架着两只细长的胳膊,一端拿把小鸡毛掸子,另一端是块毛巾,一上一下地打扫着,好似不太灵便的远程拉杆活塞,那样的严谨和缓慢,似乎他所处理的不是电视机、茶杯垫、藤椅之类,而是一碰即碎、价值连城的古玩器物。窄窄的门缝里,小雅没法见到他的表情,但他的整个侧影、吃力扭动的脚跟,与他所打扫的旧家什之间,传达出一种坟墓般的孤寂感,似乎这一系列毫无价值的动作,就是他在这人间消磨和支撑的唯一方式。
胡文伦突然开口,但身子没有转过来:“别在门缝看。出来。”听他声音,像逗孩子,带着不自然的亲昵感。哦,小雅突然间明白了,昨晚都想什么呀,其实事情再通俗不过了。她咳了一声进了小客厅,她脑子里开始出现一连串新闻报道般的想法:她用所谓年轻女性的活力,陪他说话、解闷,帮他打破那发黄的老罩子,让其感受到久违的温馨气氛。瞧,这就是“零房租”的附加值,她只要“扮演”成他的亲人而已。
“您老歇会儿,我来搞卫生吧。明天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怎么样?我会做菜!我们还可以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呢。”小雅强打精神、发出充满阳光般的声音,说出来之后,发现嗓子很干,并且由于刻意的假装而涌上来一股呕吐感。
胡文伦停下,抹布和小掸子都还在两只手上,他转身看着她,照旧没什么表情,说话有点斟字酌句:“你不要随便碰我东西、过问我的事情,除非有约定或我请求。你就是房客,不是陪护或钟点工。”
小雅略感惊讶,内心却也一阵松落。其实,善意、陪伴、活力或逗笑,她根本生产不出来!老天爷知道,她其实都不如这个胡文伦呢,她甚至都情愿跟他换,真的,老弱病死,并不赖的。小雅扭头瞥了眼外面的天,阳光仍是那么好,真讨厌哪,最好下大暴雨吧,最好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他们的洞穴里,让他们停下来都回到小角落,然后统统变成黑色甲虫。
“那……你什么病?这个能问吗?”小雅往嘴里塞饼干,饼干早不脆了,还有点油哈气。胃里很空,总得往里头扔点儿东西吧。胡文伦这房子虽是老旧黯淡,却反而增添了一种家的恍惚感,令她想起小时候妈妈做的酱油炒饭,一边冷冷地嘲笑这不合时宜的念头。
胡文伦好像有点惊讶似的:“病?”愣了几秒钟,他皱着眉勉强地说:“我有糖尿病,后半夜容易低血糖、会昏迷。”
小雅盯着胡文伦,他左手的两根手指又在打圈,像是神秘的暗号,他顺着她的视线:“哦,还有点帕金森症。”随即紧紧抿住嘴,不肯再往下说了。
小雅本想问他家里人什么的,见他样子勉强,算了。再说,今天星期六,每到星期六,十点左右,哪怕她窒息了坠落了快要死了,都要快快活活地打电话回去——空荡荡的家里,妈妈像老狗一样地守在那里,那个情景总让她牙根里一阵阵酸疼,更可气的是妈妈电话里的语气,总是那么急切热烈,像盲人手杖一样,引导着小雅,必须一连串地、像放鞭炮似的报告出各种好消息:又加薪了,刚到北京参加培训,被两个男孩子在追着,其中一个还是公务员呢,总之,她正在一天比一天地丰饶、壮大——这能怪谁呢,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小雅不仅有这个义务,似乎还百分百拥有这个天分。她从来没有勇气、甚至也根本没有机会张嘴对妈妈说出她的实情,比如,她被炒过鱿鱼,被劈腿两次,总是失眠,没有好朋友,厌恶逛街,不吃早饭,也有时一天吃上四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