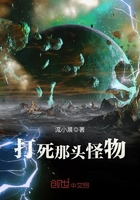1
虽然一切就绪,决赛各环节都按台词脚本备好了,静等着大幕一开启,各部门全盘照做就OK,可我这个唱主角的,却总觉气短、胸闷、心慌,时时袭来电视人小崔一般的忧思抑郁。阴历七月十五晚,天风浩荡的“卢沟晓月”歌台水榭,将上演《地球好身影》电视选秀总决赛,现场还将全球同步直播放送,我就是那个牛鼻闪闪光芒万丈的决赛冠军咩!一时间我手脚乱颤,面部肌肉痉挛,脑袋总在脖子上轻轻摇晃,感觉自己像得了帕金森。
我是打小地方来的,从没上过这么大的场子。眼瞅着祖坟就要冒青烟,谁能不处于紧张剧烈严重亢奋颤抖中呢?
娘怎么劝我放松、给我解心宽都没用。搞得她也跟着慌了神儿。自打上回她出了十万托人帮我录制MTV被骗之后,她再也不相信民间掮客小打小闹。这次她老人家是使了狠银子的,把祖屋抵押,四处散财,各种临时抱佛脚,最后通过叔伯二大爷的远房表弟的堂外甥女婿,搭上一个叫“元芳”的首长大秘,从官道上给制片人放了话,这才内定我为冠军。
三场预赛下来,我都是在被淘汰名单里给一遍遍打捞上来的。没办法,实力差距太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一遛就露馅。如果没有元芳做后台,我早已死得妥妥的。眼见着决赛在即,我这个半死不活元气耗尽的未来冠军,能不忧惧害怕得哆里哆嗦吗?
“臭不要脸的!”我娘领我去医院瞧病的路上破口大骂,“你说他们那帮人下手也忒黑!愣是让你从三层楼那么高的舞台上往下摔啊!这要是摔出个三长两短来,闺女,你说,让为娘后半生还怎么活?”
我娘说着,动手撩起衣襟抹眼泪瓣儿。
“别价了,娘,”我有点不耐烦,“不是您跟人私下里签了生死合同,说只要能拿冠军,可以不择手腕吗?我功力不够,赛不过人家,再不剑走偏锋,搞个假摔受伤什么的,还拿什么堵嘴?”
“那也不能从恁高的舞台缝里给推下去啊!摔完还得鼻青脸肿爬上来,单腿点地一瘸一拐绕场蹦跶,嘴里唱什么鸟叔《江南死大了》……”
“不是‘江南死大了’,是《江南style》,”我纠正我娘,“行了,娘。舍不得闺女套不住狼。走旁门左道,就是比正常门路风险高。这您也知道。”
说着话,协和医院到了。挂了专家门诊,一个戴眼镜的鬓发斑白的老太太接诊。她没问几句话,就刷刷刷开了单子,让我把X光B超查了个遍。检查结果出来,浑身没毛病。我这一米七五的间架骨结构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零件关节存在硬伤。
“没毛病?”我娘不信,“又是闹哪样?为啥娃整天哆里哆嗦像只筛糠鸡?”
“鸡嘛,筛糠……”医生老太太顿了顿,斜眼瞅了瞅我,“主要是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弦共振导致末梢触感不良。建议看看精神科。”
“你是说她脑子出了毛病?”我娘登时紧张,“老天爷!都说那些跳楼啊出车祸啊跑道上摔大仰八叉的人啊,越看着没事儿的,越容易颅腔淤血嗝儿屁着凉!求求你了大夫,可得救救我娃儿!这要是给赛回个傻子来,这二十来年我不是白养活了……”
我娘说着,打躬作揖唱个喏,接着又双手拍胸,脚跟跺地,拉满身段,捶胸顿足就想开嚎。我一把将她扯住:“行了,娘!快拉倒吧!这不是戏台,不是您老人家耍花腔的地方。”
“啊,是啊?”我娘手停半空,眼睛瞪大,做如梦初醒状,一副天真无邪又洞穿一切的表情,介乎少女与王母娘娘之间。
天呐!她老人家可太会装了!没闹上个金鸡梅花影后这辈子可真冤枉。只可惜我没能得她真传。
“神经的问题,精神能解决得了?”我娘严肃地问医生,脸上已然恢复一副慈母监护人状。
“要相信科学。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那个医生老太太不再正眼瞧我们,接着叫下一位。
娘只得讪讪带我走出来。“你说她到底说的是科学还是学科?”我娘问。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也回答不上来。反正,管它是科学还是学科,看病检查都得照样花钱,一分钱也省不下来。又重复来了一遍挂号问诊程序,CT核磁共振检查单子又给开了一堆。看到单子上的划价,我嫌贵,舍不得查。没人给我上三险,也没有医保社保。娘抵押房子那点钱,我可不敢穷得瑟。
作为北漂一族自由艺术家,再自由,也架不住是个盲流。
我娘不这么想。
娘说,“查!怎能不查呢!花钱算什么,闺女,别怕!只要你得了地球人冠军,以后那出场费挣海了去啦!咱家暂时抵押出去的那些房椽子、大梁、窗户框,都会变成大汤耗斯和诺贝尔家私,一件一件搬回来!不就5万块钱一平米吗?诺贝尔奖金买不起,咱买得起!”
一听这话,就知我娘心怀旷远,神驰八荒,是个关心时政、见过大世面的人,在我们老家那块儿俗称是“吃过大盘荆芥”。
据说,当年,有一回,一群记者来我们县采风,听到当地召集人介绍我娘说,这位漂亮女子是县接待办副主任,曾是豫剧团的台柱子,人家可是“吃过大盘精液的”!
座下几个男记者听了,惊得差点流鼻血,表示随时受不了!他们面面相觑,严重激动亢奋中,把县里四大班子陪酒成员晾一边,只频频给我娘敬酒、使殷勤,采风的宴会上到处是发酵膨胀的荷尔蒙气味。
等把那顿饭吃完了,想闹腾点下一步动作时,谁不经意问了一句,才知是搞错了,召集人说的是“吃过大盘荆芥”。
“尼玛荆芥那种破草根子很难吃到吗?”一个网媒记者破口大骂,“也敢发出与老子高蛋白液态物质同样的舌尖摩擦音!”
“不说普通话,实在很坑爹啊!有木有?有木有?”另一家晚报记者也痛恨得咬牙切齿。
要说我娘她老人家,若不是因为一次演出时摔跤,造成腰椎间盘突出武功尽废,她的演艺生涯早火爆云天响遏浑球,哪还有闲工夫吐血提携我这么个三围不闯关的青涩女儿?
各种检验结果出来,我脑壳里面也很正常,没有哪根血管破裂,也没有哪处脑浆冒顶坍塌成片儿汤。“你的这个,没有问题,”医生拿着检查单子对我们娘儿俩说,“要么,物理的不行,就去看看心理的。”
“娘,我不想赛了。”我终于大着胆子,说出了压抑心底许久的话。
我娘一听,一个大耳刮子搧过来:“弃赛?你休想!你还老娘的房椽子!”
我恼羞成怒,悲愤填膺,却又没办法跟我娘对抗。毕竟,我就这么一个含辛茹苦将我带大的娘,我不想辜负她。
最后的结果,猜也能猜得出来,妥协的当然是我。我忍气吞声,捂着半扇被搧红的脸,听从精神科医生的指点,到二环以里去看高价心理医生。为这,我娘又卖掉了乡下我姥姥家刚出栏的一头猪。
2
白谷狗医生的心理诊所,位于城市中心区的护城河边,环境优雅,地段显赫。一弯潺潺流水,引得岸两边杨柳垂涎,野花竞艳。除了串红、雏菊这些贱贱的地表装饰花卉外,还有大叶黄杨和金叶女贞等低纬度树种,一年到头没皮没脸地绿着,扰乱了北方四季反差鲜明的景观。我去的时候,狗正垂涎一只鸭子,虞美人凛冽盛开得像大烟花。
一进门,见白谷狗正捧读一本风靡人寰的《金条战争》。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东太平洋大学的学位证书,还配有一张做旧风格的黑白博士袍照片。紧挨着是诊所营业执照、工商年检合格证什么的。
我仰视了一眼,恍惚觉得那张博士照有点特别,跟我在别处看到的海龟们的有点不一样,但具体创新在哪里一时也说不清。于是我请求上厕所,跟白谷狗打招呼说借用一下卫生间。自打北京闹过非典之后,每逢进门必先洗手,这个好习惯我一直随时保持着。
白谷狗家这间厕所装修得不错,具体细节没有记住,就记住马桶边的后墙支架上装有卷筒手纸。抽出一块,纸面柔软,气味芬芳。一看,是加了香的舒婷牌子,上面还一截一截印着“与其伫立千年,不如在爱人肩上痛哭一场”什么的。
我差一点给跪了,心说当年中学语文老师逼迫我背诵多少次,我就是不好好用功,结果枉活了二十来年,造成就这么自己一人儿呆呆地伫立帝都。
我不由百感交集,很珍惜地把手纸诗句叠好揣在兜里。卫生间里能够提供免费手纸,足以证明白谷狗医生的确是受过国外良好教育的优质公民。
洗完手晾干出来,迎面,视线又跟墙上的照片打了个碰头。我紧了紧瞳距,觑眯着眼儿再度瞻仰,这才看出博士照片与别处不同的是那顶帽子。一般来说,毕业典礼上被大学校长开过光的博士帽,穗子应该给拨到左边。白谷狗的这个帽穗却耷拉在右边。不知他这是要闹哪样。
盛夏的午后,屋里冷气开得很足。我哆哆嗦嗦,在就诊桌旁抱颊而坐,不时偷眼打量白谷狗。只见他面白,脸尖,眼小,嘬腮,整个人面相很薄,看上去像一枚公知柳叶刀。我下意识地双手捂向肚子,很怕他会给开膛破肚切腹掏心。
“亲,怎么不好?”
白谷狗色迷迷的目光,从一对小眼中射将过来。我顿觉双腿间一热,一股热浪涌上周身。好亲切哦!多么熟悉的眼神!一股子雄性动物骚情开屏的劲儿。平常挤在地铁里拿眼一扫就一大堆。我的心里立即踏实。
“紧张,”我说,“要参加一个电视决赛,过度紧张。”
“我知道,”白谷狗说,“你刚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你是‘地球好身影’里的小鹭鸶吧?”
“哦,您也看这节目?”被人认出来,我感到惊喜,刹那间有了爆红明星感。我把腰板略微挺直了些坐。
“不上微博要落伍,不看地球好身影没球籍。”白谷狗说。
“谢谢您的光辉评价!”我赶忙道。
“尤其是,你的表演给人印象深刻。预赛最后一场,你从舞台缝里摔下去,观众都以为要出人命,都举起苹果爱派和爱疯‘夸夸夸’猛照发微博,嘿,那才叫一个威风浩荡群情激昂!就等抓拍你血哧呼喇给抬上120急救车的精彩镜头呢!哪成想,你竟然又活着爬了回来!你说你哈,不光回来,还单腿点地一直满场蹦跶,骑马蹲裆式唱完了《江南死定了》!实在是感人呐!色艺双馨!色艺双馨!”
“你才色艺双馨。你全家都色艺双馨。”
“别客气。说真的,像你这样的实诚人,演艺界里还真不多了。一般人的善后方法,都会立即把伤口面积扯大,把自己大腿骨关节掰折,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勘察现场,定损、理赔、索要巨额修复款……”
“咄!那等下三滥事情,岂是我辈干得出的!”我义正词严,把手掐腰,“戏比天大,狗爷涅槃!三尺T台,九寸荧屏,我们艺术家,心里要永远装着把步走好,把戏演真!”
“太对了,亲!我与你的看法完全相同。”
“可是……摔过那次后,我确实感觉自己出了点问题,需要你的帮助……”
忽然,我一眼瞥到桌上有本《知阴》杂志,嘴巴立刻像被封住了。我早听说,一些心理医生是《知阴》的特约撰稿员,他们利用法术把人催眠吐露隐私后,以千字一万块的高价卖给杂志,通常都是女明星黑木耳漂白、修复处女膜,男星断背娈童、强撸灰飞烟灭什么的恶心事。一旦追究起来,他们还振振有词,说老祖弗洛伊德巨著《梦的解析》就这么干的,书里最熠熠生辉的段落就是病例实录。
我可不愿意自己花着钱给白谷狗提供下脚料。
“亲,肿么了亲?我们这里可是计时收费的。”白谷狗诱导着我说。
“我……就是担心决赛时再摔跟头。”我小心翼翼,斟酌着字句。
“甭担心。人不该在同一个赛场摔两次跟头。人也不会在同一个舞台缝里掉下去两次。”白谷狗十分肯定地说。
“不……不,不一定吧……”我嗫嚅,“玛雅人说2012……人类文明要换届……等离子能量与暗物质产生聚变,两次迈进同一条河流将成为主流……”
“噢,你是说那个?”白谷狗不屑,“小概率事件,属于基因库病毒逆袭,人类灵魂加压反应堆没有经过360度绿坝反智处理。”
怕我听不懂,他又凑近我,几乎接近耳语着说:“这么跟你说吧,伊甸园里那个苹果,亚当吃完了给牛顿吃,牛顿吃完了乔布斯还接着吃,为什么?”
“为什么?”我茫然。
“因为,”白谷狗神秘地看了看左右,扭头又把嘴巴进一步贴到我的耳朵根,一字一顿,吹气如兰,“因,为,苹,果,是,女,的……”
他嘴里的哈气搞得我耳朵眼痒痒的,神经麻酥酥一直导电到大腿根儿处,惹得我下身有点不对劲儿。我赶紧闭拢双腿,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把头稍稍偏过一点躲开。
见第一次试探性骚扰没有得到回应,白谷狗收回嘴去,自我解嘲说:“嗯,苹果的问题嘛,继续留给夏娃去蒙骗上帝。亲,看你的才艺气质俱佳,是哪个院校培养出来的?”
“我小时候家里穷,只上过五年学,后来辍学在家放鸭……”
“嗯,好!念书少,没被体制约束和阉割,所以筋骨灵活,保持了原始野性和抗摔力。”
“……后来又上过无线电演艺短训班。”
“TVB还是BTV?”
“CCAV。”
“好!非常好的学校,纳入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大学。有这么好的履历,你还愁什么?”
“我一直为自己的出身自卑,从小在农村里长大,没受过系统教育,不像其他选手来自大城市,都是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从小就开始练钢琴、练唱歌,练芭蕾舞……”
“错!”白谷狗手势有力一劈,“乡土中国,只有说自己是农民、生活悲惨、自学成才、求艺路途坎坷、从小父死母改嫁,或者干脆不知自己亲爹是谁,才能对得起时代!”
“你是说,为了一己成名,就得让自己的亲生母亲让别的男人给操了?”
“流言当道,不来点身世传奇还怎么成才?”
“呸!”我大声道,“告诉你,我不能那么做!姐是有底线的!只不过底线有点靠近终点。”
“门萨的娼妓……”
“你说什么?娼妓?”我脸涨得通红,“腾”地站起身来,转身就要走。“少跟我扯什么娼妓!”
“别激动,”白谷狗也站起来,温柔地一手按住我的肩,示意我坐下,“《门萨的娼妓》,是一本世界名著,伍迪?艾伦早年写的小说,专门表扬高智商的女子卖艺不卖身。”
我仍然气哼哼,“我不知道门萨。我只知卡门和茶花女。”
“一样的意思。”
“告诉你我什么都不卖!要卖,我早就当商务模特儿三陪去了,还用得着这么假摔!谁不知道睡觉挣钱来得快。”我大声嚷嚷,突然感觉着自己个儿有点委屈。
“睡……还是不睡,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白谷狗若有所思。说这话时,他苍白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有一种哈姆雷特的忧郁延宕气质,让人很是着迷。可也是,敢在二环以里沿街商铺开店的人,都得有两把刷子,谁都不是白给。
我克服义愤,重新平静下来,听他为我作疏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亲!多么高贵的理性,亲!多么伟大的力量,亲!多么优美的仪表,亲!多么文雅的举动,亲!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亲!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亲!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嗳,亲,你说,男人,更喜欢跟妓女睡还是喜欢跟波伏娃睡?”
“当然是妓女……对不起,跟你说了我不想谈论睡觉。波伏娃是谁?打网球的?”
“文化人。”
“哦。那更不行。”
“法国的。”
“法国……”我沉吟了一下,“外国娘儿们,那就另说了。”
说着,忽然觉得不对,谈话脱离正轨,正在被他引向爆料窥阴的危险边缘。
这狗娘养的!
我得扭转话题。
“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商务模特儿,卖艺不卖身。”我更大声地说。
“商模也不该遭贬低。”白谷狗频道也跟着转换得快,“你看,虽然你嘴巴大、颧骨高,属于杀夫不用刀的克夫脸型,不太符合国人传统审美,但你的下半身,却相当精彩!你的大腿修长,小腿光滑,膝盖骨圆润,脚踝纤细,当你穿着黑丝站在台上时,简直迷死一大片!绝对是国际范儿!对了,亲,你有多高?”
“1米75。”
“够高了。站在哪里,都鹤立鸡群颠倒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