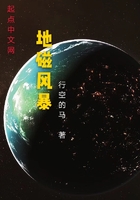在尤达宣读遗嘱的时候,云韵纹丝不动的坐在客厅面向花园的落地窗前的一个扶手椅里,显出一副心神不宁、若有所思的样子。丧礼的第二天,她穿着一袭形似旗袍的黑裙默默无言、温文尔雅的坐在那里,和在切面店里判若两人。不同的环境使同一个人看起来不那么一样了。在切面店里她是个和面粉打交道的普普通通的妇人,而在这个奢华的客厅里她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位端庄贤淑的富太太。她的那张蜡黄的布满细纹的脸依旧毫无特点,她那干瘪瘦削的身体依旧和气质无缘,但穿着雍容华贵的服饰,置身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呼吸着淡雅清香的空气,这外在高雅的一切使这个年过半百、其貌不扬的妇人显出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尤其是笼罩在她周身的那种真挚而高贵的忧愁和哀伤更为她平添了几分母性的柔情和女性的魅力。
但她并不是始终这样一动不动的坐着,而是时不时会抬起眼、转过脸看一看永恒所站的位置。某时,她会出神的盯着这个心不在焉、神思恍惚的少年陷入沉思中,然后又摇摇头,轻声的叹口气,便无奈的移开了目光。很显然,在场的所有人中,唯有这个妇人和这个少年对遗嘱的内容没有半点兴趣。当遗嘱宣读完毕,大家争先恐后、信誓旦旦的深表决心时,云韵站起身,无声无息的从大家的背后绕到永恒的身边,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一举动,把这个神思游离的少年从对昨天经历的回忆中拉回到当下现实的处境中。永恒的身子骤然颤动了一下,好像被这个触不及防的动作吓了一跳。他转过身看了看拍他的人,脸上原本惊讶困惑的表情立刻转变成对面前之人的同情、爱戴和尊敬之态。他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云姨,不知道为什么,眼里突然噙满了泪水,他伸出手抓住云姨的手,看着她红肿的、充满忧伤的眼睛,似乎想对她说点什么,却只是无声的翕动了一下漂亮的双唇,一个字也没有吐出。
仲馗的死带给云韵的痛苦永恒看在眼里,懂在心里。他比任何人更能理解这个妇人的深沉的哀伤和无言的隐痛。尽管他和她彬彬有礼的朝夕相处了一年,她对自己的痛苦始终守口如瓶,对他就像一位母亲对待儿子一样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但他还是看出这个时常强颜欢笑的女人生活的不幸福。她终日在切面店里忙前忙后,像所有认真对待生活,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的女人一样一刻不得闲,总给人一种妇道人家为琐屑的日常生活烦扰的无暇去顾及其他任何事情的样子。但是,永恒明白,这样忙碌的她,其实内心里却异常的空虚和孤寂。关于这一点,永恒根本不用刻意去留心和观察,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声情并茂不经意间总是把她人生的不如意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无声的忧愁比语言的描述更逼真,更形象,也更具说服力。
永恒虽然涉世未深,不谙世事,但也明白云姨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她得不到爱,既得不到孩子们的爱,又得不到丈夫的爱。在这个家庭里,她的位置形同虚设。至于原因究竟是什么,仅凭和云韵相处了一年时间,他不可能明白。然而,纵观这个家庭形成的过程以及各个成员的性格特点,我们不难理解:孩子们不爱她,是因为从小他们就没有真正的体会过健全的父爱和母爱,他们的母爱总是笼罩在愁云之下,而他们的父爱又总是掺和了太多铜臭的成分。因此,人世界最无私、无畏、深沉的爱在这个家庭里是不存在的。那种在伦理范畴内习惯于被世人夸大的亲情在这个家庭里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血缘关系使他们不得不藕断丝连、若即若离,实际情形令他们又渴望形同陌路、非亲非故。在伦理观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违情悖理的风貌,但却也真实、中肯,毫不矫揉造作。
孩子们从小对爱既体会不深,又毫无所求,因为他们常年在外奔波的父亲用金钱取代了他们对爱的一切要求。因此,既然他们不要求被爱,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爱。所以,他们的母亲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疼爱着孩子们,却无法要求孩子们用自己希求的方式来敬爱回报自己。这种隔阂,亦或者这种矛盾始终横陈在母亲与子女之间,让他们终其一生既亲近着彼此,又伤害着彼此。想拉近又拉不进,想推远又不能推远;丈夫不爱她,是因为她的丈夫是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不会有爱的人。对一块石头谈论感情,那不是石头的过错,而是人的无知。
因此,当一个清秀俊美的少年突然被安插在云韵生活里的时候,这个女人便把那种快要变质的亲情之泉毫不保留的浇灌给了这个亲情干涸的少年。她用真挚的近乎于母性之爱的情感对待着这个忧郁、简单、直率、坦诚的少年,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时间里,尽着一种连她自己都难以理解、模糊不清的责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竭尽全力的袒护、庇佑着这个少年。每次只要丈夫一流露出让永恒离开切面店的意向,她就像抱窝的母鸡支棱起翅膀维护肚下的鸡蛋一样,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理由证明现在让永恒离开切面店去干其他事情还为时过早。平日里,她虽然看起来木讷、愚钝,但某时也会显得特别聪明、圆滑。在对待永恒的问题上便是如此。在假装漫不经心劝说丈夫的时候,她始终以丈夫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丈夫生意上的实际所需着想,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竭力说服丈夫,说以她妇人之见认为,永恒年龄还太小,个性上又有点执拗,再加上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出去无论干什么事情,如果身边没有个老成持重的人管束,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让他在切面店多待些时日,等他思想和性格上略微成熟稳重一点后,再安排他干其他事情也不晚。一向精明老练的丈夫也认为妻子的话言之有理,便暂且打消了让永恒离开切面店的想法。
多年来,虽然丈夫从未和她谈起过自己生意上的事,但一种模糊的本能使云韵相信丈夫的生意并不干净,因此一种良知上的道德感使她不愿让如此单纯的永恒涉足丈夫的生意,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一条将来一定会悔恨终生的歧途。所以,她一直假装糊涂,却不动声色的,用母爱般的智慧和机敏想方设法把永恒留在身边。在暗中和丈夫较劲这一方面她做的很成功,也相当出色,那只是因为她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丈夫,虽然了解的不够透彻,但也多多少少知道他的弱点。但在其他方面她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干涉这个少年的生活了。例如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上的男性渴望,以及同伴对他的影响。实际上,一起在切面店干活的同伴对于永恒的影响远胜于她对永恒的教导,因为耳濡目染比谆谆教诲更具实效性和感染力。因此,在她与永恒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里,她虽然殚精竭虑的想让他远离那种很可能诱导和腐蚀他单纯心田的不理想生活,但却不能完全左右他的意志。她源于美好动机的干涉始终局限在某种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外的一切这个忧郁的少年总是默默无语的自行其是。于是,永恒不由自主的驯顺着生存的这条荆棘满布、坑坑洼洼的道路一路跌跌撞撞的摸爬滚打,已经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了太多世俗的陋习和生活上的恶脾。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善良的庇护人都无能为力。但即便如此,正直的云韵始终坚定不移的暗自违背丈夫的意愿而如履薄冰的站在与她非亲非故的永恒这一边。但她也只能做到如此,既不敢也不能有进一步的大胆作为了。她始终认为,她的丈夫虽然不是个好丈夫,但是她绝对有理由尽到妻子的本分。她可以不赞同他所有的行事准则,但绝不能不顾夫妻情分而冷酷无情的出卖他、背叛他,这是她作为人妻的基本底线。
这个终日里围着一团面打转的女人,在世俗的那些爱夸夸其谈的人的眼里毫无见识,却显示出了圣人般的人性至善的美德。不禁令人深感钦佩和尊敬。
现在,丈夫故去了,虽然这种故去来的那么突然,就像那阴晴不定的天气,刚才还晴空万里,霎时间却下了一阵太阳雨一般。然而不管怎么样,丈夫的故去的确让她悲痛欲绝,她没有感觉到家里的顶梁柱骤然倾倒后那种天塌地陷的感觉,而是觉得原本支离破碎的命运更残缺不全了。丈夫的离去,与其说让她心痛,倒不如说让她受累。说不出为什么,当她看到一向吆五喝六、说一不二的丈夫像一具干尸一样呼吸微弱的躺在切面店二楼的那张整洁的床上等待末日的审判时,一种莫可名状的不安和疑窦使她心绪不宁。她认为丈夫死的如此之容易,让她有点难以置信。一个把自己的命运始终仅仅抓在手里的人是不可能轻易的在死亡面前妥协的。而躺在床上的那个奄奄一息,她几乎有点认不出他本来面貌的男人却似乎渴求快点死去。
“也许,他真的想早点解脱了。”她看着她突然觉得一点也不熟悉的丈夫,曾这样想道。
然而,当他回光返照又显示出片刻的精气神儿后,便无力的垂下手臂,永远的闭上了那双任何人见了都觉得恨透一切的眼睛时,云韵诧异的发现,一种她不愿承认却异常真切的解脱感遍布了她周身的每个细胞,使她压抑已久的神经兴奋的跳跃起来、苦闷的心情豁然开朗。她难以克制的感觉到了重生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正因为她如此清晰的感觉到自己即将枯萎的生命突然被未来的朦胧希望注入了新的给养,这种对逝者的残酷和不敬行为使她大惊失色。为此,这个善良的女人不禁在内心里自责起来。她越是为自己不该有的行为感到羞愧,就越显得伤心不已。这种伤心不单单是为了沉痛悼念逝去之人的生命,也是因为自己的冷酷无情和毫无人性。是的,当云韵真切的意识到自己远没有原先认为的那么深爱和依赖着丈夫,实际上,在灵魂深处她一直渴求解脱和逃离,但却由于个性柔弱而连幻象都不敢抱有。如今,当这个赠予她一生痛苦的男人先一步踏上黄泉之路后,她敢于流露自己的真心了,并认为这是残酷的命运由于良心上的不安而赐予她的最后眷顾。但不管她为自己的这种比丈夫生前的任何行为好不了多少的绝情行为找多少看似恰当的理由,她都不由自主的为自己的另一面感到吃惊和胆寒。于是,她努力掩饰自己的解脱感,而表现的像一个深受丈夫宠爱而又深爱着丈夫的女人刚刚守寡后所能唯一体现的那种人间言辞难以描摹的忧愁、沉痛而哀伤的样子。虽然她认为自己一直在竭力表演,实际上,她对自己人生难言的悲伤借助这种情感体现的更真切和感人肺腑。因此,她越显得伤心,永恒就情不自禁的越想关心她。于是,仲馗的去世,让这两个在不同的处境中同时得以解脱的人的关系拉的更近了。而云韵也开始敢于毫不畏惧的为永恒的未来设身处地的着想了。
故,当这份遗嘱弥漫出一种魅蛊人心的诱惑力,使人们心甘情愿的臣服在它的召唤下的时候,云韵不禁为永恒担心起来。她不希望他继续盲目的留在这里,不明所以的为这个迷津暗道的团体效力卖命。所以,在乘人不备的情况下,她悄悄的走到他的身边,想把他叫到一边,好好的和他谈一谈。这当儿,她看到永恒用这么善解人意的温柔目光望着她,就越发觉得应该为他做点有意义的事了。于是,她歪了一下头,示意永恒跟她走。永恒既茫然又温顺的跟在云姨的后面,两个人轻手轻脚的离开人群,从客厅拐到上二楼的楼梯口。这个角落,站在客厅里的人的视线是扫视不到的。
“永恒,”一走到楼梯口,云韵便开口了,“告诉云姨,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永恒默默的看着云韵,没有作声。
“永恒,”云韵又说,“你听云姨说。现在你仲叔也不在了,说句公道话,即便他在世的时候,他也没怎么对你另眼相看、照顾有加。他那个人,别人都不了解,也看不透。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如果没利可图,他是不会平白无故对一个人表现出友好和热情的。虽然这些话,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应该在他去世后拿来评价和非议他的。但我一直没把你当外人看待,所以这些如实的知心话也愿意对你说。云姨知道你的为人,你这个孩子虽然看起来傻乎乎的,但心地善良,品行纯洁、端正,是个难能可贵的好孩子。以前,我不敢干涉你仲叔的任何事情,现在他不在了,云姨就想对你说几句实在话。永恒听云姨一句劝,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人吧。说白了,客厅里的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呀?这些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他们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做人的准则。你跟着这些人会把自己毁了的。我知道你仲叔用人的标准,他专门挑选一些亡命之徒和见钱眼开的人,然后抓住他们的弱点,利用他们,煽动他们,诱惑他们,让这些人在欲望的作祟下对他言听计从、忠心不二。可是,孩子,那是别人选择的路,你不应该走这样的人生道路,因为云姨看的出来,你和他们完全不一样。永恒,听我说,”说着,她一面谨慎的环顾四周,一面把一张银行卡仓促的塞到永恒的手里,“这张银行卡里有一笔钱,数目虽然不大,但足以为你选择新道路芟除一些开头阻挠你前行的荆棘。你不要拒绝,这是你应得的。我知道,你仲叔在过去一年里曾每个月都会给你一点生活费,但那远远抵不上你的劳动所为他创造的价值。这些钱是云姨补偿给你的,你受之无愧。永恒,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些人。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这时,云韵听到逼近的脚步声,她探前身子瞥了一眼,看见旱魃正低着头大步向这里走来,便神色不定的说,“好了,你回去吧,旱魃来找你了。”永恒正要走,她又拉住他的手臂慌里慌张的加了一句,“一定要记住云姨的话,别跟这些人厮混在一起。”永恒茫然的点点头。云韵放开他的胳膊,急匆匆的上楼了。
这时,旱魃走了过来。
“我说看不到你的人影,原来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抬起头瞥了一眼刚拐过二楼平台的云韵的背影,又把锐利的目光放在永恒呆滞的脸上,说。
永恒垂下眼睛,把银行卡紧紧的攥在手里,没有回答。他刚才虽然始终在认真听云韵讲话,但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她都说了些什么。从云韵口里流泻出的那些语重心长的金玉良言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进他左边的耳鼓,又从右边的耳廓飘走了,在整个过程中,一个字都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停留过。因此,这一刻,当旱魃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仅大脑一片空白,而且思维混乱一团。
“走了。”旱魃看他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摇摇头又说。
“去哪?”永恒问。
“当然是回我们住的地方了。”
永恒点点头,然后跟在旱魃的身后回到客厅。他还没站稳,刚才宣读遗嘱的仲叔的私人律师便走到他的跟前,把他叫到一边。这位法律顾问——尤达先生——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因为他习惯于摆出一副老气横秋、威严肃穆的庄重表情,因而看起来足有四十多岁。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外面套一个黑色的马甲,脖子下系着一条黑色的领带,臂弯处夹着一个公文包,趾高气扬的仰起头看着永恒。这位律师中等身材,五官中庸,眉心处有一颗醒目的痦子,使他看起来异常的狡猾奸诈。即便像永恒这种不会凭着面相揣度别人性格的人,也觉得此刻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他以自己的身高看起来的矮个子是个讨人厌的虚伪之人。此刻,尤达带着轻蔑的眼神望着被他叫到一边的这个无论在身高上,还是在面容上都优越于他的少年。虽然表面上呈现出一种不屑轻蔑的神情,内心里却无比嫉妒这个少年一表非凡、得天独厚的外型。
“永恒,”身边只有他们两人时,尤达用神秘的口气说,“仲叔在去世前曾特意嘱咐我,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他让你在他去世后的这一年一定要跟着旱魃,不要离开这个小集体。旱魃会指导你去做一些只有你才能完成的事情。你知道,在生前,仲叔就对你寄予厚望,在他死后,这种厚望不但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反而越发坚定不移了。仲叔对我说,他深信,你绝不会让他失望的。所以,一定要听逝者的话,那等同于神祇,会让美好的未来按着你的意愿展现在你的眼前。”说完,他也不管听他讲话的人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便一脸阴笑的拍了拍永恒的肩膀,信步走开了。
这一天,不同的人对永恒说了不同的话,但任何人的话永恒都没有听在心里。任何话都像过眼云烟一样,一眨眼便没了踪影,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打从昨天开始,他便像做梦一样,一件接着一件的经历着一些非比寻常的事情。他年轻的心还不足以立刻领悟和消化这些事情。他对一切既将信将疑又摇摆不定,一会儿感觉一切都是切切实实的,一会儿又感觉一切都是朦胧虚幻的。一会儿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怎么样,此刻觉得张三说的对,彼时又觉得李四做的对。连日来,他始终像踩在云絮上生活一样,既轻飘飘又茫茫然。没有一天是真实的,又没有一分钟是不真实的。他觉得生活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始终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兴致盎然的揉来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