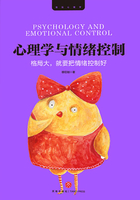安宁付了钱,跟着进了弄堂,潘冬子的电话被她给掐断了。
这个时候的安宁,哪有心思去应付潘冬子,她的一颗心都在许愿身上,而她掌心紧捏着的那块小饰品,全沾染上了****的汗渍……
安宁每往前走一步,心里头就扑通扑通地直跳。
她跟许愿保持一段路的距离,就怕被发现,都跟踪了这么久了,不能前功尽弃。
这儿的弄堂,虽然比较破旧,但比上次去找许愿的那一处贫民窟好多了,那边鱼龙混杂,这边人烟萧条,图的是清净。
安宁庆幸自己一贯走的是朴素的路线,没有引人注目。
许愿停了下来,安宁也止步不前,许愿是在弄堂末的那间古朴的房子前停下来的,而那尽头是死胡同,被高大的围墙筑得老高,死死堵住了前面的路。
许愿推门进去,门似乎没有关,安宁也没见到许愿拿出钥匙来。
许愿进去了三分钟,没人出来,也没人路过,安宁才敢上前,那门旁还有一捆捆叠起来的干稻草,安宁环顾了下四周,那是藏身的好地方,又靠近窗台。
安宁飞快地跑到那稻草后藏了起来,她发现一半的窗户被稻草挡住了,远看窗户是紧闭的,只有靠近,才能够察觉有半扇的窗户是打开的。
许愿没有走远,就在进屋子的这个房间里,因为安宁听到了她的声音,然后,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声音,让她不敢置信,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整个人在瞬间就化作了一块僵石。
她有一种落荒而逃的冲动,这秘密,犹如惊雷,对她而言,无法承受。
她有些恨起自己追根究底的秉性起来了,她完全没必要追上许愿的。
她以为许愿来见的是潘冬子,没想到居然是……居然是那个她平日里极为尊敬的人……
他一贯谈吐清晰明白,情绪掌控的很好,他的内心,没人能够看透,他藏得极深。
安宁扶着墙壁的手指轻轻的弹动一下,又仿佛强自克制住了,她改为背靠着墙支撑自己身体的力量,她有些担心自己太过惊吓导致身体瘫软下来,站不住了。
安宁面无表情,说不清是什么情绪在刹那间纠缠住了自己,她死死地咬咬唇,冷静了数秒。
这个男人,是潘冬子的父亲潘少岳,她怎么也没想到潘少岳会跟许愿有私情。
难怪潘少岳那么强烈地抵制潘冬子娶许愿呢?
安宁本来还觉得奇怪,潘少岳应该不是那种难说通的人,潘冬子幼年丧母,潘少岳是既当爹又当妈地将潘冬子给拉扯大,潘冬子既然认定了许愿,潘少岳应该祝福才是。
本来想不通的那些问题,在这一刻,安宁是豁然开朗。
但她却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藏着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叫她回头如何面对潘冬子。
她甚至对潘冬子隐隐生出了几分同情来,潘冬子想必不知道的,不然那孩子,他不可能就这样带回。
安宁暗暗心惊,以潘冬子的性子,若是此事揭开,他若是不吵不闹,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潘少岳有想过这样的后果吗?还是他太过自信,觉得自己有把握处理好它。
连她都无法接受的事情,何况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女友跟他的父亲……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坦然地接受吧。
除非……他疯了。
“小愿,如果你真想结婚,我的助手便是个很好的人选。”
潘少岳沉沉的声音在安宁的耳边来回晃荡。
许愿嗤笑一声,“潘少岳,这就是你电话里说对我的弥补吗?你的儿子正养着他的弟弟,而你,却要你的孩子的亲生母亲嫁给你的助手。”
“是啊,你的助手精明能干,娶了我又能够升官,我是你的女人,他私下里定不会动我,你是打算我嫁给他后,跟你继续私情藕断丝连还是跟你了断前尘往事呢?不论哪一项,对你都没有坏处,既能安抚了我,又能让你天下太平,是不是?”
许愿明显顿了顿,“可是你有没想过如果你的儿子知道了这些事,会拿怎样的眼色看你,要知道冬子现在跟你已经水火不相容了。”
“你在威胁我?”
潘少岳的声音听上去变得略微的低哑,可能是太过压抑自己过激的情绪导致的。
“我有没有在威胁你你自己清楚,做人要问心无愧,既然你心里有鬼,无论我说什么,在你听来,都带了含沙射影的成分。”
许愿不急不缓地道,倒是镇定,潘少岳情绪的起伏,对她而言,就是最大的激励,她最恨他态度冷淡地对自己,仿若自己对他而言,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值。
她本来傻傻地迷恋他,什么都为他考虑,可是倒头来呢?什么也没得到。自己还留了一手,那一手就是那个孩子,潘少岳不知道她怀了身孕,后来孩子六个月的时候她告诉潘少岳,自己怀了他的孩子,潘少岳先是错愕,回过神来便毫不留情地要求她打掉。
六个月大的孩子,器官都成形了,打掉孩子,母体也有生命危险,他最爱的还是他自己。
他对这个孩子一点爱也没,那可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在潘少岳心中,他的声誉,他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潘冬子,也是他的心头肉。
想当初,自己跟潘冬子在一起,刻意让他知道的时候,他恨不得杀了自己,可是他又不敢让他的儿子知道。
她生孩子的那些时日,是东躲西藏的,潘少岳暗地里在找她,她不是不清楚,那样落魄的日子里,她没一觉睡得安稳,住的地方都选那些偏僻没有人烟的地方,就怕被逮住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