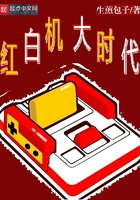不可重来的缘分(序)
母亲这辈子对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一句是多吃点,一句是多穿点。
15岁的时候,觉得这两句话特别唠叨,特别多余。人活着,总是要吃要穿的,我都那么大的人了,难道还不知道吃穿么?
25岁的时候,初尝社会的人世沧桑和情态悲凉,才渐然知道这世上,只有母亲才会如此耐心地重复这两句话,也只有母亲才不会端着酒杯让你多喝点。
于是,临近三十的时候,每每听到母亲在电话的末尾说起这两句话,总忍不住两眼浪潮。
母亲说,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想去看看北京的天安门和长城。以前听到这句话,总是忍不住大笑,心里觉得她土气。现在别说听到这句话,就连想到这句话,都禁不住热泪翻涌。她16岁开始为人母,尝遍生活的苦难和丧夫的绝望。她把一切都给了儿子。可儿子现在都那么大了,却连这个小小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提议春天带她去玉樱潭赏花,她说春天家里农活多;提议夏天带她去什刹海游湖,她说夏天太热;提议秋天带她去看香山红叶,她说秋天人多;提议冬天带她去长城观雪,她说冬天太冷……
她心里永远记挂着儿子。她看着儿子成天对着电脑写作,一字一句,来之不易。儿子大了,得结婚,得育女,得承担一个家庭的重担,得为生活忙碌奔走。她心疼儿子的每一分钱,她觉得那每一分钱都是儿子的血汗。
因此,即便她此生仅有这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肯为了儿子曲意逢迎,委屈成全。
但她不懂,对于儿子来说,这样的成全,便是在逼儿子不孝。她的温慈和溺爱,在儿子心里埋下了一块合也合不上的伤疤。
儿子想毫无保留地对她好,而她,却只肯远远地站在那儿,微笑凝视儿子的幸福。她不知道,在她努力不想成为儿子包袱的时候,已经朝儿子的心口重重地推下了一块巨石。
躺在床上翻唐诗,无意读到儿时念过的句子:“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是唐代诗人张籍的《秋思》和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因为深有感触,所以将这两首诗里的一些字词提作了该书的小辑名。
这是2012年的春天,很久没有这么安静过了。坐在窗前写这本书的序言,写着写着,忽然不知该说点什么。
之前并不懂得,久习佛经之后,才开始明白,母子,兄妹,父女,祖孙,等等,其实,都是一场不可重来的缘分。不管这辈子你爱不爱他,对他用不用心,下辈子都不可能再有碰面的机会了。
母子
四十岁以后,她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唠叨。她和所有上了年纪的母亲一样,多疑,悲观,小性,容不得儿子的半点忤逆。
我只能顺着她,哄着她,像对待孩子一样宠着她。
年岁愈增,她越是变得敏感。似乎,她正在渐渐丧失一个母亲对儿子的体谅与宽容。
偶尔累了,坐在沙发上不想说话,她偏要过来与你搭讪。没完没了地唠叨,没头没尾地数落。
人到底是有脾气的。但成年儿子对母亲的怒吼,总是会在片刻之后,瞬间掀起心里的愧疚狂澜。
我知道她这些年的不易。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两个苦命的孩子,无怨无悔地走到了今天。
她把生命里可以给出的爱,全都给了我和弟弟。只是同时,她也把生命里所有的敏感,都留在了心底。
虽说母爱无私,可天底下,有哪位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孝顺体恤?她不需要回报,但却渴望得到儿子的感恩之心。她走得越苦,就越是希望孩子能记得她的拳拳之爱。
偶尔她会落泪。独自一人坐在暗沉沉的客厅里,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儿子偶然的盛怒,在她看来,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忤逆。
我不说话,也陪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没有灯光的客厅里。鼓足勇气叫她一声,见她不应,也便没了那份继续喊出的坚定。
片刻后,她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唠叨。窸窸窣窣,像是空气中的蚊蝇拍翅,又像是半夜窗外若有似无的风声。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倾诉的对象也越来越明显。
可惜,我是她的大儿子。怀胎十月,她在给我血肉身躯的同时,也一并把那不可扭转的怪脾气赐给了我。
我们再一次发生了剧烈的争执。
这次,她似乎彻底绝望了。不再等待儿子的无声愧疚,也不再叙说往事的风波暗伤,独自起身摔门而去,惟留那呼呼渗进的冷风。
我们冷战了整整三天。她不看我写的深情文字,而我,亦不再吃她精心准备的饭菜。我俩像隔世的仇人,在这一辈子,处心积虑地让对方难受。
再后来,朋友的母亲陡然去世,我只得连夜赶去探望。
他母亲也是个苦人儿。操劳一辈子,还没等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被病痛夺取了性命。
回来的时候,经过母亲操持的那块田地,忽然忍不住大哭起来。心里想着,总觉有千般不是,也不该那般待她。
多少人,燃香祈佛,跪地拜天,都不能完完整整地做一世母子,为何,我有此福缘,还不懂得珍惜呢?
要知道,母子,本就是一场不可重来的缘分。
忘记我,便是你最好的报答
一
2004年10月18日,我和你相识正好三个月。这一天,你虽然还叫我叔叔,但却送了我一件让人热泪盈眶的礼物。
你把所有作业本上的名字都划掉了。你说你以后再也不叫王小贝了,从今天开始,你正式跟我姓许,叫许多多。
我有点疑惑,问你为什么要叫多多。你说自从和我在一起,你就忽然觉得活着有了意义。于是,你开始有了许多愿望,许多幻想。
王小贝,你这个死丫头,又把我弄哭了。你好像很喜欢做这些让人矫情的事儿。
2004年7月18日,那是我第一次在博爱孤儿院见到你。
孤儿院的老师说,你的父母是在一场洪水中丧生的,他们像两座石雕一样举着家里洗衣服用的大铁盆,死死不肯松开,而你,就安然沉睡在这个温馨的铁盆里。
听说,那是1998年的湖南。肆虐无情的洪水像猛兽一样席卷了湘、鄂、赣三省。一片汪洋,哀声震地。
抗洪救险的军人把你从铁盆里抱出来时,你尚且还在甜美的睡梦中微笑。你的衣兜里还揣着你母亲给你放进的奶瓶。
你父母的双手死死扣着铁盆边缘,像要融进这冰冷的金属里。善后的军人们始终掰不开他们的手,没有办法,为了能让他们入土为安,只能动用工具把手指撬起。
那时你还小,不到一岁。所有关于父母的记忆,你只能靠听闻来缓慢拼凑。你甚至不知道他们葬在哪里。
第一次听说你的故事,我就被感动了。因此,我决定去看看你。
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六岁半了,会背很多古诗,会写很多字。只是,坐在草地上的你一言不发,远远看着天际。你那股从纯真心灵里透出的忧伤,一下子就把衷情写作的我给俘虏了。
王小贝,就在那一秒,我决定收养你,并带你离开这块伤心的土地,远赴美丽的云南。
二
你仍旧很少说话,你从不向我索要玩具,更不会像其他小孩一样毫无缘由地撒泼。大多时候,你安静得像一颗绿色的豆子。
兴许是职业的缘故,我特别喜欢安静。由此,我更爱你了。甚至,我觉得我们俩是命中注定的父女。那骨子里透出的默契,让我们即使在无言的世界里静坐,也从不觉得尴尬和孤独。
带你去丽江看雪山,是你笑得最多的时候。那是六月的滇西,百花盛放,流光满地。
高原上呼啸的大风把你的头发吹乱。但你仍然坚持不关车窗。你把头手伸出窗外,任凭这广袤的世界将你的衣衫鼓成风帆。
我给你拍照,帮你打扮,将你搂入怀中。
在蓝月湖,你兴奋得乱成一团。你说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蓝色的天然湖。
你要在湖中的岩石中留影。我依了你。可就在我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你一个趔趄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湖水里。
我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冰冷的湖水里。我睁大眼睛在水中寻你。
你死死地抱着我,怎么也不肯松开,我难以施展动作,只好高呼救命。
离开水面的一瞬间,你忽然在我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也许,你在水中想到了1998年的湖南,想到了你的父亲,还有那无处可寻的家园。
我帮你洗澡,帮你换上干净的衣服,像父亲一样将你抱上温软的大床。那是我第一次告诉你,如果你落水了,一定不要紧张,更不要在水里吸气,你要憋足了劲等着别人救你。你要放松,不要抱住人家的身体,不然连救你的人都会有危险。
余惧未消,你的身体一直在被窝里颤抖。
我给你说《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故事,直到你沉沉睡去,天边露白。
第二天醒来,我正趴在你的床沿上。找不到你,我急坏了。我给宾馆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让他们帮忙找你。
就在我们忙得焦头烂额到时候,你呼哧呼哧地出现了,鼻翼挂满汗珠,手里提着豆浆油条。
我阴沉着脸刚要骂你,你就被吓哭了,叔叔,叔叔,我只是想给你买豆浆油条,你昨天说了,你想吃豆浆油条,我跑了很久才找到……
我把你放在怀里,像个慈祥的父亲一样抚摸你,轻拍你,并教你以后不管去哪里都一定要事先告诉我。
三
2004年11月11日,在你的强烈要求下,我只好带你去公安局更名。
许多多,许多多,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这么叫你,你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答应我,说这个名字真好听。
不知你从哪里听来的,竟然知道那天是光棍节。你用你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说要为我庆祝,希望我来年得到幸福和爱情。
丫头,我又被你感动了。因为你那一句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这句话,你应该是在我未完稿的小说里看到的。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写一些情情爱爱的约稿,你受此影响,思想早熟,我非常难过。
但你那句话,的确打动了我。因为我觉得,那是只有女儿对父亲才能作出的认可。
你没问我为何单身,我也没告诉你成年人的爱情世界有多么复杂。你迟早会长大,会经历,会懂。
2006年春节,我开车带你回云南老家过年。不幸,中途刹车失灵。没办法,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我只能尽可能减速并让保险杆与山体相撞,以此阻止车身继续前行。
虽然你已经跳到后排的座位上趴好,但巨大的震动还是使你昏厥了。
再后来,你去了北京,住在我一个朋友家里。我们一周一次电话。
你问我为什么要把送去北京,我说,那里教育条件好,你能学到更多更全面的知识。我说我会去看你,只是最近工作比较忙,等闲下来我就直接飞过去。
你答应我会好好听那位叔叔的话,会等我来北京接你,会好好学习,争取考第一名。
我很高兴,我把你去丽江所有的照片都冲洗出来了,还给你邮了一份。收到照片的当夜,你主动给我打了电话,结果,我把你骂了一通。
你不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吗?你不知道我写作的时候需要安静吗?谁让你给我打电话的?我跟你说了很多次,每周一次电话,我会在周六的时候主动给你打,听到没?
你在电话那头默然不语,我隐约听到了眼泪落下的啪啪声。我忽然心软了,想要说想你,却咬牙挂断了电话。
四
听朋友说,初到北京,你有众多不适。教学方法的殊异,心情的沉闷,让你的成绩一落千丈。
你从来不和我的朋友说话,你吃完饭就去念书,念书回来就进房间睡觉,如果他不问你,你甚至可以一个月也不跟他说一个字。
有一次,他彻底恼了,半个月没给你早餐钱,就等你开口问他要。结果,你宁肯半个月不吃早餐,饿着肚子上学,也不开口问他要半分钱。甚至学校要交杂费你都从来不告诉他,最后没办法,老师只好主动给他打电话。
期中考试,你成绩位列倒数。朋友气得暴跳如雷,把你狠狠训了一通。你不说话,也不哭。
沉默了很久,你终于开口,我在这里,只是为了等我叔叔来接我。
朋友怒了,叽里呱啦说了半天,你竟然只回那么冷冰冰一句。于是,他一时没忍住说,就你这样他还来接你?成绩都倒数了,还有什么接的必要?要是我自己的女儿这样,我直接不要她了!
就因为他这句无心之言,你哭了,胡说!我叔叔不会不要我的!不会的!
一晚上,你都在说这一句话。你说我不会不要你。最后,你累了,在嘤嘤的啜泣中慢慢睡去。
第二天,你彻底变了一个人。你开始认真看书,写字,学习地道的北京话。
2007年12月30日,星期天晚,你用地道的北京话跟我说你考了第一名,问我能不能去北京看看你的成绩通知单。
我说很忙,暂时脱不开身,如果你下个学期期末也还能考第一名的话,那我就去看你。
你说,好,那你现在就可以订票了,明年我肯定也是第一名!
就这样,我们之间有了一个约定。
五
2008年夏,你真的考了第一名。
抱歉,多多,直到秋季开学,我都没能去北京看你。
开学当晚,你给我主动打了最后一个电话。你在电话里说,叔叔,我遵守我们的承诺考了第一名,但你没来看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我以后也不会纠缠你了。
你的语调冷静得让我有些吃惊。我都忘了,多多,今年你都十岁半了,估计都快到和我一般高了。
我想去北京看你,但是我不能。因为2006年的那场车祸,我彻底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我可以坐在轮椅上写字,可以给你打电话,却不能独自去北京看你。
我自己都不知道,北京的地铁站和公交车站,有没有残障人士的专用席位。我成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说话,不见朋友,更是很少外出。
我比以前更沉默了。除了和你一周一次的电话之外,我几乎都是在沉默中度过。你的耳朵和我的耳朵一样,都是彼此声音最忠实的听众。
2008年冬天,我从昆明回到了大理。多多,这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我曾在这里踏下油门带着你去丽江,去蓝月湖,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说要带你去我老家看看,可结果,不但没去成,还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以前总嫌咱们家门口的邮筒低,这次回来,它竟忽然高了。我必须一只手艰难地撑在轮椅上用另一只手使劲够它,才能打开。
信件忽然像雪花一样飘洒下来。邮戳全是来自北京。
我一封封打开它们,小心翼翼,像是在拆阅自己的生命。读着读着,忽然就哭了。我真没想到,多多,你会给我写那么多信。
你说,叔叔,如果电话会打扰到你,那么,我就给我写信好了,把想说的话都写在信里,等你有时间再打开看。你看完了,知道就好,也不用给我回复,这样,就不会打扰到你,是吧?
你把我朋友给你的每一分钱都用来悄悄买了信封和邮票。你开心的时候给我写信,悲伤的时候给我写信,思念的时候给我写信,无聊的时候也给我写信。你把一切关于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你说对我不能有任何秘密。
六
你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也再没给我写过信。
有的时候,写累了,我就把轮椅摇出去,坐在门口的邮筒下面等。我总觉得,有一天会再次收到你的来信。
我想给你打电话,但又怕这电话会在你的心间掀起滔天狂澜。我害怕,你会因为我的电话而成绩下降,你会因为我的电话而对新的家冷冷冰冰,我怕这怕那,既想把你送到一个光明的渡口,又怕那条赶来渡口接你的船会开的太快,使我来不及说完告别该说的话,流完告别该流的泪。
思念如同毒药。终于,我忍不住给你打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