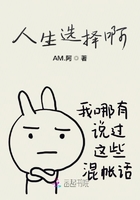一
1路车到了柳家就停下,不再往前走了,这里是终点站。下了公交车没有走几步,我在路边等候拉客的三轮摩托,找了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师傅。这种车不打表,经过讨价还价,他答应往返十元钱,拉我去秦董姜镇天主教堂。我坐在司机的旁边,封闭的三轮摩托空间窄小,摇落车窗,让清新的风流了进来,平坦的永莘公路上车辆很少,短短的几天中,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已经过小满,麦子正是灌浆的季节,疯狂地生长,很少有人干活,路边的小商店、饭店、物流、宾馆、停车场进出的人,比田里的人还多。沿途的墙上涂着“钱江摩托”“阳春啤酒”的广告,商业的气息侵蚀平静的生活。三轮摩托向右拐,驶向一条不宽的乡间公路,就看到那片耀眼的红瓦屋顶。
在五月的乡村,我来到一座“红瓦顶的教堂”前,关于它的资料稀少,人一茬茬地走了。只是这近百年的建筑,还在发出生命的呼吸。当地的老滨县人,管教堂叫“红房子”,因为当初建教堂时,它的顶是红瓦,而周围的村庄是灰色的小片瓦。水泥方形门柱子,上端是四面坡形的尖顶,红纸金字的对联,被风雨抽打得剥落,露出去年圣诞节时,教堂贴的白纸黑字的对联。大铁门顶端的铁质十字架伸向天空,我犹豫一下,没有敲响关闭的大铁门。
1991年的秋天,在瑟瑟的冷风中,马路上有了落叶。我住在大杂院的一排平房中,门前有一株柳树,叶子变得枯黄,枝子在风中摆动。读书累了的时候,站在窗前,看着叶子在空中坠落。一条通路邻居们走来走去,院子中间的公共水池,时间一长水嘴关不严实,经常滴滴嗒嗒地漏水。那时迷恋于文学创作,在小说中编织一个个故事,填满稿纸上的空格。我四处找书、读书、写作,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在政协工作,送我一本《滨州文史资料》第三辑。我读到了王洪祥、张锡英的《天主教在滨州》一文,第一次知道滨州有这么一座教堂,年轻时有太多的幻想,也不懂得什么是历史。《滨州文史资料》被压在书堆的深处,前不久在整里书的时候,它被翻了出来。有一次在民间工艺家张洪庆的书房聊天,他展示收藏的鲁北的民间剪纸、手工的枕套,在浓重的历史气氛中,我无意中谈起秦董姜镇天主教堂,他却说老家篦子张就在附近,1962年,他在教堂里上的初中,当时叫滨县第一中学。对于教堂里的一切,窗子朝哪个方向开,门是不是后改造的都了如指掌。我凭着多年前读得那点资料的记忆,询问去教堂的路线和地理方位,略略解教堂的历史和状况。
从那时开始,我搜集有关教堂的资料,对这么偏僻的土地上,怎么会有天主教这个西方的宗教,为何选中这个地方传播?
据新编《滨州市志》记载,19世纪末,天主教传入黄河以北。首先在今滨北办事处的李在天村活动,后传至城北秦董姜村,逐渐扩至滨城境内数十个村庄。李在天堂口初建时,由德国籍葛神甫主持,后来由本村李玉功接管。姜家堂口建立后,取代李在天堂口,成为管理滨县天主教一切事宜的总堂。上则接受周村教区主教公署的领导。
姜家堂口第一位主持为李神甫,后来继任者有沾化籍的冯神甫、宗神甫,美国籍的顾神甫。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籍神甫司道远接替顾神甫主持滨县教务。1940年,在司道远主持下,建起了今天尚存的大礼拜堂。这个时期,天主教在滨境有了很大发展,在二十余个村庄建了堂口和分堂,教徒发展到1500人左右。教会除正常的宗教活动以外,还在滨城境内创办了一些社会福利事业。1940年姜家总堂创办医院一所,内外科兼备。同时,创办高等小学一所,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在校生最多时在200人左右。此外滨境各分堂也创办了多处小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11月,两位神甫撤离滨境。从此,天主教在滨境内的活动衰落下去。
这只是简单的概略,并未对李神甫,以及后来继任者有沾化籍的冯神甫、宗神甫,美国籍的顾神甫的详细记载。我们只能凭想象,为他们描绘出一个献身宗教的圣徒的形象。现在惟一可触摸的就是这座活着的教堂,贮藏了历史中的声音、色彩、光线和情节。二米多高的院墙,切断远眺的目光。墙上大红体的标语,写着“自强不息,追求卓越”。这时一只鹊雀,闹喳喳地在天空飞过,向远处的村庄疾行。
二
我大声地喊一句:“有人吗?”瞬间消失在空气里。食指弯曲伸出时,我的指尖微微动了一下,还是敲响大铁门,铁皮声传出很远,院子里不见任何反应,隔着门上的铁栅栏,向院子里张望,我的目光变得焦急。院门的马路对面有一家小商店,走出一个老年妇女,衣着装扮普通。她热情地询问一番,我把记者证递过去,简单地介绍此次来的目的。她看了一下,知道我是来看教堂的,她说她就是教堂的管理员,并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铁门旁的侧门一开,我踩着砖铺的甬路,走进在资料上读过的秦董姜教堂。
从路往前走到头,现在是一座学校,正是上课的时间,听到读书声。迎面的墙上一个大十字架,上面书写一行“耶稣爱你”。
教堂坐西朝东,穹窿式尖顶上,有一十字架,下面“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被时间浸漶得模糊,不仔细地辨认,分不出笔划,文革期间绘上的红五星,还是那样的清晰。革命和宗教在墙上共存了多年,当新升的太阳从东方出来,照在神圣的十字架上,也照在红五星上。大门两侧有上下两层尖形券窗子,有一种向上的动势,如同举向天堂的手。乡村的教堂在大地的深处,毫无华丽的装饰,多一份虔诚。在这里人的情感变得虔诚,耶稣的圣像激发了情感。
偶尔有参观者走进教堂,他们是宗教的旅游者,不是虔诚的教徒。教堂里的净手池,跪凳和精致的雕塑,让他们浮躁的心,有了震动的愉悦,这一切对于他们就够了。当年能工巧匠,凭借一双手,使青砖料石有了生命,有了信仰。
我未来得及问清姓名,她打开大铁门,我们进入了秦董姜镇天主教堂。红门被推开,一群阳光涌了进去,狭长的尖形券窗上,彩色玻璃都损坏了,换上一般的玻璃。阳光热烈地挤进,采光充分主厅装饰简单,却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氛。
九十多年前,李神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为什么来到古老的凤凰城,这块偏僻的乡村传教,建筑这座教堂。他是坐车子来的,还是徒步而行,鞋子上落满灰尘,也无法吓退他传教的决心。
当初设计教堂的建筑师,但决不会想衰败的样子。教堂经历战争和政治运动都未拆毁掉,它艰难地存下来。我走近教堂,在败落的建筑间找寻细节,通过微小的发现,复原历史的真实。我是闯入者,站在教堂前的思考,目光的游移,打破了凝固的往日。我选择最佳角度,切入教堂的时间里,它是一卷活着的档案。
在正门的右侧,有一人多宽的木楼梯,贴墙盘绕而上。二层的木的阁楼,向外悬空。年代久远了,木质的楼板保养得不好,变黑的木板块,踩上去吱吱作响,再也承受不了超大型负荷的力量。我走在上面,不敢放重脚步,怕哪一只脚稍不注意,破坏了脆弱的地板。教堂的管理员指着二层阁楼,称它为“唱经台”,作为主日乐队演奏的地方。1972年,她还是扎着辫子的小姑娘,青春的脸上,毫无人生风雨的敲打。她装满革命的豪情,脸上化了浓妆,和同学们走上楼梯,来到二层的木楼上。革命点燃情感的火炬。她扮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剧情中提示道:“李奶奶虔诚地擦着号志灯。铁梅凝神地注视。”李奶奶说:“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戏中李奶奶虔诚对待革命,她青春的声音里少了沧桑感,在大厅里徘徊。这里上演的是革命的节目,凳子上坐的接班人,不是虔诚的教徒。主祭台上受难的耶稣,早已被砸烂,让红色的标语替代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2007年,她却成为了教徒,教堂的守护者。我在墙上的《秦董姜镇天主教堂堂管会》的名单上,找到她的名字——会长赵宝恩。她是一名当地的普通妇女,三年前,她家在教堂外一百多米的马路对面,盖了一幢五间的砖瓦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她正式加入教会,用一双劳动者的手,拈开《圣经》的每一页。多少年后,经历人生的磨砺,她竟然成为天主教徒,被神父委任担当会长。
三
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指出:“然而,真正的意义所在,并没有从建筑师用立面和平面图构筑的密闭世界中,或他们的自我审美表述中体现出多少。使我越来越感兴趣的并不是建筑的外形、窗户的形状或屋顶的形式,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建筑为何建成和它们如何建成,对我而言它们的含义远比它们的外形更重要。”建筑背后深藏的东西这就是历史了,建筑和权力紧密相连,1949年,这座教堂被渤海行署改建成师范学校。1958年,改为滨县一中,后成为滨县教师进修学校。如果当初没有被改建师范学校,
中国京剧院集体改编:《红灯记》,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1版。
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无法回答。1996年7月,从师专毕业的大学生,带着青春的豪情,踏着到处是坑的破烂公路,来到绿树簇拥中的村庄,村中的教堂就是滨县一中。“早上六点起床,做一点早饭,听一听鸟儿的欢唱,”便走上七尺讲台。2010年,他在博客中写道:“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老教堂也受到了洗礼,四周的耶稣像都被红卫兵给破了四旧,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经过了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字迹还和刚写上去的一样,那时的人们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伟人的敬爱之心。里面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口号或者是“打倒某某”。据老教师介绍,这墙上都能找到当时校长的名字,当然都是被打倒的对象。还有一位校长因为受不了批斗,在教堂里面悬梁自尽。”2004年,他离开滨县一中,离开教堂,到当地的另一家学校任教。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怀念那儿,是怀念一种生活,是一种对逝去生活方式的留念。”
修女姜万礼和信徒田德荣有一张黑白的合影,那是寒冷的季节,身后的小树上没有一点绿色,地上枯黄的野草,背景就是破旧的秦董姜镇天主教堂。两个清瘦的老太太都是缠足的小脚,姜万礼一生未结婚,教徒们称为“姜大姑”。她是当地所剩无几的修女之一,家里几代人是教徒,她也从小开始信奉天主。14岁的那一年,一个中国神父介绍,她去了惠民县一家教会学校上学。在校其间学过医学,毕业后,姜万礼先回到了当地教书,又去沾化县一所教会学校任教。一边教学,一边传教,后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她便再次返回老家秦董姜村教书,同时传教,方便照顾老人。
2010年5月22日,我又一次来到教堂,这次去并不是敲响大铁门,而是走进教徒赵会长的小商店里。赵会长正在吃午饭,认出了我们前几天来过,热情地接待,客气地把连椅让给我,自己坐在马扎上。第二次见面是在商品包围中交谈的,我的思绪在过去的年代里转悠,想调查到真实的事情,透过窗子能看到教堂的一角。
我想见见这位“姜大姑”,赵会长说,她去年就升天堂了。接着是一段时间的沉默,窗子投进的阳光不是那么强烈,门被推开了,一群买东西的孩子打破寂静。我在连椅边上,看到黑皮的《圣经》,我触抚一下,翻开一页,“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天主将光称为“昼”,称黑暗为“夜”。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我抬头向窗外望去,阳光在天空“运行”,照在旧的教堂上。明天是5月23日,赵会长邀请我来做礼拜,听一听神甫传道。离开赵会长的小商店,我隔着那道墙,注视教堂的红瓦顶,我真想再次走进去,一个人坐在教凳上,听着天主的声音。
法国雕塑家罗丹走近大教堂,他的步子缓慢,感受到圣灵的风吹来。他在教堂的外面徘徊,注视教堂的每一处细节,在柔和的阴影中发现纯朴的美。罗丹说:“大教堂里没有时间,有的只是永恒。黑夜赋予这里的和谐比白昼更多。大教堂正是为黑夜而造。白昼向大教堂倾洒光明,不正如同胜利者将它们控制太严了吗?”人在教堂里倾听圣言,丢弃人间烦杂的物事,所以罗丹说这里毫无时间的概念,只有永恒的存在。2009年6月,我到金华开笔会,最后一天时,文友们纷纷离去。我一个人顶着雨,在街头寻找书店,在书城里我遇到罗丹的《法国大教堂》,这本书,我早在1996年就读过。窗外下着碎雨,南方的潮湿黏贴在身上,书城里的空气不流通,汗水洇透T恤衫,我买下仅有的两本《法国大教堂》。
2010年3月6日,我在新书的后记中写道:“2010年,春节期间,我和高淳海每天到山大老校里散步,学生们放假,诺大的校园时变得空荡,我们在清寒的空气中,一边走,一边交谈。聊的多是人生和读书,两年的研究生生活,高淳海的眼界开阔,思想成熟了,有新思想和对读书的理解,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一些意见,非常准确。高淳海推荐了几本重要的书,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保罗·利科的《解释的冲突》,维克多·E·弗兰克尔的《追寻生命的意义》。我们在操场破旧的塑胶跑道上,一圈圈地散步,洪楼教堂的钟声正点响起,轰起一群大鸟儿,在天空叫着,向远方飞去。”我们每天在教堂外的跑道上散步,听悠悠的钟声,撕破城市的喧闹声,宗教用它神圣和庄严,在浮躁中切出一块圣地,让心灵有宁静和忏悔的地方,静穆与安谧之中人变得平静,所有的杂乱悄然退去。
大片的麦地簇拥着教堂,远处是村庄和高耸的电塔,我拍下成长的麦地,镜头中记下这个日子。监视器中装满了绿色,村庄里的教徒,就是在这麦地边的路走过,抖落鞋上的泥土,进入红瓦顶的教堂。
坐上三轮摩托,身后的教堂远去了,我回过头,透过不大的后窗子,看了一眼红瓦,行了一个注目礼。
2009年5月22日于抱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