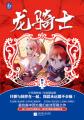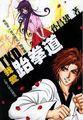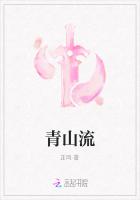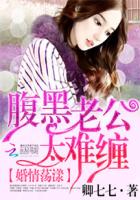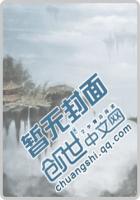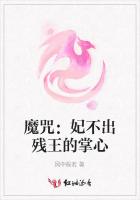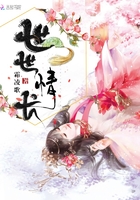奥涅金更具典型性与概括性,他较接近毕巧林这一型,对叔父临死前的敷衍,学问一知半解,善于插科打诨,只对化妆打扮感兴趣,周旋在少女与妇人之中,在花天酒地的上流社会如鱼得水,甚至对寻花问柳都感到厌倦。乍一看,极像清客与花花公子的杂交品种。事实上,他对这种人生内心非常排斥:“今天和昨天没有差异,一样的单调,一样的繁忙。天天在游乐,随心所欲,情场的胜利足够他夸口。然而,我的奥涅金可真感乐趣?……他的心里可真是那么安憩?”“不是的。他的感情早已冷却,世俗的烦嚣已使他厌倦”“总之,是那俄国人的郁闷多多少少地侵蚀了他。活与不活,仿佛都不在意”。
于是像维特一样,“‘悒郁’这毛病像是影子,或踏实的发妻,也守着他、追着他、把他跟定”。
这些人无法施展抱负的现状如同毒素一样,在体内蔓延,连爱情都经不起这种力量的侵蚀,便如同官场不得志的一样,寄情山水,佯狂装疯,在醇酒与女人中周旋,把生命如麝香一样挥发。他们尝试着反抗,却不想四周是厚厚的墙壁,原来看似松松垮垮的“这套东西是机器缝的”(易卜生的《群魔》),却没有勇气像欧士华一样给自己藏好十二颗吗啡丸子。
他们都患有同一种病症,有着不同的个体差异,虽然奥涅金是花花公子,奥勃洛莫夫是个懒汉,别里托夫是个稍嫌怯懦的人,罗亭只是空想家,但不妨碍都有作为“多余的人”的本质。他们找不准在世界的位置,没办法与世俗妥协,甘愿屈服于一种幸福但却是妥帖凡俗的人生;想要战斗,又寻不到同志与根据地,根本是寻求不到任何的出路。于是生命中可贵的一切,聪明才智,都白白地耗费了,甚至爱情也成为殉葬品。
所以,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生命都是以也只能以这样的节奏完成,这既是因又是果,既是表象又是深层:
“我没有职业,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无所用心,总是感到烦闷无聊”“学习么时断时续,计划么一个接着一个,却从来没有实现;有时我也吃喝玩乐,不过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阿道尔夫》)
“他冷淡下来的速度比他当初发生兴趣的速度还要快,这本书他一旦扔下来就永远不会再拿起来了。”(《奥勃洛莫夫》)
“总觉得缺点儿什么,精力集中不起来:他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抽雪茄,喝咖啡,想了很久,琢磨今天应该先干什么,是看书呢,还是出去散步?”(《谁之罪》)
难道这种萎靡不振的状况要完全归罪于他们,完全归罪到浮华不切实际的个性中去吗?或者说他们的痛苦是不真切的,只是无病呻吟而已,与社会的联结并非那样的紧密?问题的深刻性在于,这些多余的人,包括“奥涅金的痛苦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真实实的痛苦。苦恼的原因在于他不满意周围的现实。”(斯罗尼姆斯基)从主观描写上,别林斯基也说过:“他所刻画的人物,不是坏人,甚至大部分都是好人,他们折磨、迫害自己和亲人,常常并不抱有坏的企图,而是抱有好的企图,不是由于恶毒,而是由于无知。甚至那些因为感情猥琐,行为下流而令人反感的人物,作者也不是作为恶的天性的牺牲,而是作为他们自身无知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牺牲来描写的”从受到痛苦的真切程度与社会意义来说,他们更值得同情而不是一味的责难。
在奥涅金想到书中寻求慰藉、填补灵魂空虚时,翻开书来看,却发现“不是信口胡诌,就是谎话连篇,有的没头脑,有的没心肺,本本是俗套,一切囿于成见,新曲不过是老调的重弹。”
“一位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看到一个如此做作、如此虚假的社会而感到万分惊讶,这与其说意味着他的性情乖戾,倒不如说表现出他的天然本性。再说,这样的世界丝毫也没有什么可怕,它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悄无声息,却施展出巨大的影响,而且用不了多久,它便会按照那种普遍的模式磨砺我们。我们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大吃一惊,反而会在这种新的环境里感到如鱼得水,就好像人们最终会在人声鼎沸的剧场里自由自在地呼吸,而他们刚刚走进这个地方时却闷得透不过气来。”(引自《阿道尔夫》)
“……生活!这种生活!从那里能找到什么?头脑和心灵的需要吗?你看看,这些东西有中心吗?围着什么转呢?根本没有中心,没有任何深刻的切中要害的东西。这些社会成员都是僵尸,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人,比我还糟!他们在生活中跟着什么走呢?他们倒是没躺着,天天像一群苍蝇似的乱飞,有什么益处呢?……我躺在自己家里,没有用纸牌毒害自己的头脑,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们更该受到责备呢?”
“我们的优秀青年都在干什么?……天天虚度光阴!可是,你看,他们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神气得使人莫名其妙,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光打量谁不像他们那样着装,没有他们那样的门第和封号……不仅青年如此,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吧!……他们既然是这样一种人,为什么还要聚会?为什么彼此紧紧地握手?没有一回真心的笑过,没能有一丝好感!都在拼命争名争位。……这叫什么生活?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中能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教益?”
“……我的生命是从熄灭开始的。说也奇怪,可事实却如此!从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在熄灭下去。我在衙门里伏案写公文的时候,就开始熄灭了……在看到友谊是由毫无目的、彼此毫无好感的聚会维系着的时候,又继续熄灭下去。与米娜交往的日子我也在熄灭,浪费精力……在涅瓦大街上那些穿海狸皮领和浣熊皮大衣的人中间心情沮丧、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同样熄灭下去。……或许是我不懂得这种生活,或许是它毫无意义,怎样可以过得有意义些,我又不知道,又没有看过,更没有人向我指出。你像慧星一样,出现的时候光华四射,但瞬间即逝。我渐渐忘却这一切,只有熄灭下去……”(以上三段引自《奥勃洛莫夫》)
在批评现实生活与自我省察方面,多余的人都有不可替代的深刻性,能够一针见血地看到社会的弊端与自我的局限。只不过这些认识并没有使他们能够着手去改变,或囿于性格,或囿于环境,或囿于少有才干,这些想法最终都没有变成向上的力量,把别人或者仅仅自我从生活的泥沼中救赎出来。
“是的,天赋给予我许多东西;但是,我将不会做成任何与我的能力相配的事,也不会在身后留下任何有益的痕迹,就这么死去。”
“在我身上有一种愚蠢的坦率直言的性格,喋喋不休的习惯”
“要是我真的能献身于这种事业,最终战胜自己的惰性,那多好呀……但是不会的!我仍将是一个与目前一样的一事无成的人……遇到第一个障碍——我就整个儿散架了……”
“是的,我应该行动。我不应该埋没自己的才能,如果我是有才能的话;我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尽浪费在空谈上,浪费在无聊、无用的废话上,浪费在空口说白话上……”(以上引自《罗亭》)
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生活在自相矛盾中,这自欺欺人的一面迟早要露出它难以取信于人的一面:
“看来,他只是口头上说要寻找纯真和忠诚的心灵。”
“是的,他像冰一样冷,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装出一副火热的样子”。
“罗亭说的话最终仍然是话,永远也不会变成行动——然而就这些话却会搅乱、毁灭年轻人的心。”
“问题就在于,他甚至还不像达尔杜弗。那个达尔杜弗至少还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喋喋不休所苦的罗亭,只好在空谈中误了自己的一生,像我们做噩梦时,很清醒地感觉到却无法摆脱梦魇,宁愿让这些咬噬光自己的热情与精力。
奥勃洛莫夫对一般仕途的人生道路持否定态度:“对世上其他的东西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他却会出人头地,渐渐把实权掌握到手里,青云直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仕途!人在其中:人的智慧、意愿、情感有多大用处?不过摆设而已!活了一生一世,身上有许多东西还从来没有动过……然而从十二点到五点他在衙门办公,从八点到十二点在家里办公——可怜!”但自己正是犯了小过失,害怕上司的责罚主动辞去公务员的生活,只好一天到晚在家里,靠老家土地农奴上缴的赋税,过着无所事事、病入膏肓的生活。别里托夫也因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受到别人的倾轧与排挤,退出公务员队伍,他试图对农奴制度用一些小小的改变,马上所有贵族阶层就意识到:“他不能和他们共利益,他们和他的利益也无法一致,因此他们憎恨他,他们觉得别利托夫是他们的对立面,是揭露他们生活的,是反对他们的生活制度的”;奥涅金试图对田庄进行改革,将古老的徭役制度改为赋税,也同样受到其他地主的排斥。生活已经把他们逼到狭缝里面啦,因为无金钱之虞,所以变成了无所事事的人。
事事都遇到挫折,于是他们多余的热情自然会转移到语言上,向着他们感兴趣的男女宣扬一些热情的生活,描绘出一幅美景作为替代品,并陶醉其中。事实上,这些小说中描述的女性,都或多或少有着多余的人一样的苦闷,所以较其他人更深的理解这些多余人。柳博尼卡的痛苦其实也是利莎的痛苦,同时也是达吉亚娜的痛苦。她们敏感而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可是这两位女性比多余的人来讲,多一点作为女人基于直觉的热情,不容易被理智轻易说服熄灭的热情。对爱情方面有女性的坚定与执著,形象上更胜一筹。
叶连娜“她的心灵在孤独中燃烧,又在孤独中熄灭,她拼命想挣脱,犹如一只笼中之鸟,然而笼子并不存在:没有人束缚她,没有人限制她,可她还是在苦苦挣扎着、煎熬着。有时她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甚至害怕自己。她觉得周围的一切不是毫无意义,便是不可理解。”爱蕾诺尔,她一直“与她的命运不停地进行斗争,也可以说她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句话向她所置身其间的阶级表示反抗”。“她切实感到现实世界比她本人要强大得多,而她的种种努力又根本改变不了她的处境”,而莉莎则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话”,那只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浅显直白的说法。莉莎也看到农奴制的罪恶,并愿意为之赎罪。她们都有无畏的信仰,为个人幸福争取斗争并为之付出牺牲的精神。当多余的人在她们心中唤醒热情,最后毅然地渴望与他们结合,结果都因为多余的人天性上的懦弱而没有成功。
多余的人虽然有力点燃起爱情与渴望自由的火焰,却并没有看到渴望的蓝图,生活会变一个样子,可是却已经预见泥潭搅动后的波澜,生活依旧会回归到死水微澜的状态。在对待爱情问题上,多余的人的懦弱性、对生活表里不一的情形表现得犹为明显,暴露了身上的致命伤。
阿道尔夫虽然没完全堕落,个性上却犹豫软弱,任凭欲望引发的激情在内心激荡,只因为要求摆脱空虚,虚荣心得到满足,当他一得到便感到餍足,爱情就成为羁绊,内心的火焰熄灭啦,却找不到一种果决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只好一天到晚忧愁烦恼,左右彷徨。
内心完美主义的倾向,促使他偏好残缺的事物,然而却无法从根本上接受她。他能爱,但却有一种比爱更强大的力量,比爱还要强大百倍的冷静力量,使他的爱只不过是虚荣的发泄,极容易地煽动起来,又偏偏极容易熄灭下去,当爱情处于游戏阶段,他热烈地接受,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当爱成为责任,失去开始的新鲜感,要完完全全地和生活焊接在一起,意志里的排异功能开始启动,随着爱情的熄灭慢慢竟变成一种无法融合的反抗。又无法像浪荡子一样抛开不顾,处于既不能爱又不能逃的两难境地,仿佛那是命运与热情布好的一个死胡同等着他撞得头破血流。
他厌恶社会的丑恶现象,却无法站起来反抗,更可怕的是,先前无法接受的观念渐如生理盐水一样注入体内,所有的思想从冥想中来,又归于冥想中去,整日喟叹:“整个世界都沉溺在冠冕堂皇的浮华逸乐之中,是不会理解像我这样一颗心的”,“我所想的与世人所关心的完全两样,我与任何人都格格不入,因此只好一个人落落寡合,忍受痛苦”。并且自省“我很难与别人进行严肃正经的谈话,这毛病总是难以改掉。”最后在绝望中这样说过:“我讨厌斗争,还是让我们在船上躺下身来,在暴风雨中安睡吧!……我所希望的,就是安宁”。
阿道尔夫死死地拖住爱情不放,作为拯救灵魂的一根稻草,“我只有同这个妇人恋爱的生活经验;怀疑她,就等于怀疑一切;诅咒她,就等于全都否认;失掉她,等于一切都毁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缪塞)。殊不知,它仅是一根稻草而已,并没有力量使其有自救的可能,反而成为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本已不堪重负的灵魂。
奥勃洛莫夫也从来没有过真的爱情,原因只是“那就是跟女人来往太麻烦”,慢慢地,“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心似乎不再期待,而是绝望了。”他害怕生活,连单单品尝肉欲的堕落的勇气都没有。相比其他多余的人来讲,他的性格上没有基于内在矛盾引起的锋芒,相反,他温和善良,却病入膏肓,贴身仆人与他是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双,就像堂吉诃德与桑丘样的和谐。
他与奥莉加的恋爱犹如精神上的回光返照一样,为最后心安理得地进入暮气沉沉的生活作最后努力。就算恋爱再真挚炽热,然而一旦想到恋爱过后的现实的生活,奥勃洛莫夫还是担惊受怕,“诗篇逐渐结束,严肃的故事就要开始”,竟至于把爱情看作一种热病,干扰了他平静的生活。
奥莉加最终认识到这一点:“我自视甚高,因此受到惩罚,我太相信自己的力量。我错就错在这儿,而不是错在你害怕的事情上。我梦想的不是含苞欲放的青春,不是美。我以为我能使你振作起来,你还能为我而活着,其实你早就死了。我没有预料到会犯这个错误,我一直在等待和期望……结果是……!”
奥勃洛莫夫终于在平凡善良、稍稍有点愚昧的女人那里找到了渴求的生活,也许不能称为幸福,但至少他“仿佛生活在一个金色画框里,这是一幅只有昼夜季节变化的西洋景,没有任何别的变动,尤其没有特大的偶发事件足以从生活的底部搅起那往往是苦味而又混浊的全部沉渣。”他的生活终于与父辈们的生活一脉相承,重新把生活裹在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大袍子里。
达吉亚娜对奥涅金赏识且认同,奥涅金却对爱情早已心灰意冷,和女人在一起不过是厮混,一方面是曾经沧海的花花公子,一方面却从未遇到真爱的匮乏。达吉亚娜的出现,唤醒久已沉寂的感情。但是那种冷静,可怕的冷静仍旧使其最终选择了放弃:“然而,我与幸福早已决别,我的心和它冰炭不容;你固然十全十美,但我却完全不值得您的垂青。请相信吧(我以良心保证):别管我的爱情怎样热烈,日久生厌,它就会变冷,我们的婚姻将痛苦地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