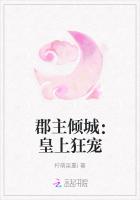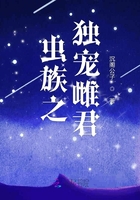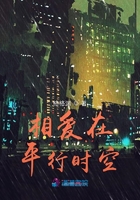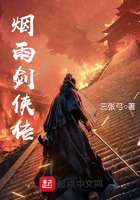社会如果没进步到共产主义,无论是偏僻的乡村,还是高楼耸立的美丽都市,这人间的污垢——乞丐就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他们总是不合时宜的出现,夹杂着难以听懂的地方口音,向你伸出一只脏兮兮早已分辨不出原本颜色的手,这无疑会搅去和家人共度周末的一点雅兴。就像老有一两只嗡嗡叫的苍蝇分享着你的美餐,多烦!这时候同情心一定躲在利己主义的后面,虽然还是不情愿地掏出一两毛钱掷在他的身边。
有真币就有假币,有人妖就有太监,假乞丐的产生当然不足为怪。经济界是“劣币驱逐良币”,乞丐界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假装的乞丐由于滥用人的同情心,使施舍者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弄到真乞丐都混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当那些真乞丐,被人们用怀疑的眼光左右上下鉴定时,心理上会不会有受了比乞讨更大的耻辱。不过,限于篇幅,我探讨的只局限于真乞丐的范围,那些假乞丐,还是留给“打假工作办”的同志去处理吧!
如果以对行乞者的态度进行分类的话,世上只有两种人:愿意施舍的和不愿施舍的。我!是从来不向乞丐施舍的,哪怕是一个铜子,并不是残忍和悭吝如此,我自认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情感是丰富而且细腻,出手也是一样慷慨大方的。之所以不施舍,是因为个人做的每件事情,都愿意找出一两条理由,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一旦施舍,我就会陷于自己都说服不了的境地。
各样的乞丐,老的、少的、强壮的、孱弱的、智力正常的和非正常的,等等,我认为都是社会自然法则淘汰下来的人,优胜劣汰,谁能挽救这个结局呢?老的,要么年青时不努力;要么儿女不孝顺,被赶了出来。少的,父母根本就没必要生下来,免得从生到死都饱受生活的煎熬。强壮而又智力正常的,更要自食其力,没必要要别人的施舍。造成他们这种悲惨状况的,不是上帝就是社会,或者自己。总之,在他们身上,我总能找出更主要、更有必要的义务承担者,完完全全没必要让我这样的旁人干涉。
如果人类还存在天使与野兽兼而有之的成分,那一定就是同情,“同情是一把双刃剑”,搞不好便会伤了自己。它是一种建立在对现状暂时的肯定和对未来持久的恐惧基础上的情感,是极不稳定的,具有极强的变异性。同情与自私之间的距离,有时比爱恨之间的距离还难以区分。越深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会越发现它的矛盾。我们同情乞丐,在潜意识中不过是炫耀自己,使心理产生一点优越感:这世上至少还有需要我施舍的人。施舍的过程中,往往误认为自己在付出,而没想到在对方卑贱的态度中得到莫大的满足。这种物质的少许付出而精神的极大占有,是残忍不人道的。所以在精神上自给自足的人,在物质上也是吝啬的,“我不布施什么,我并不穷得如此”。这位大师(尼采)还说过:“乞丐为何还活着──倘若一切施舍只是出于同情,那么整个乞丐帮早就饿死了。”
有人认为,有些人给予时并没想到回报,甚至是匿名的,他的同情心应该是百分百的吧。错!需要施舍的人,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从根本上说都不是真正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和你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像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利用、剥削、倾轧、欺骗等等。乞丐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了社会的人,由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定义出发,他们已算不得什么人了,已经与世无争,成了闹市中的隐士。所以在施舍这个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单纯的,而越单纯的关系,似乎越容易辨别是非,所以心理上也容易得到满足。在付出一两毛钱的时候,或者更多的钱,你就认为自己崇高而又伟大,如同佛主一样了。这也就好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对素不相识的乞丐伸一援手,而不愿意给身边的人一丁点的帮助,甚至她(他)曾经是你的妻儿。戏剧里常有一中状元就抛妻弃子陈世美式的人物,当她(他)千里寻夫或千里寻父时,非但装作不认识,甚至于还杀人灭口!难道他在乎那点金钱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时候,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两个钱可以摆平的,她(他)已经开始有使他变成伪君子,做不成驸马爷,甚至犯下欺君之罪被杀头的危险,一句话,她(他)已经开始严重地威胁到自己高高在上的阶级地位了。所以说,当你拿这两种行为放在一起比较时,你认为何为恶,又何为善?何为假?又何为真呢?
假如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乞丐,他觉得给少了,问你多要几块钱时,也就是说稍稍暴露一下贪得无厌的心态和要求时,你一定开始对他厌恶起来,甚至后悔前一分钟的施舍,但你不知道贪得无厌只是人类一切天性中的一种罢了。所以向任何一个乞丐施舍,哪怕是一个铜板,你已经把他当动物看待了,把他的要求归于生存方面的,其他方面,哪怕万分之一上升到人性上面的(善的和恶的)都被你无情的剥夺了。试问一下,还有比把人当动物更残忍的事情吗?
施舍乞丐,只是把本来存在于社会的分配制度,稍稍的修正了一下,还好,修正得不太多。乞丐的产生,和小偷和强盗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人面临困境时的几种分化,当小偷不声不响地使你的财产发生转移,强盗拿着刀逼你掏出刚领到手的工资,他们也只不过使财产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分配而已。但从你来说,你只愿意骄傲地抽出工资的千分之一或更小的基数,去给乞丐,甚至给妓女(当她们笨拙地向你媚笑时),但却不愿把百分之一或更大的部分给小偷和强盗。一方面前一种施舍,是自愿的,等价的,最重要你是站在高处的,而后一种是被动的,非情愿的。你是处于配角地位的;另一方面这时候,你清楚地知道,这个数目太大了,大到你热爱起原先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换成教科书的语言也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所以说,任何一个简单心理和行为,都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它作用于你白日的思维,同样惊扰着你静夜的清梦。
当然,像冯谖那样的乞丐,先是“贫乏不能自存”,后来好不容易有人收留了他,还一下子“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又一下子“长铗归来乎,出无车”,还得寸进尺的“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如果碰到的不是有点雅量而又有几个闲钱的孟尝君,人格保留得这么完整的乞丐,在任何“人心很古”的古代,恐怕也难以混下去吧。
乞丐的问题,在文明社会的大背景下,就像美女脸上的色斑和暗疮,虽然颇让正人君子痛心疾首,可解决起来,正如小偷和强盗等问题一样,除了社会的进步别无他法!《武状元苏乞儿》中苏乞儿劝告皇帝:“只要你做个好皇帝,国泰民安,天下的乞丐自然会少下去”。施舍只是治标不治本,无形中还助长了堕落人性的滋生。不过问题已经出现,能治标还是治一下吧,小范围的调整一下分配制度,未尝不是权宜之计,好在像我这么反动的并不多,否则大多数乞丐都要下岗再就业了。
不过听人说,在对付乞丐方面,各个城市都有一种通用的、不成文的、还颇有效的方法:由民政部门出面,把本地固有和游方的乞丐全部拖上卡车,然后偷偷放到外地的郊区轰下去。这应该是不错的,有几次我就奇怪一夜之间怎么出现这么多乞丐,一定是违反别处的治安管理条例,被驱逐出境,赶到奉新这块风水宝地来了。在社会进步任重道远的现在,用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巧妙方式解决,未必不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注:写完此文后,看到杨绛先生译的《小癞子》中有以下一段话:“那年小麦歉收,市政府决议,并由叫喊消息的报子宣布:‘外来的化子一概驱逐出城,以后再进来,抓到就罚吃鞭子’”。而在译本注中注明:“1540年托雷都市政府有此决议。”可见驱逐叫花子是古今中外心照不宣、不谋而合的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