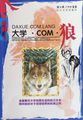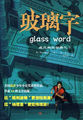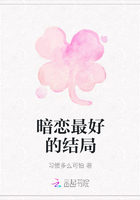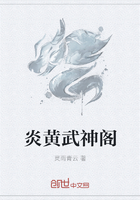还有一个朋友,是三年级的同学,也是“不打不相识”的那种。名字忘记了,好像姓江,坐在我后面,有一天因为边界问题吵起来了,当时胡小毛也在班上,有他在场,我胆子不会怎么小,随手把钢笔的墨水洒了他一脸,他先是一怔,一怔过后,也不甘示弱,回手拿起一支钢笔,也给我洒了一脸,结果你一下,我一下,两人脸上都长满了蓝黑色的雀斑。不过两人还有上海人的风度,虽然吵得厉害,斗争始终没有升级,没有发展到拳脚相向。全班同学看着两张大花脸,都笑起来,我们两人也不好意思,就到学校后面的小溪边,我帮他擦,他帮我擦,傻呼呼地看着笑起来,竟成了好朋友。可是由于我的留级和妈妈调走,这段友谊也没很好地保持下去。
就在甘坊垦殖小学,我遇到一位值得终身怀念的老师,像美国电影《男孩镇》中的牧师,有相似的人格力量和魅力。如果一个人一生注定只能碰到一个好老师,那么我希望是在一年级,因为那时心理幼稚,最需要有爱心有办法的老师扶持,至于以后碰上个把两个混账的,有了点抵抗能力,也就无所谓。老师的样子,我还记得,二十来岁吧,棱角分明,清清秀秀,姓赵。他是班主任,教我们语文,从来把孩子看成是很上进,要面子的人,从不责备人,只说某某学习很用功(常举住他隔壁一位同学的名字),对你的小进步从不忘记表扬,使你很努力,很有兴趣地学下去,并不把学习看成是负担。我只觉得上课好玩,懵懵懂懂,考试只在五十分上下,在他的鼓励下对学习有了兴趣,语文也考到七十来分。除了学习方面的事情外,还教我们吃饭不挑食一些简单易行的道理,黑板上方贴的不是什么“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大而无当的话,而是“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几个大字,我挑食的习惯在那时改了过来。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六·一”儿童节,我带了弟弟一起去,教室里买了很多瓜子和糖,知道我带弟弟来了,特意叫过去,在他口袋里装了很多的瓜子和糖,可是在我看来,也不知道谢谢什么,认为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下午看了一场电影,好像是《五十一号兵站》,根本看不懂人物关系,可是那个“六·一”是一生最难忘的一次。后来他到上付送练习册,我远远在一边玩着,也许他以为碰上的只是一位没有感情的浑小子。其实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尤其是过了一年多没见面,他的好处,我至今还记得。如果一生的老师有一半能像他那样,我对学生时代厌恶的程度肯定不会那么厉害。
教数学的老师姓严,四十来岁,人如其姓,一向比较严厉,不苟言笑。有一次全班同学不知怎么惹发了他的火,上课不听讲还是什么,一气之下,他出了一张试卷,只有十道题,每题十分,发下去让大家做,我坐在那里老半天,看着题目发呆,想想不写点什么不好意思似的,只是在每个题目空白处,像领导批字似的画了几下,结果成绩下来,最高的只有四十来分,二十几个人的班上,有十六七个是零蛋一个,我当然也荣列其中,好在零分不止我一个,只觉得好玩,并不觉得羞愧。也许这是他一生改得最痛快的一张试卷,在学生时代被老师用这种方法修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三年级的课本里有三味书屋这篇课文,介绍了鲁迅小时候的学习经历,上课后的第二天,绝大多数男生都不约而同的和桌子过不去,用铅笔刀刻上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早”字,我力气小,也不甘落后,浅浅的似有如无地凿上了一个。崇拜英雄原是普通人的义务,只不过时代不同,英雄的层次和含金量会发生很多变化。知慕少艾,从崇拜大力士到仰慕文化先哲,也算一大进步。这以后,汽车、门板都成了我们即兴的演绎场所,写满了各种刚从课本或其他地方学来的东西,当然也有“打倒×××”之类无聊的话语,内容多样,水准不一,也许是文人雅士到处题字的潜意识在人性中作怪。
不知单恋算不算恋爱,如果算的话,我的初恋,应该也在三年级。在班上,我暗暗喜欢一个叫谢黎明的女孩子,她学习好,每次都可以得到老师表扬,人也长得漂亮,清清纯纯的样子,对于我这个差生来说,她是可望不可即的。这个名字,是唯一没有特殊关系,而在童年的记忆里记全了的,可见重色轻友一向是我的本性。那时妈妈为了省钱,总叫我到食品站的食堂买馒头,我知道谢黎明住在那里,每次去买馒头的时候,总希望能见到她,可是也奇怪,在那种场合,一次也没有见到她。有一天下午,别人带了几本小人书到教室里,我借了一本在看,记得是《孔雀公主》,她竟走到我面前,问是什么书,并且拿过来翻了一下,我的心莫名其妙跳快了好一阵子。以后从甘坊出来,再也没有过任何她的消息,现在她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为人妻为人母,一无所知。这些梦就像童年一样,有着不可言喻的美妙和天真。
最大的一次打击也在三年级,那时语文开始学写作文,数学开始学乘法,我总也弄不清里面的关系。晚上妈妈在家辅导我,在纸上左画一个盘子,右画一个盘子,这里加上几个小圆圈,那里加上几个小圆圈,可是比来比去,几个圆圈摆来摆去,把我弄得头昏脑涨,总也听不懂,急得妈妈要命,妈妈做过几年老师,自以为教育方法很形象生动,没理由听不懂。这个情景被妈妈一个办公室的彭伯看到,不知是出于幸灾乐祸还是善意的玩笑,在旁边说了一句:“望子成龙,子却成了一条虫。”可能他认为我还听不懂这句话,我本来身心疲惫,这一句话无疑是一记重拳,又重重地打在我的心里,当时打击真不小,差不多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
有三幅画面一直记得,一次是四五月的样子,开始还是晴朗的天空里,突然下起了不小的阵雨,雨水在太阳的照耀下,落在手心里,已经有些暖意,而且太阳的光芒射在雨水上,显出很明显的虹带,真是非常美丽。我一边看着,一边忙着告诉这个那个人,当时快乐的心情,还记得很清楚。一次过年,在甘坊看龙灯,那时山里人做龙灯做得很长,二三十节的很常见,甚至更长,四五十节的也有,在空心的竹笼里点上蜡烛,灯火通明的在山林里,蜿蜒在黑山里,远处看去,时隐时现,伴着阵阵的锣鼓声,真是很美很吉祥的一幅图画。另外一次是放学回家,我坐在用钢绳捆住的一大堆木头上,一个人坐着,开始刮起风来,而且渐渐的大起来了,地面上时不时地卷起一阵小小的旋风,一些轻的东西,更多的是纸片,悠悠荡荡随着风在天空飘起来,有些甚至飘过了屋顶,当时甘坊粮管所的院子很大,所以一些纸飘起来,也颇为壮观,我从来没看过,所以至今记得。
算起来,我只是在七岁前在甘坊,在记忆里能记起的至多只有两年,但这些却非常的深刻,深刻得让心灵都无法承载。还好,这些所有的恨与爱,歧视与尊严,痛苦与快乐,都佑护着我成长,没有伤我的元气,使我有力量面对以后的人生,至少在现在,它们还在灵魂内发生作用,使我努力,使我自新,不敢停顿,在犯了无数大小错误后,仍有勇气看着前面的人生,这是我有所感怀而且激动的。
每当被大人用腿夹住无法挣脱时,就觉得有长大的冲动;夏天游泳被反复告诫,这里或那里不准去,只能到浅的刚没过脚背的地方玩耍时,更有想长大的冲动;当跟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出去玩时,总借口这或借口那推脱甩开时,也有想长大的冲动;当有人告诉我甘坊原来是一片大海,我对长大有一种向往,总觉得大人了解得更多,懂得更多,他们的快乐也更多,如果不长大永远不知道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永远有被大人夹住无法挣脱的窘迫感。大人有他们的世界,更大更有趣,几次想冲进去,但都以头破血流的结果而告终。有一次听彭伯在办公室讲,今天的电影如何如何好看,有这个艺术那个艺术性,我在旁边听了,问过妈妈要钱,自己偷偷跑去看,结果是清朝的古装戏,可能十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竟在电影院睡着了,还是第二场完时有人认识我,把我叫醒。于是我终于明白,大人和小孩是两个世界,以自己的力气和思考方式,进入他们的世界是徒劳的,但渴望长大的要求更强烈了。
由于妈妈工作的调动,我离开了甘坊,搬家那天,已是晚上,外面野地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的海洋里荡漾。可是在摇晃的车厢里,我竟不能和伙伴们一同抓萤火虫了。八九年后,回去过一次,见到的景象,竟使我有沧海桑田的感慨,粮管所门前的稻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房子,残缺的牌坊没有了,只有那灰白的石塔,还在拱桥的身旁,桥下依旧不停的流水,还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