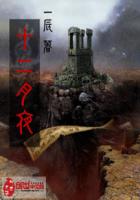程朗忽然启动车,朝南京的方向继续开去。
“季素,我要带你去见他,我要帮你把他夺回来。”程朗坚定地说,目光注视着前方的车辆。
心里很温暖,第一次见程朗这样子的大男人主义,他说要帮我把之放夺回来,那么为什么我自己还不够勇敢呢,我也要把属于我的夺取回来。
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强取豪夺的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为爱牺牲,是一种壮烈而残酷的事实,不愿牺牲,那么就要争夺。
程朗开车到了一家连锁酒店,我和贤芝暂先去酒店把随身物品放在酒店里,三个人在一起吃饭,吃饱后才有力气。
我翻出手机里记下的之放的公司地址,大约下午三点多能去之放的公司,这个时候他应该正常情况下是在公司里,或者就是在他自己的音乐室。
吃过饭后,程朗和贤芝陪我一起去之放的公司,我起初是想单独去找之放的,但是贤芝和程朗都不放心,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是怕我和麦乐万一发生了冲突打起来我会吃亏。
其实我不会和麦乐打架泼骂的,我再也不会为了一个男人不顾颜面去和另一个女人出手打架了。
曾有对门的邻居看到之放后问妈妈,你家的季素是不是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人啊,那小伙子看起来就像个蛮有钱的富二代啊。
也许会觉得我是想嫁有钱人,是因为贪钱。
事实证明,我和之放在一起,我并没有怎样向他要钱要首饰,只是小放的手术费是他交的大部分,我并不是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孩子的将来所以想靠着他,享受他给我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的生活。
仅仅是因为我们患难与共,从和温安年蜗婚至今,发生的那些波折和坎坷,一路有他相伴不离不弃,我真以为没有什么患难可以把我们给分开。
有本书上说,但凡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超过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那么这个女人大多是悲剧结局的,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的定律。所以很多的女人宁愿嫁给一个自己不讨厌但是很爱自己的男人,这样的话,总是幸福而不动荡的。
婚姻里,一旦你在意对方超过了这个男人对你的在意,那婚姻就将容易动荡起来,你过于在意他,你就会无端的紧张和害怕,你总是会怕你深深爱着的男人会离开你,所以,最后受伤的,总是爱的最深的那一个。
贤芝开始大谈她的恋爱哲学,有的还是十分有道理,比如说恋爱中有一个你不得不信的地方,那就是你以为你爱这个人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到最后却发现你只能爱到今天。
是对的呢,竟然再爱一个人,也可以有不爱的一天。
车停在了之放的公司楼下,我并不确定他是不是就在公司还是在音乐室,我下车,程朗坐在车里,他低着头开始猛抽烟,他变得很深沉不愿多说话,他让贤芝陪着我上楼,他在楼下等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事,他立即上楼。
我对贤芝说:“你也在车上等我吧,我又不是去打架的,我只是来寻找我的未婚夫。”这句话我想已经摆明了我此行的态度,我只是很简单的未婚妻来看自己的未婚夫,只是要给自己男友一个惊喜。
贤芝犹豫了一下,手撩了一下额边的碎发说:“真的不需要我陪你上去吗,你一个人行吗,万一那个叫什么麦乐的女歌手也在呢。”
“没事,在就在,我又不怕她,我又不是来找她的,再说,我就不相信我和她发生了冲突,之放会无动于衷不帮我,相信我,我会和平解决的,不是谈判,我是带我的男人回家。”我说着,把贤芝推进了车里。
我挎着包,进入了公司大厅,等电梯。
在二十二楼,真够高的,如果冲动起来从上面跳下来岂不是要摔成大饼一样。
在电梯里,人都挤了进来,最后我被挤出了最外面,超重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我往往周围的人,几乎是每个人都同样的目光望着我,好像这个电梯里就多了我一个就超重了,我低头看看我自己的体重,我想我重吗?也许是因为我站在最外面吧。
于是我很乖巧地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继续等待。
心里很纠结,手机握在手上都发烫了。
我脑子在飞快旋转,我去了公司我该怎么说,如果出现意外的打击情况我该作何面对,各种状态都在我的脑子里一幕幕上演。
但我告诉我自己,总结一点最重要,那就是要淡定要稳住,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都要微笑,我都不能嗷嗷喊叫发作起来。
进入电梯,电梯在缓缓伸向高层,我心怦怦地急剧跳动起来,慌乱的,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我居然穿着黑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牛仔裤,脚上的皮鞋都是灰沉沉一层,头发还很乱,都没有好好梳理就从医院走了出来,我用手机的屏幕反光看着自己的脸,有轻微的妊娠留下的斑,原先皎洁的脸庞上冒着薄薄的一层油光,忘记了化妆,嘴唇还有些因为干燥掉皮,真的是要多不堪就有多不堪。
是不是我这个样子一出现,我就已经是败了。
麦乐是新人歌手,小有名气,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精致而前卫。
看着镜子里面,没志气没血色的自己,挫败感好大,再怎么样我也该化化妆也该穿精致一点,这样的黑衣蓝色牛仔裤登场,气场就矮了一截,会不会我和麦乐站在一起,是个男人都将会选择麦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