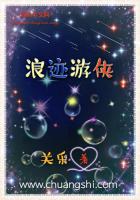杨之放俯身吻过来,暖暖的一个温暖,甜甜的,他刚吃了什么,嘴这么的甜,他说:“我想我就看过两个孕妇洗澡,一个是我妈怀我的时候,一个就是你,你以为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谁洗澡我都看吗?”他坏坏地做着表情说。
“那你唱首歌给我听,好不好?你是职业作曲人,我到想听听你唱歌的水平怎样,不然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你怎敢笑我唱歌跑调?”我沾满水的手在他脸上抹了一下。
第一次遇见是程朗怕我刚离婚情绪不好,独自带团会出意外,就暗中委托好哥们杨之放来一路照看,杨之放正好也借旅游泸沽湖的美景来找找作曲灵感。
怎么会在那时相遇呢?如果不是程朗的安排,我和他,会有遇见的机会吗?是缘分,还是注定?
杨之放唱的竟然是一首葡萄牙语的摇篮曲,虽然歌词我是一句也没有听懂,在他低柔舒缓的声音下,周围温暖舒适的水温,摇篮曲还是起到了催眠的作用,我泡在鱼缸里,渐渐睡去。
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梦,梦中,我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婚礼,我穿着婚纱,这是第一次穿婚纱,和温安年结婚因为存钱买房子,根本没舍得弄隆重的婚礼。
梦里,新郎是杨之放,他就站在我一米远的距离,那么的近,只要我们伸长了手臂,就可以牵住对方的手。我的手,是迫不及待的想伸出去,想牵他的手,可怎么也抽不出手,我的手好像被定住了不能动弹一般。
那么的焦急,那么的担心他会从我手边溜走,或者换而言之,是害怕到手的鸭子会飞了。
“别走,别走……等我,等我,我的手动不了,怎么办。”我在梦中一遍遍说着。
整个人觉得好像是清醒的,但又是迷糊的,隐约我感觉到四周站满了人,其实有秦汤汤,她们开始骂我,说季素你就是个傻货,你是个自私的女人,自以为是却什么也不是的女人。
美梦一下子就变成了噩梦,我挣扎着想逃离人群包围圈,不远处的一团光亮,我冲开人群,追着那团光,我看到勇敢的自己,微笑的样子。
“季素,你没事吧,怎么了,做恶梦了,别怕,有我在!”杨之放柔声地说,手将我额间的发丝拂过,原来,他没有走,一直守着我在。
我努力睁开眼,眼睛很酸涩,这几天心力交瘁,睡的很快,醒来却很累,我望见他靠在枕边,手撑着头,发呆一般地看着我。
记起好像刚还在浴缸里泡着,现在都到床上来了,我揭开身上的被子,孕妇内裤和睡衣都穿得好好的,我羞红了脸,他给我穿的,我怎么这么嗜睡,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我没事,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美梦加恶梦,还好,醒来有你在。那个,我衣服是你穿的吗?”我承认,这句话问了纯属白痴,这房子里,除了他就是我,不是他穿得难道是我肚子里的杨小放穿的?
他双手叠交着在脑后,靠在床上,故作神秘兮兮的样子,清了清嗓子,说:“是啊,是我给你换的,我给你选的,不过我是闭着眼睛给你穿的,我没有偷看。”
鬼才相信你没有偷看,我撇撇嘴,偷偷掀起睡衣,想看清楚他给我穿的是什么样的孕妇内裤,我一抬头,看见他的眼神也凑了过来,我盖上被子,掖了掖,说:“你看什么?”
他又假装不在乎的样子,耸耸肩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啊,我只是怕我闭着眼睛给你穿错了内裤,我也洗澡了的,我怕把我的内裤给你穿上了,所以瞧瞧。”
我笑了,说:“你怎么这么坏呢,你的我能穿的上吗,我的肚子这么大。我们还没有结婚,等孩子出生了,我们结婚了……”
“我们就可以做成年人该做的事了,对不对?”他邪魅一笑,脸又凑了过来,想索吻。
我笑着推开他的脸,说:“谁要和你做成年人做的事,你在我眼里,有时还像个小孩子。”
杨之放站起身,不厌其烦地展示了一下他的肌肉,明媚的微笑说:“有这么健壮的小孩子吗?总有天,我要让你看到我多男人!”
我望着他高高大大站在床边,带着欧洲混血男人的深情与威猛,多像从美剧里走出来的男子,其实,这不过是他的外表,他的内心,还单纯的像是个孩子。
他努努嘴,又凑过来索吻的样子,多像一个孩子在索要心爱的玩具,让人不忍推辞。
等孩子出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三口之家,该多幸福。我想,答应温安年复婚,也只是暂时的,我不能再执迷不悟,错过了一次,也许,就回不了头了,我想嫁的,还是杨之放。
虽然会偶尔有不安全感,比如对自己条件的自卑,还有对他的完美有些不放心,可我又想,两个人真的要在一起,决定下来了,那么就不要想配不配的问题,只要爱了,还在乎配不配吗?
曾有多少人说我和温安年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的啊,最后呢,成了仇敌,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恨他巴不得他不得好死。
过去的爱,一丁点儿也不复存在了。
还要彼此信任,不要瞎猜疑,不要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