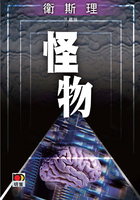“你还没走吗?”不知什么时候主人回来了,在迷亭身旁坐下。
“什么‘还没走吗’?这话说得多不中听啊!你不是说‘马上回来’,叫我等候的吗?”
“他凡事如此!”女主人回头瞧着迷亭说。
“老兄不在家的工夫,我可是毫无遗漏地听说了你不少的轶闻啊。”
“女人就是喜欢多嘴,拿她们没办法。要是人也像这只猫一样不言不语,多好啊!”主人摩挲着我的头说。
“听说你给小孩子吃萝卜泥?”
“嗯。”主人笑着说,“虽说是孩子,可现今这小孩子可机灵呢。自从给她吃了萝卜泥以后,只要问她:‘好孩子,哪儿辣?’她准把舌头伸出来。好生奇怪。”
“这不是像驯小狗似的吗,大残忍喽。不过,寒月兄也该到了呀!”
“寒月也来吗?”主人很意外地问道。
“来呀。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要他下午一点钟之前到苦沙弥家来。”
“你就喜欢自作主张,也不问问人家是否方便。叫寒月来干什么?”
“冤枉我了。今日之约可不是我的主意,是寒月本人的要求。据先生说将在物理学会发表演说,需要演练一下,让我听一听。我就说,那正好,叫苦沙弥兄也一起听一听吧。因此,才叫他到你家来的。--我觉得你反正是个闲人,这不是正合适吗?--他不是个妨碍别人的人,你还是听听好吧。”迷亭自说自话。
“物理学的讲演,我可不懂!”主人有点恼恨迷亭独断独行似的回道。
“不过,这个讲演可不是像镀镁喷嘴那么枯燥乏味的内容噢。是《关于自缢的力学》这样的超凡脱俗的题目,很值得一听啊!”
“你是个险些上吊的人,听听也好,我可就……”
“你该不会得出‘连在歌舞伎座看戏都会打冷战的人,听不了’的结论吧”迷亭照例没有正经的。
女主人呵呵地笑着,回头瞧了瞧丈夫,退到隔壁房间去了。
主人不置可否地抚摸着我的头。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格外温存地抚摸我。
过了大约七分钟,寒月先生果然来了。因为晚上要去讲演,他破例穿着漂亮的长礼服,刚刚浆洗过的雪白衬领笔挺笔挺的,使原本帅气的寒月更添了几分风采。
“让二位久等了……”他优雅地致歉。
“我俩已经等候多时了。请你速速开始吧,是吧,老兄!”
迷亭说罢,看了看主人。主人只好含糊地“嗯!”应了一声。寒月却不着急,说:“给我倒一杯水吧!”
“哟呵,还认真啦?接下来该要求我们鼓掌了吧?”迷亭一个人起着哄。寒月先生从礼服内兜里掏出草稿,缓缓说了句开场白:
“因为是演习,请不要顾忌情面,多多批评指点!”
然后开始讲演了。
“对罪犯处以绞刑,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施行的一种刑罚。远溯其民族的上古,吊颈,主要是一种自杀的方法。据说犹太人的习惯向罪犯投掷石块来行刑。经研究《旧约全书》可知,‘缢死’这个词,最早起源于:将罪犯的尸体吊起来,当做喂养野兽或食肉飞禽的食饵。按希罗多德的学说,犹太人在离开埃及之前,最忌讳夜里曝尸。据说埃及人将罪犯斩首之后,只将其躯体钉在十字架上,夜里曝尸于野。而波斯人……”
“寒月兄,这与‘自缢’的题目似乎越来越远了。不要紧吗?”迷亭插嘴道。
“这就进入正题,请稍安勿躁。且说,那波斯人是如何行刑的?据说也是采用碟刑的。只是搞不清楚,究竟是把人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是杀死之后再钉上去的……”
“那些事,不知道也无所谓的。”主人无聊地打起了呵欠。
“我还有许多事要想诸位说明的,但是考虑到诸位也许会感到厌烦,所以……”
“会感到厌烦的,不如‘想必会厌烦的’听起来顺耳。是吧?苦沙弥兄!”迷亭又在鸡蛋里挑骨头。苦沙弥不以为然地说:“都是一回事。”
“那么,现在就进入正题,且听我一一道来。”
“‘道来’之类的都是说书先生的行话呀!演说者还是用高雅些的词语为好。”迷亭又在打岔。
“如果‘道来’太俗气的话,用什么词才好呢?”寒月有些愠怒地问道。
“不知迷亭君是在听演讲呢,还是在捣乱?他老是瞎起哄,寒月君不用理睬,赶快往下讲吧。”
主人是想尽快度过这个关口。
“这可谓恰似‘勃然自辩,望见庭中柳’吧。”迷亭依旧云里雾里,胡诌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寒月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据我查阅资料,真正处刑时动用了绞刑的,出现在《奥德赛》第二十二卷,就是忒勒马科斯绞死珀涅罗珀的十二个宫女那一段。虽然也可以用希腊语朗诵原文,但是难免有卖弄学识之嫌,因而作罢。请从四百六十五行看到四百七十三行,自会明了。”
“希腊语云云,还是免去为好。这不是等于在炫耀自己会讲希腊语吗!是吧?苦沙弥兄。”
“这一点,我也赞成。还是免去那些过于露骨之词,显得文雅一些。”主人破例地马上袒护了迷亭,因为二人一句希腊文也不懂。
“那么,今晚就把那两句略去,听我继续道来……噢,听我继续说明。”
“现在来想象一下这种绞刑,应该有两种执行方法:其一是,那位忒勒马科斯借助欧迈俄斯和菲力西亚斯的帮助,将绞绳的一端系在柱子上,然后在绳子上打许多活结,把宫女的脑袋一个个套进活结里去,将绞绳的另一端猛劲一拉,就将人吊起来了。”
“就是说,把宫女吊起来,看做就像西方的浆洗房晾衬衫似的,就对了吧?”
“正是。再说第二种,是这么个程序:将绞绳的一端如上所述,系在柱子上,而另一端上已经高高吊在顶棚上了。然后从那吊在高处的绳子上放下几条绳来,将绳子头儿结成套圈儿,套在宫女的脖子上。到了行刑的时候,将宫女们脚下的凳子一撤即可。”
“打个比方吧,就想像一下草绳门帘头上吊着些小圆灯笼一般的情景,应该没有差不多吧?”
“小圆灯笼不曾见过,因此,无法发表意见。假如真有这种,大致可以类比吧。下面将以实例给大家证明:从力学角度看,第一种方法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立的。”
“真有意思!”迷亭说罢,“嗯,有意思!”主人也表示赞同。
“首先,假定宫女们被等距离地吊了起来,并且假定吊在距地面最近的两名宫女的脖子和脖子上套的绳索是水平状的,那么,把α1、α2……直到α6看成是绞绳与地平线形成的角度,把T1、T2……直到T6看成绳子各部分受的力,把T7=X看成绞绳最低部分所受的力。不用说,W自然是宫女们的体重了。怎么样,各位明白了吗?”
迷亭和主人互相对望了一下,说:“大致明白了。”但是,这个大致的程度,只是二人随口一说,换做他人或许就不适用了。
“那么,根据各位所知的多边形的平均性原理,可成立十二个如下的方程式:T1cosα1=T2cosα2……T2cosα2=T3cosα3……”
“方程式,就不必一一赘述了吧?”主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演讲。
“其实,这个方程式正是演说的大脑部分。”寒月显得甚为遗憾。
“那么,大脑部分就改日领教吧。”迷亭也有些为难的样子了。
“假如删掉这一方程式,我苦心钻研的力学,就等于全泡汤了……”
“何须如此多虑,能删的就尽量删去……”主人淡淡地说。
“那就仅遵指点,狠狠心删掉吧。”
“这就对喽!”迷亭竟不合适宜的啪唧啪唧鼓起掌来。
“接下来谈一谈英国。在《裴欧沃夫》这部史诗里有‘绞首架’一词,即galga这个词。可见绞刑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就实行的。根据布拉克斯通的说法,被处以绞刑的罪犯,万一由于绞绳的缘故未能死去,须再受一次同样的绞刑。奇妙的是,在《农夫皮尔斯》这部著作里却有‘纵使恶棍,也绝无重复绞首之理。’这么一句。那个说法是真实的虽然不清楚,但由此可知,不走运的话,一次未能绝命的受刑者是不乏其例的。有这么个例子,公元一七八六年,曾将一个名叫费茨·杰拉尔特的臭名远扬的恶棍送上了绞架。但是,真是巧了,第一次,他的脚刚刚离开绞架之际,绞绳竟然断了。又吊了第二次,但是这一次因绞绳太长,脚着了地,还是没死成,最后在看客们的帮助下,才送他上了西天。”
“哎呀呀!”一听到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儿,迷亭就来了兴致。
“这可真是死不了啊!”连主人都兴奋起来。
“奇妙的还不止这个哪。据说一吊脖子,人的个子就会被抻长一寸左右。这确实是医生测量过的,千真万确!”
“这可是个新招术啊!怎么样,苦沙弥兄,如果申请上吊,把脖子抻出一寸来,说不准会成为中等身材呢!”迷亭瞧着主人调侃,主人竟格外认真地问道:
“寒月君,把身体抻长一寸左右的人,还能活过来吗?”
“那肯定不行了。说什么一吊起来,脊骨就被拉长了,哪里是个子变高,是因为脊骨被抻断喽。”
主人也死了心,说:“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演说还有很长,寒月本打算一直论述到上吊的生理作用为止,因迷亭起哄似的胡乱插言,主人又不时无所顾忌地打呵欠,寒月不得已中止了演讲,打道回府了。至于当天晚上寒月先生是以何等姿态、进行了何等雄辩,因是发生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咱不得而知。
其后二、三日平静度过。一天下午两点,那位迷亭先生,又照例像偶然童子似的飘然而至。他刚一落座,就冷不防来了一句:
“老兄,越智东风君的高轮事件,你听说了吗?”看他那势头,简直像是来报告攻陷旅顺的最新消息。
“不知道,最近没见面。”主人一如往常,满面阴郁。
“今天,我是为了向你报告东风君遭遇惨败的故事,才于百忙之中专程来访的哟!”
“又胡说八道了,反正你就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哈哈哈……与其说‘不可救药’,不如说是‘无药可救’为宜吧,这二者不分清楚的话,可事关本人的声誉哟!”
“都差不多!”主人装糊涂,完全是天然居士转世。
“听说上个星期天,东风君去了高轮的泉岳寺。天气这么冷,按说不该去的。可是------最起码,这个季节去泉岳寺,岂不像个初次来东京的乡巴佬吗?”
“那是东风的自由喽。你又没有权利阻止他。”
“不错。我的确没有阻止的权利。权利有没有不重要,不过,那个寺院里不是有个叫做‘义士遗物保存会’的展出,你知道吗?”
“这个……”
“你不知道?可是,你不是去过泉岳寺吗?”
“没有去过。”
“没去过?真想不到。难怪你极力为东风君辩护。老江户,却没去过泉岳寺,多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也照样可以当教师嘛。”主人愈发像个天然居士了。
“这个先不说了,且说东风君去那个展览会参观时,来了一对德国夫妻。起初,他们好像是用日语对东风君问了些什么。不过,你也知道,东风先生不是总喜欢卖弄几句德语吗?结果他就叽里咕噜地说了两三句,说得还相当流利。事后一想,这恰恰给他惹了祸。”
“后来怎么样了?”主人终于被吊起了胃口。
“那德国人看到大高源吾的漆金印盒,就问东风君,他想买下来,不知是否能够卖给他。当时东风君的回答真是太风趣了。他说,日本人都是清廉的君子,绝对不会卖的。直到此时,他还很得意呢,但是后来,那德国人以为好不容易遇到了个像样的翻译,便不停地问这问那。”
“问了什么?”
“问题就在这儿,倘若听得懂,还不要紧,可那德国人说话飞快,连珠炮似地发问,他完全听不明白。偶尔听懂一句半句,对方又问起鹰嘴钩子和大木槌来。西洋的鹰嘴钩子和大木槌这两个名词,东风先生没学过,如何翻译,所以就傻眼了。”
“难怪啊。”主人联想到自己当教师的经历,深表同情。
“可是,一些闲人好奇地陆续向这里聚拢过来,最后将东风和一对德国人团团围住瞧热闹。东风满脸通红,尴尬极了。和开始时的洋洋自得相反,狼狈不堪的。”
“最后怎么样了?”
“最后,据说东风觉得实在应付不下去了,便用日语说了句‘塞见’,急忙撤退。德国人问道:‘塞见,没怎么听过。难道你的家乡把再见说成塞见吗?’他回答:‘哪里,当然是说再见。只因为是西洋人,为了与西方发音相协调,才念成了塞见。’东风君身处困境也不忘协调,实在令人钦佩。”
“关于‘塞见’,就算了,那西洋人怎么样了?”
“据说那西洋人听了目瞪口呆。哈哈哈,够滑稽的吧!”
“也没有多么滑稽。倒是为此特地来报信的你,滑稽得多呢。”
主人将烟灰磕进火盆里。这时,门铃儿冷不丁地响起来。
“有人在家吗?”是尖细的女人声音。迷亭和主人不由得面面相觑,默然不语了。
女客造访主人家,可真少见。我一瞧,那个发出尖声的女人,在席子上拖拉着她那身双层绉绸和服走进屋来。年纪约莫有四十出头了。她那光秃秃的前额上高耸着一排发帘,犹如一道堤坝,使得至少有半张脸朝天凸出着。她的眼睛就像凿出来的陡坡一般,斜吊成两条直线,左右对立。所谓直线,是比喻其比鲸鱼眼睛还要细之意。独有鼻子大得出奇,仿佛把别人的鼻子偷来安在自己的脸正中。就如同将招魂神社靖国神社的石头灯笼搬到了不足十平米的小院里,尽管唯我独尊,却让人感觉很是不舒服。那鼻子是所谓鹰钩鼻。一度高耸,忽而觉得过分,中途又谦逊起来,到了鼻尖,没了初时的势头,开始下垂,窥视鼻下的嘴唇。因拥有如此不可一世的鼻子,这女人说话时,不能不令人以为她不是嘴里在说话,而是鼻孔在发声。我为了向这尊伟大的鼻子致敬,准备以后称她为“鼻子夫人”。鼻子夫人叙罢初次见面之礼,冷冷打量一番室内说:
“很不错亮的房子呀!”
“说谎!”主人心里说,吧嗒吧嗒地吸烟。
迷亭则望着顶棚说:“老兄,那是雨水的痕迹,还是木板的花纹?图案很奇妙啊!”他在暗示主人说话。
“当然是下雨漏的。”主人回答,迷亭若无其事地说:“蛮好看哪!”而鼻子夫人则在心里怒骂:“真是些不懂社交礼仪的人!”好一会儿三人鼎坐,相对无语。
“我今天来是有点事想问您一下……”鼻子夫人又开了口。
“噢!”主人的回应极其冷淡。鼻子夫人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可不行,便说:
“其实我家离您家不远,--就是那条街角上的那栋房子。”
“就是那个有大仓库的洋房吗?怪不得,门牌上写的是金田哪。”
主人似乎终于知道了金田家的洋房和仓库。然而,对金田夫人的尊敬度却依旧没变。
“是这样,我丈夫本想自己来和您商量一下,无奈公司里太忙……”鼻子夫人的眼神好像在说:“这下该起点作用了吧?”
然而,主人却无动于衷。他认为鼻子刚才的措词作为一个初次见面的女子来说,过于不礼貌,而已然耿耿于怀。
“我家男人不只管理一个公司,而是兼管着两三个公司哪,并且,担任的都是董事……想必你是知晓的。”夫人的神色似乎是“说得这么清楚,你还不对我毕恭毕敬吗?”
我家主人,倘若对方说自己是博士或大学教授的话,他会非常恭敬的,奇怪的是,对实业家们的尊敬度却极低。他确信中学教师远比实业家们伟大。即使不那么确信,以他那不知变通的固执个性,对于获得实业家和财主们的眷顾,也不抱任何指望。不论对方有权势也好,有财富也罢,既然已断定没有希望承蒙惠顾,那么,对于他们的利害得失,自然无关自己痛痒。因此,除了学者圈子以外,对于其他方面的事,他都表现得极其迂腐。尤其是对于实业界,有那些人、在哪里、做什么事,他都一概不知。即使知道,也不会产生丝毫的敬畏之念。
鼻子夫人做梦也想不到,在环宇之一隅,竟有如此怪人同样沐浴在阳光下生存着。她阅人无数,只要一说是金田夫人,无不立即另眼相待。不论出席什么样的会议,也不论在身份多么高贵的人们面前,“金田夫人”这块招牌都非常吃得开,何况眼前这个迂腐不堪的老夫子?她满心以为,只要说一句我家就是街角的那处公馆,不等问干什么之类的,他就已经大惊失色了。
“你认识金田这个人吗?”主人漫不经心地问迷亭,迷亭则一本正经地回答:
“当然认识。金田先生是我伯父的朋友,前些天还来参加了遊园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