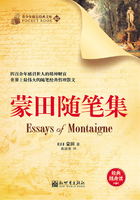当然,由你的来信中,很容易揣测你部分的心情,你表达的能力并不弱,由你的文字中,明明白白可以看见一个都市单身女子对于生命的无可奈何与悲哀,这种无可奈何,并不肤浅,是值得看重的。
很实际的来说,不谈空幻的方法,如果我住在你所谓的“斗室”里,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布置我的房间。我会将房间刷成明亮的白色,在窗上做一个美丽的窗帘,在床头放一个普通的小收音机,在墙角做一个书架,给灯泡换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灯罩,然后去花市仔细地挑几盆看了悦目的盆景放在房间的窗口。如果仍有余钱,我会去买几张名画的复制品——海报似的那种,将它挂在墙上……这么弄一下,以我的估价,是不会超过四千台币的,当然,除了那架收音机以外,一切自己动手做,就省去了工匠费用,而且生活会有趣得多。
房间布置得美丽,是享受生命改变心情的第一步,在我来说,它不再是斗室了。然后,当我发薪水的时候——如果我是你,我要用极少的钱给自己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如果我觉得心情不够开朗,我很可能去一家美发店,花一百台币修剪一下终年不变的发型,换一个样子,给自己以耳目一新的快乐。我会在又发薪水的下一个月,为自己挑几样淡色的化妆品,或者再买一双新鞋。
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地在变了。
我去上课,也许能交到一些朋友,我的小房间既然那么美丽,那么也许偶尔可以请朋友来坐坐,谈谈各自的生活或梦想。
慢慢的,我不再那么自卑了,我勇敢接触善良而有品德的人群(这种人在社会上仍有许多许多),我会发觉,原来大家都很平凡——可是优美,正如自己一样。我更会发现,原来一个美丽的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便可以达到,我也不再计较异性对我感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自得其乐都来不及,还想那么多吗?
如果我是你,我会不再等三毛出新书,我自己写札记,写给自己欣赏,我慢慢地会发觉,我自己写的东西也有风格和趣味,我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不快乐的女孩子,请你要行动呀!不要依赖他人给你快乐。你先去将房间布置起来,勉励自己去做,会发觉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兴趣是可以寻求的,东试试西试试,只要心中认定喜欢的,便去培养它,成为下班之后的消遣。
可是,我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快乐,是帮助他人,而不只是在自我的世界里享受——当然,享受自我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你先将自己假想为他人,帮助自己建立起信心,下决心改变一下目前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弄得活泼起来,不要任凭生命再做赔本的流逝和伤感,起码你得试一下,尽力的去试一下,好不好?
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问题是你一定要有行动,空想是不行的。下次给我写信的时候,署名“快乐的女孩”,将那个“不”字删掉好吗?
你的朋友三毛
爱我更多
——[中国台湾]张晓风
爱我更多,好吗?
唯有在爱里,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惊喜地发现自身的存在。
爱我更多,好吗?
爱我,不是因为我美好,这世界原有更多比我美好的人。爱我,不是因为智慧,这世界自有数不清的智者。爱我,只因为我是我,有一点好有一点坏有一点痴的我,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我。爱我,只因为我们相遇。
如果命运注定我们走在同一路上,碰到同一场雨,并且共遮于一把伞下,那么,请以更温柔的目光俯视我,以更固执的手握住我,以更轻缓的气息贴近我。
爱我更多,好吗?唯有在爱里,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惊喜地发现自身的存在。所有的石头就是石头,漠漠然冥顽不化,只有受日月精华的那一块会猛然爆袭,跃出一番欢快欣悦的生命。
爱我更多,好吗?人生一世如果是赶集,则我的行囊空空,不是因为我没有财富而是因为我手中的财富太大,它是一块完整而不容切割的金子,我反而无法用它去购置零星的小件,我只能孤注一掷地来购置一份深情。爱我更多,好让我行囊满涨而沉重,好吗?
爱我更多,好吗?因为生命是如此仓促,但如果你肯对我怔怔凝视,则我便是上演戏的舞台,在声光中有高潮的演出,在掌声中能从容优雅地谢幕。
我原来没有权利要求你更多的爱,更多的激情,但是你自己把这个权利给了我,你开始爱我,你授我以柄,我才能如此放肆如此任性地来要求更多。能在我的怀中注入更多的醇醪吗?肯为我炉火添加更多的柴薪否?我是饕餮的,我是贪得无厌的,我要整个春天的花香,整个海洋的月光,可以吗?
爱我更多,就算我的要求不合理,你也应允我,好吗?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中国台湾]刘墉
四海漂泊几十年,不论年轻或年老,也无论生与死,她觉得慈爱的父亲,总在自己的身边。
小时候,父亲常带她去爬山,站在山头远眺台北的家。
“左边有山,右边也有山,这是拱抱之势,后面这座山接着中央山脉,是龙头,好风水。”有一年深秋,看着满山飞舞的白芒花,父亲指着山说:“爸爸就在这儿买块寿地吧。”
“什么是寿地?”
“寿地就是死了之后,做坟墓的地方。”父亲拍拍她的头。
她不高兴,一甩头,走到山边。父亲过去,蹲下身,搂着她,笑笑:“好看着你呀?”
十多年了,她出国念书回来,又跟着父亲爬上山头。
原本空旷的山,已经盖满了坟,父亲带她从坟间一条小路走上去,停在一个红公花岗石的坟前。
碑上空空的,一个字也没有。四周的小柏树,像是新种的。
“瞧?坟修好了。”父亲笑着,“爸爸自己设计的,免得突然死了,你不但伤心,还得忙着买地、修坟,被人敲竹杠。”
她又一甩头,走开了。山上的风大,吹得眼睛酸。父亲掏手帕给她:“你看看嘛?这门开在右边,主子孙的财运,爸爸将来保佑你发财。”
她又出了国,陪着丈夫修博士。父亲在她预产期的前一月赶到,送她进医院,坐在产房门口守着。
进家门,闻到一股香味,不会做饭的父亲,居然下厨炖了鸡汤。
父亲的手艺愈来愈好了,常抱着食谱看,有时候下班回家,打开中文报,看见几个大洞,八成都是食谱文章被剪掉。
有一天,她丈夫生了气。狠狠把报摔在地上。厨房里刀铲的声音,一下子变轻了。父亲晚餐没吃几口,倒是看小孙子吃得多,又笑了起来。
小孙子上幼儿园之后,父亲就寂寞了。下班进门,常见一屋子的黑,只有那一台小小的电视机亮着,前面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打瞌睡。
心脏不好,父亲的行动愈来愈慢了。慢慢地走,慢慢地吃。只是每次她送孩子出去学琴,父亲都要跟着。坐在钢琴旁的椅子上笑着,盯着孙子弹琴,再垂下头,发出鼾声。
有一天,经过附近的教堂。父亲的眼睛突然一亮:
“唉?那不是坟地吗?埋这儿多好?”
“您忘啦?台北的寿墓都造好的。”
“台北?太远了?”
拗不过老人,她去教堂打听。说必须是“教友”,才卖她。
星期天一大早,父亲不见了,近中午才回来。
“我比手划脚,听不懂英文,可是拜上帝,他们也不能拦着吧?”父亲得意地说。
她只好陪着去。看没牙的父亲,装作唱圣歌的样子,又好笑、又好气。
一年之后,她办了登记,父亲拿着那张纸,一拐一拐地到坟堆里数:“有了?就睡在这儿?”又用手杖敲敲旁边的墓碑:“Hello?以后多照顾了?”
丈夫拿到学位,进了个美商公司,调到北京,她不得不跟去。“到北京,好!先买块寿地,死了,说中文总比跟洋人比手划脚好。”父亲居然比她还兴奋。
“什么是寿地?”小孙子问。
“就是人死了埋的地方。”女婿说,“爷爷已经有两块寿地了,还不知足,要第三块。”
当场,两口子就吵了一架。
“爹自己买,你说什么话?他还不是为了陪我们?”
“陪你,不是陪我?”丈夫背过身,“将来死了,切成三块,台北、旧金山、北京,各埋一块?”
父亲没有说话,耳朵本来不好,装作没听见,走开了。
搬家公司来装货柜的那天夜里,父亲病发,进了急诊室。
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孙子。从母亲离家,就不曾哭过的父亲,居然落下了老泪:
“我舍不得!舍不得!”突然眼睛一亮,“死了之后,烧成灰,哪里也别埋,撒到海里,听话!”
说完,父亲就去了。
抱着骨灰,她哭了一天一夜,也想了许多,想到台北郊外的山头,也想到教堂后面的坟地。
如果照父亲说的,撒到海里,她还能到哪里去找父亲?
“老头子糊涂了,临死说的不算数。就近,埋在教堂后面算了。”丈夫说,“人死了,知道什么!”
她又哭了,觉得好孤独。
她还是租了条船,出海,把骨灰一把一把抓起,放在水中,看一点一点,从指间流失,如同她流失的岁月与青春。
在北京待了两年,她到香港;隔三年,又转去新加坡。
在新加坡,她离了婚,带着孩子回到台北。
无论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或台北,每次她心情不好,都开车到海边。一个人走到海滩,赤着脚,让浪花一波波淹过她的足踝。
走过那么多路,脚上留下许多伤疤,再找不到少女时的娇嫩。但是四海漂泊几十年,不论年轻或年老,也无论生与死,她觉得慈爱的父亲,总在自己的身边。
爱
——[美国]爱默生
“你虽然已去,而实未去,不管你现在何处,你留给了他你炯炯的双眸与多情的心。”
爱的世界的核心是个人,个人是一切,一切是个人。因此即使最冷静的哲学家在细叙一个在自然界漫游着的稚幼心灵从爱情之力那里所受到的恩赐时,他都无办法把有损社会天性的话说出口,认为这些是对人性的拂逆。因为虽然降落自高天的那种狂喜至乐只能发生在稚龄的人们身上,另外虽然人到中年之后很难在其身上发现那种令人如狂如癫,那种难以比较分析的冶艳丽质,然而人们对这种情景的记忆却往往最能经久,超过其他一切的记忆,而成为鬓发斑斑的额头上的一副花冠。但是这里所要谈的却是一件奇特的事(而且有这种感触的非止一人),那就是当人们在回顾往事时,使他们感到最为美好,最值得记忆的是某些事物。那里爱情仿佛对一束偶然与琐细的情节投射了一种超乎其自身意义并且具有强烈诱惑的魅力。在他们回首往事时,他们必将发现一些其自身并非符咒的事物却往往给这求索般的记忆带来了比曾使这些回忆免遭泯灭的符咒本身更多的真实性。虽然我们各自的经历有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别,但无论是谁都会记住那种力量对他的冲击。因为这会把一切都重造过一样,这会是他身上一切音乐、诗歌与艺术的黎明,这会使整个大自然充满雍容华贵,便昼夜晨昏冶艳迷人,大异往常;此时他会变得异常敏感、紧张,而一件与某个形体稍有联系的卑琐细物都要珍藏在那琥珀般的记忆之中;此时若出现一个人,定会引得他侧目凝视,直到这个人在视野里消失,也会痴上半天。这时一个少年会对着一扇彩窗而终日凝眸,或者为着什么手套、面纱、缎带,甚至某辆马车的轮轴而系念极深;这时地再荒僻,人再稀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难过,因为这时他头脑中的友情交谊、音容笑貌比旧日任何一位朋友所能带给他的都更丰富更甜美;因为这个被热恋的对象的体态举止与话语并不像某些影像那样只是书写在水中,而是像浦鲁塔克所说的那样“釉烧在火中”,因而时常在朗朗无日或夜深人静走入恋人梦境。这时正是:
“你虽然已去,而实未去,不管你现在何处;你留给了他你炯炯的双眸与多情的心。”
这种感觉即使在步入中年甚或晚年之后,回想起来,仍使我们震撼。深深感喟到彼时的所谓幸福实在远非幸福,而是不免太为痛楚与畏惧所麻痹了,因此能道出下面这行诗句的人可谓渗透了爱情的三味:
“其他一切快乐都抵不了它的痛苦。”
另外,白昼在此时过得太快,黑夜也总是要糜费在激烈的追思回想之中;这时枕上的头脑会因为它所决心实现的慷慨举动而滚热沸腾;这时连月色也成了悦人的狂热,星光成了传情的文字,香花成了隐语,清风成了歌曲;这时一切俗务都会形同渎犯,而街上南来北往的男女也被看做是梦境中的人物。
这种炽情将把一个青年的世界重新造过。它会使得天地万物蓬勃生辉,充满意义。整个大自然将变得更加富于意识。现在枝头上的每只禽鸟的高唱都变得富有深意,连那些音符也变得有生命起来。当他仰视流云时,云彩也都露出美丽的面庞。林中的树木,迎风起伏的野草,探头欲出的花朵,这时也满含着笑意,但他却不大敢将他心底的秘密向它们倾吐出来。然而大自然却是充满着慰藉与同情的。在这个林木幽深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在人群当中所得不到的温馨。
“凉冷的泉头,无径的丛林,这正是激情所追求的地方,还有那月下的通幽曲径,这时鸡已入睡,空中惟有蝙蝠鸱枭。啊,夜半的一阵钟鸣,一声呻吟,这才是我们所最心醉的声响。”
请好好瞻仰一下林中的这位优美的狂人吧?这时他简直是一座歌声幽细、色彩绚丽的宫殿;他昂首挺胸,神气十足,有傲视一切的气概,他不断自言自语,好似在与花草林木交心;他在自己的脉搏里找到了与紫罗兰、三叶草、百合花同源的东西;他好与沾湿他鞋袜的清溪交流。
他在增强他对大自然感受的力量的支持下开始对音乐和诗产生兴趣。一件经常见到的情形便是,人在这种激情的鼓舞之下往往能写出好诗,而别的时候是无法达到此种境界的。
这同一力量还把他的全部天性调动起来。它将扩展他的感情;它将使莽夫文雅而儒夫立志。它将向最卑微龌龊的人的心中注入以敢于鄙夷世俗的胆量,只要他能获得他心爱的人的支持。正因他将自己交给了另一个人,他才能更多地将他自己交给自己。他此刻已经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人,具有着新的知觉,新的与更为激切的意图,另外在操守与目的上有着宗教般的肃穆。这时他已不再隶属于他的家族与社会。他具备了应有的一切:地位、个性、灵魂、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