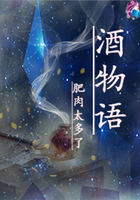谢流年幸亏还不算完完全全会说话,若会,能把谢四爷气死。她甫一看见青铜古彝、墨烟冻石鼎、汝窑花囊诸物,第一个念头就是:值多少钱?值不少钱吧。不用多,胡乱拿上两三件回去,拍卖会上一拍卖,下半辈子不用辛辛苦苦工作了。
“我的?”谢四爷来看她时,抱在父亲怀中,逐件指着各样名贵古董玩器,一一询问。谢四爷点头,“你的。”确认完毕,谢流年小手一扬,意气风发叫道:“小樱!”
小樱应声过来,太了解这位七小姐了,手中直接拿着小账本,“七小姐,给您一一登记上去?”知道她是要把这些古董入册。
谢流年这小账本记的很清楚:现银有多少,庄票有多少,金银玉器有多少,贵重摆件有多少。其中,她最关心的是现银和庄票,流通性最好。
谢四爷无语。过了两日,给两个小女儿都添了几名相貌清秀可人的大丫头、小丫头。这些丫头都通文墨,时常给两位小姐读读书、弹弹琴。便是陪两位小姐玩耍,也比寻常丫头有趣些。
“真是暴殄天物。”三太太明面上虽不说什么,暗地里跟谢绮年感概,“有多少人家,正经小姐不过略识几个字,平日只以针黹为重。谢家可倒好,连丫头们也多有读书的。”
“这有什么。”谢绮年微笑,“郑玄家中奴婢皆读书。他家连婢女都能出口成章,倒是佳话。”郑玄,东汉经学家,他家一名婢女触怒主人,被拽在泥中受罚。另一婢女走过,问“胡为乎泥中?”婢女答:“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一问一答,既应景,又据典,皆出自诗经。
奢侈是奢侈了些,提身份。谢绮年对于这一点,只有赞成的。她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谢家越矜持,她便跟着越娇贵。若说什么针黹、女工之类,小门小户的女子也尽有出色的,大家闺秀何必跟她们比这个。
“我便是不服气!我这庶子媳妇恁的不得志,小四跟小七这庶女倒自在得很。”三太太恨恨的叹气,“偏偏你二舅不争气,又打了败仗。”更是让人颜面无光。
生厥江一役,苗家二舅爷也是一场激战,身受数创,无奈时运不济,随同大军败退。如今天朝虽是二度征讨安南,苗家二舅爷身上有伤,却上不得战场,只有仰天长叹的份儿。
谢绮年柔声劝慰三太太几句,“您歇会子午觉,可好?”哄着三太太睡下了。每日,只有三太太歇息的辰光,谢绮年可以松口气,到华年处坐坐,说会子闲话。
“好生服侍太太。”谢绮年临出门,吩咐大丫头怀书,“太太要茶要水,不可怠慢。若太太醒了,速去回我。”怀书盈盈曲膝,“是,二小姐。”
望着谢绮年扶着小丫头出了门,怀书轻轻叹了口气。可怜,尚未及笄的姑娘家,整日一步不离的看着自己亲娘,唯恐她再出什么岔子,再被撵回娘家。二小姐也是怪不容易的。
华年正坐在侧间窗下临贴子,见绮年进来,忙站起身笑着问好,“二姐姐。”她俩一年出生,相差不过数月,小时候一处长大的,情份自是和旁人不同。
绮年和华年手拉手坐下,小丫头上了茶,绮年看见桌上的字,笑道:“三妹妹字写的越发好了。”华年微笑摇头,“哪里,转折之处总是难以自如,略有凝滞。练了这些年,总没多大长进,让二姐姐笑话了。”
二人正说着话,小丫头过来禀报,“二小姐,三小姐,家里来了远客。是四太太娘家两位外甥,从京里来的。”谢绮年忖度着,既是来了亲戚,怕是二太太和三太太都要出面待客,该备些表礼之类。便起身告辞,谢华年也是一般想法,并不多留。
来客是岳泽、岳澄。这两名少年分别跟沈忱、岳池差不多大年纪,岳泽比沈忱略小几个月,岳澄比岳池略小几个月,从小打到大。
岳泽十四岁,岳澄十一岁,两个男孩儿身量并不错什么,都是一般高大。岳澄自出生起,便是个傻大个子,长大后更是比同龄小孩高出一头。
两人一般打扮: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身着宝蓝箭袖,脚登青缎朝靴。长相也极为相似,都是长眉入鬓,目若朗星,英姿勃勃。
岳澄正跟四太太诉苦,“姨母,忱哥儿、池哥儿都能上战场了,我们哥儿俩连出趟远门都费尽周折。”“娘亲不许我们出远门。这回是祖父要去湖州,我们跟着祖父出的京。”
四太太含笑听着。大堂姐只有这两个嫡子,岂有不上心的?堂姐夫又远镇辽东,成年累月不在靖宁侯府,也难怪大堂姐过于胆小。
“其实我们跟着去湖州也蛮好。”岳澄个子虽大,年纪尚小,还是一团孩气,“可惜傅侯爷嫌我们慢,不肯带我们。”他俩本是跟着傅深、岳培一起出的京。傅深心急,“要不我先走一步?”岳泽岳澄骑术还欠着点儿,体力也不够,拖后腿。
岳泽大上几岁,性情又似他父亲岳霆,一向沉稳持重,笑道:“我们哥儿俩数年未见姨母,可是想念得狠了。”把话岔了过去。
叙了寒温,岳泽、岳澄随四太太到萱晖堂拜见了老太太、二太太、三太太,随后又拜见了谢老太爷、谢四爷。岳泽岳澄相貌英挺,礼数周到,很讨人喜欢,收了一大堆丰厚的见面礼,在谢府住了下来。他俩要等到岳培从湖州返京,才跟着一起回。
“表的!”谢锦年、谢流年自然是要见见这两位表哥的。两人一个三岁多点,一个不到三岁,还是常把“哥哥”叫成“的的”。
岳泽彬彬有礼叫了“六表妹,七表妹”,岳澄则是眉开眼笑蹲下身子,“两个小不点儿,再叫声哥哥!”两个小粉团儿似的妹妹,真好玩。
谢锦年又乖巧的叫了“表的”,谢流年不肯再叫了。这种半大孩子最烦人,懒的理他。眼前这岳泽岳澄是张伯伯的侄子么?跟张伯伯不怎么像啊。
两位小姑娘对表哥不过尔尔,见面知道是表哥,不见面就忘了。府中三位大姑娘则有所不同。谢绮年、谢华年、谢丰年自然也和岳泽岳澄见过礼,面对高大英俊、老成持重的岳泽,三位年龄相近的少女有的面孔微红,有的神色自若,有的害羞胆怯。
多多少少都有点动心。岳泽家世没的挑剔,父母都出自名门。父亲是靖宁侯府嫡子,如今任辽东总督,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母亲是汝南韩氏嫡女,温婉端庄,素有贤名。岳泽人才又很出众,年貌相当,再没一点不好的地方。
“绮儿,我看这人还过的去。”三太太见过岳泽,心里乐开了花,“虽是没爵位,好在父亲能干,将来便是靖宁侯府分了家,日子定也不差。”想的很长远。
谢绮年羞红了脸,低喝道:“娘,您小点儿声!”怕别人听不见还是怎么着。咱们是女家,要矜持,一定要矜持。否则,会被人看轻的。
三太太笑着打了女儿一下,“你娘亲我,这不是高兴坏了么。”一时得意忘形。从前我就盘算过,四太太娘家堂姐的儿子不错,如今看来,我眼光果然很好!
二太太冷眼看了几日,三太太常到四太太处说话闲坐,四太太客客气气的,却不兜揽,便知四太太无意此事。华年和绮年身份相同,若是绮年不成,华年也是一样。
华年多好的姑娘,全吃亏在出身庶房!二太太出了半天神,恨起出身。如果华年是大房的姑娘,或是四房的姑娘,四太太哪会如此。
谢家从上至下待岳泽都甚好,老太爷老太太关怀备至,谢四爷四太太嘘寒问暖,即便二太太三太太这面子上的亲戚也是一盆火似的赶着。更有三位正值豆蔻年华的表妹,时常送来自做的奇巧糕点,殷勤待客,曲尽地主之谊。
岳澄也没闲着。他如今既没父母管束,祖父又不在身边,好似脱了缰的野马般,每日只在族学中露个脸,便溜出去玩耍了。也无人认真管他,岳澄自在了。
“小七,听表哥的话,表哥送你洋娃娃。”岳澄蹲下身子,低头逗弄谢流年。谢流年冲他伸出一个小手掌,“五个。”我有五个洋娃娃。
“那,表哥送你万花筒。”岳澄比划着,“里面可好看了,千变万化的!”谢流年依旧冲他伸出一个小手掌,“五个。”万花筒我也有五个。
岳澄不死心,“小七,表哥送你望远镜!”这可是希罕物事,民间少之又少。谢流年一脸淡定,还是冲他一个小手掌,“五个。”张伯伯送了一个,张家四兄妹各送了一个,我有五个。
岳澄拍拍脑袋,恍然大悟,“小七,你还听不懂话呢。”原以为她是真有。才刚明白了,敢情她还是个小傻子,不管自己问什么,她都是伸出小手说“五个”。
你才听不懂话呢!谢流年白了他一眼,迈开小腿咚咚咚跑了。张伯伯这侄子,跟他说话可真费劲。
靖宁侯府有两回派了管事过来,大车小车的拉着不少补品、药材、表礼、彩缎等物,一则是给老太爷、老太太请安,二则是想接岳泽岳澄回京。岳泽无可无不可,岳澄不走,“哥,再玩个一年半年的。”谢家好玩。
一直玩了大半年,玩到征夷大军攻破多邦重镇,攻破盘滩江天险,安南大溃,乱党首领被擒获后槛送京师。天朝终于一雪前耻,皇帝大喜,对征夷大军全面封赏。封张雱为南宁侯,岁禄两千石。
“小七,你张伯伯打了胜仗。”谢四爷怀中抱着小女儿,手中拿着张屷的信,脸上有淡淡笑意,“张伯母和一双幼子幼女从湖州动身去京城,很快会路过太康。”到时又可以见面了。
“你张伯伯打了胜仗”。什么情况?张伯伯什么时候去打仗了,我怎么从未听说啊。谢流年转头看着谢四爷,大眼睛中满是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