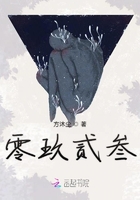南宫灺下意识的手指抖了抖。
南宫汲花在她面前蹲下,伸手拭去了她额上因痛楚涔出来的冷汗,“既然已经是内定了的殇清宫下任宫主,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些个狐媚惑人的法子向来是些个下作的妓女惯用的,你将是一宫之主,就该首先知道宫主之尊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光线透过窗纸进来,淡淡映照在男子身上,地上的剪影与地毯花纹相映,俊美似神祗。
女子垂目,“灺儿明白了。”
南宫汲花起身,“把手接好,继续到外头倒立着,宫规、《女戒》各百遍。”
“是。”
南宫灺平静着神情,接好手骨,起身出殿。
刚踏出门,凌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刀刮似的疼。南宫灺搓了搓手,继续往雪地里去。
南宫灺已经不记得这是她这个月来第几次受罚了。自从她莫名其妙被三位宫主当众立为殇清宫唯一的少宫主后,三天两头免不了一顿罚。从言行规矩到武艺考校,再到内事决策,稍一有错,就得受罚。
以至于无论在哪远远见到了三位宫主,她都恨不得多长几条腿马上飞奔避开。
她曾问过姑姑,她这一辈,堂兄妹这么多人,为何偏偏选中了她?
当时,姑姑支着脑袋想了半天,然后,很认真的看这她,说:“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坐得了,他们思来想去,觉得也就只有你才承受得住。唔……换做旁人,被这么天天逼着,是会疯的,真的。”
姑姑随性惯了,加上有姑父撑腰,说什么话都不顾及。
后来,她又问了她爹。南宫汲花当时心情很不错,携了她手带着她跑到了房顶上,伸手指着黑宇那轮明月,问她,“好看吗?”
那天是十六,月儿很圆。她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接了一句,“好看。”
“旁边的星星比月如何?”
“如你所说,繁星虽美,不及月明,不及月亮,不及月大。所以纵观天宇,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月。星不及月,那月便为尊。”顿了会儿,泥眼看她,“你还要问我刚才的问题?”
南宫灺摇头,心下雪亮。
南宫灺已经不记得自己和她父亲的关系什么时候竟然越走越近了。她曾经,是那么想要杀他。
整整四年把母亲关在小院,不闻不问。母亲盼了他那么多年,想了他那么多年。到最后一死,那份期盼也没有少过半分。
当时,南宫灺是真的想要杀了他。凭什么他可以对她母女不闻不问这么多年;凭什么他明知道母亲的那份心,却依旧弃之如履;凭什么母亲死了,他可以那么无动于衷,除了一句“葬了”,什么也没有……
他讨厌她看他时的眼神,不止一次两次威胁若再用那种眼神看他,就挖去她的眼睛。
她知道她的不自量力,匕首刺过去得瞬间就被察觉到。然后,是手臂陡然大痛,被生生的扭断了骨头。
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她,“弑父?”
“你不是我父亲!”她扯着嗓子对着他吼。
他俯身下来,她以为她触怒了他,她以为他会杀了她。
可谁知他只是对她说,“杀我?你还没那个本事。”
接骨,和断骨一样疼。
“就叫灺吧,南宫灺。”
南宫灺,她的名字。母亲生前盼了那么久想让他给她一个名字,可是现在名字有了,母亲却永远听不到了。
接下来她就病了,身子滚烫得厉害,很严重的发烧。姑姑端着药急得厉害,她躺在床上,不想让姑姑操心,脑海晕晕沉沉的,浑身无力,她望着房里荧荧的光火,她想,是不是她这么死了,就可以去陪娘亲了?
一直不喝药,姑姑眉里满是担忧。然后,他进来了。
火红的衣服,刺得人眼生疼,明明母亲今日过逝,他怎么就能一直穿着这么惹眼的红?
她愤怒,她恨,可是她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
“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真会把你的眼睛剜出来。”他一开始,就是这句话。
她不说话,只是狠狠地盯着他看。
他端起桌上那碗药,递过来,“想杀我?没力气你怎么杀?”
她鬼使神差的接过那碗药,一口气喝下去。然后,她听到他说,“我给你机会杀我,不过你得先活下去。”
然后她被送去了殇清宫的稚养所。
稚养所,是殇清宫所有暗卫最初培养启蒙的地方。
这里,不论年纪大小,只按照不同能力编排组别。从最上的甲等,到最末的戊等。等级越高,待遇越好。等级越低,便是数不尽的苦难。
她被直接送到丙等。中途插进来的人,年纪小尚且不说,且分到了中等位置,自然被多人所不容。再加上她不善同人交谈,也不大喜欢同不相干的人相处,是以,所有人都不待见她。
充满竞争的环境里,多的是手段高明的设计陷害。进去的前五天,她天天被罚。实打实的倒刺藤条打在身上,每一下都划破皮肤留了血。
白天,同众人一起习武,晚上,课毕后受罚。
受罚永远不会耽误上课的时间,但如果因受了罚而耽误上课,那么罚后还有罚。
来稚养所的第七天晚上,她上完课,白日里被罚一个晚上装满天井所有水缸。水缸有十口,个个比她人还高。风寒刺骨,井绳子又粗又冷,一桶水一桶水的打上来,她人小,力气不大,虽有几分内力,一个时辰过后也是累得再使不上劲,而那边的水缸才不过堪堪满了两个。
这时候,她面前出现了一个人。黑衣黑发,她认得他,他是那个人的近卫,叫做随花。
她被带到了那个人的书房里。
她的匕首随身携带,一直不离。一接近他用最近新学的招式奋力朝他刺去。结果,同上次一样,被他轻而易举的制住,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卸掉她的手臂。
匕首被反抵在了她的脖子上,匕首冰凉,贴在皮肤上,刹那间浑身血液凝固。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离死这么近。
“要想行刺一个人,就必先要弄清楚自己的能耐。连自己都不相信能伤得了的人,还要去伤,那就是不自量力,就是找死。”烛光之下,男子盯着她,缓缓说了这些话。冰寒的眸子里,稍带了几分严肃,匕首收回,“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领罚吧。”
这是他们之间早就定好的约定,那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红衣男子,光华斐然,“你若想杀我,随时随地,我任你动手。若能伤得了我,有赏。若出手伤不了我,便受罚。若什么时候你成功得手杀成动了,那便再好不过,届时,不但没有人追究你事责,我所有一切还都会是你的,包括随花,包括殇清宫的宫主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