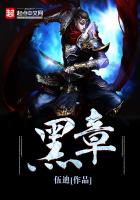晴朗。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感到阳光就在指尖跳跃,是温热的、洁净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光,在清晨的风和树叶的合力编撰下,一漾一漾的。晴朗,有时候可以和天气无关的,而是一种由心而生的状态,诸如现在。我看见西边更远处的群山淡青色的剪影,也是风生水起的样子,看不出山的脊梁和气势,是水墨画中的没骨画法,那是沉默的远山。
假使还有额外的豪情去给每一座山起一个崭新而自我的名字,又会叫做什么呢?是龙,还是马?把那些显然牵强而拙劣的名字附加在某一座山上,除了作为地标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柔软的山脉和身旁坚定的石头,共同组合成了山的意象,远和近、轻和重、虚和实,是相片和底片的关系,当它们重合在一起,才有了切实的质地,有如过去和现在。
穿云破雾的阳光明媚流泻下来,远山逐渐显现,转眼间似乎挺直了腰杆儿,是一座苏醒的山,一个晴朗的男人的形象,似乎随时准备上路。在北方的大平原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
这一条路,我们究竟走了有多远呢?
这里的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多的是在内心、在成长的漫漫征途中——或许更简单的归于时间的行列。你我都清楚,那不是以客观的、恒定的每时每刻所能标注的,而是一些看似重要的段落和一些显然平淡的字句所组成的一篇文字,没有结论,没有中心思想,是一条无归的路。
有人说,青春对男人来说其实比女人更珍贵,也更迫切。那一段身体强健却还没有到肩负责任的时光,奔放而自由、轻松而清洁,真正堪称流金岁月。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在青春之中尽情地奔跑,那么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当然,这里的奔跑应该是流浪,或漂泊的意思。也许类似的比较本身就是虚拟的,一个女人站在男人的立场,或一个男人尝试用女人的思维,看待“青春”,看待这一段在任何生命过程中都金光闪闪的时刻,都会蒙上一层虚化了的繁华的幻影,包括美丽的憧憬,或惆怅。
所谓晴朗,是远离了一些纷至沓来的阴影长舒的一口气,是走了很远的路之后对脚步、对生命的一份感念,那不仅是窗外的晴朗,还有内心的,由内而外的一种关注。
从某个年龄回望青春,感触或发觉的光影肯定是不一样的。三十岁回望也许仅仅是淡然,是门里门外的光景。四十岁回望也许会逐渐看清了往昔的迷雾,不仅仅是对自身的伤怀,而是重新建立起的对青春的崇敬。五十岁回望,是理解,是宽容,是对从前走过的弯路,遇到的坎坷,而“进行”的一次深情的抚摸;于是,那崎岖的,充满褶皱的一段路,将平滑如绸,一马平川。六十岁回望,看到的也许已不是风景,青春早已消融到身体、到血脉、到气质之中了……再三回望,却是由外而内的,渐行渐近的,晴朗。
从青年——中年——老年,到底如何清晰地划分,哪个年龄可以充当确切的分水岭呢?一切都是在循序渐进中,遁了影踪。你所看到的那条路,雪落无声。
既然时间是一条绵长的路,那么可以将前尘和后世清理得泾渭分明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分得清楚的。不然,原来和现在就像一团乱麻,牵绊人的脚步。但是仍有一些牵挂——说来话长。
生命,在漫长的枯萎的过程中,让人忘记了曾经可能有过的昙花一现。前尘后世的分野几乎是一条笔直的路,大路通天。
当生命向前倒叙,从前的日子就是一座浑厚的山,风化和开采同时进行,风化的很可能就是你想牢记的,而开采的恰恰是希望遗忘的——望和忘,在晴朗的天空下,相互对峙,胜负难决。
并不是说值得庆幸和总结,在那段被称为青春的时光里,我有过一次又一次远行的经历,我甚至想说是飞翔。那种对个人而言最接近自由的状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片海到另一片海,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通过不断变换的距离,得以一次又一次打量本来的地方,那一年的海,还有我结识的最初的山。
远行,完成了本性中向外拓展的梦想,而距离使我更接近内心的需要。放眼风物,从梦想到需要,说不清是上升了还是下沉了,只是站在今天这个点上,开始体会到一种携着两袖清风渐渐挥散的平静。
走了这么远的路,我想带着晴朗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