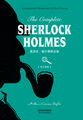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三木老师为我题的一幅书法作品,立轴,草书,五个潇洒狂放的字——天地一沙鸥。七年了,一直就挂在那里。当初洁白的纸张已被熏染成了老旧的暗黄,浓郁的墨迹仿佛也柔和飘逸起来,只有赤红的两方印章依然鲜艳。挪开画轴,墙上有雪白的痕迹,是再也消弭不了的时间之痕。墙上的纸已经泛黄了,纸背的墙完好如初,时间就在如此平淡的张贴之中露出了行脚。再看这五个字——“天”字浓墨重彩,是结结实实的一方穹庐:“地”字纤巧秀丽,有些像一块晶莹的“顽石”,闲倚在海天一色当中:“一”是轻松的一个点儿,起笔落笔全没费心思,但折回来的“沙鸥”已是枯毫渴墨,自上而下,天地全然不见了,只有一双豪迈的翅膀,是笔触极深的——懂得。若非了解,老师不会题赠这五字给我的。若非爱惜,我也不会一读就是七年。这幅书法,几乎可以代言我对行走的期盼——天地一沙鸥,有一点儿孤单,更多的是自由。在沙鸥的目光里,天地任我行,在天地的怀抱里,全是本色和性情的体现,一展一合,一动一静,所谓天地的大美,尽在行走之中了。这几个字挂在北墙上,稍一侧身我就能看见它,空闲时,我就看一会儿字,已经没有什么感触了,是习以为常的一个场景。南窗的阳光照不到它,反而在阴霾的雨季,这几个字尤为皎洁。这字、这窗形成一种经年的对视,我坐在中间,一边是理想的或者说曾经的天地,一边是熟稔的现实的四季。窗外,就是我的西山了。遇见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一遍又一遍用目光勾勒那一笔温婉的曲线,起落处是树、是楼,它们都在不断地生长,向蓝天和白云索取空间,我的西山越来越矮了。原来,我坐着看山,现在只能站起身来,才刚刚够着那一抹快要被覆没的山脉。用不了多长时间,山注定会被掩埋于钢筋丛林之中的,这里坐着的,也肯定不会是我了。关于离开,倒没有过多的想与不想这些主观的方向,该走的时候那就走吧——也是一种行走,在九月的风,四月的雨里。我又看了看山,今天浓雾紧锁,我看不到山,但是我知道,山在那里。
山在那里,几乎是所有远行者的铮铮之言,成了淡定中的一种信念。山不再只是山,诸如前路、明天、抵达、经过、回忆、永远等等代表时光或时间的词语均可落座,它们会奠基成一个人的山脉,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它——存在。即使永远不能抵达,也是一种肯定会有的经过,在时间里,在生命中。我没有机会或奢望遇见许多山,仅此一座,也就足够了。前路的山水不曾许诺谁的约期,明天的晴朗或阴雨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色,那么,走吧。在行走之中,我想告诉你,抵达只是一段插曲,有则更好,没有也不必遗憾。在途中你会读到许多值得记取的地方——山穷水尽处的一块碑石,镌刻着一个人曾经在这里挺立和安息;茫茫戈壁的一棵胡杨,让人在无人之境看见了绿色的生命的象征;寂寂渔村外的一条破船,用疲倦的身躯展览破浪的历史;竹林深处的小楼,艳粉色的一角儿衣裙转瞬不见;冬日的海,是个肃穆的长者,与老一辈的灯塔喃喃叙说,悠长而细软的沙滩上是字字句句的沙砾,涌上来,退下去,一夜一夜来来往往……类似的印象和片段,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回忆行走的历史,我将其归结为血脉里的动荡因子。做一个纯粹的浪荡子曾经是我长久的梦想。从上路开始,我就接近了远行的真谛,用心、用目光去爱一路的“种种”——这两个字可将其视为空格,可以自由填写由心而生的字句,可供选择的有:风光、民俗、历史、人文、气候、猎奇、眼界和心胸。通过行走而改变的视野,通过心胸而拓展的世界,相比之下,我看重后者,后者不仅仅是一个字词,而是随时随地涌现地“敞开”,几乎可以细化到以厘米为单位,我能用内心的标尺去衡量,在某一瞬间似乎可以达到完全敞开,那,也许就是“天地一沙鸥”的感觉了——你相信自己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你相信自己能用双脚丈量世界——世界在此仅仅是一条首尾相牵的长路,只要走,哪儿都可以走到。看看脚下,你也许仍在原地,可是会飞的心却在高处俯瞰大地,那里有翅膀的影子,也有路过的一块石子。
影子和石子,虚实如此和谐统一。在路上,你所要的是影子还是石子呢?如果说追求影子的是理想主义者,寻找石子的就是现实主义。我没有两全的答案,也不会自作聪明地说两者兼得。在家是梦想者,出门是实干家,也许是最理智的结合。我更希望留下的是石子,带走的是影子——影子和石子都是记忆。我还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连石子都不要了,那是真正完成了行走之后的放心,不是时间的缘故,而是更轻松的看山、看云、看海,这些凝固的往事,往事如烟。
相对行走而言,我已留下太多的文字,几乎躲之不及。但是在这篇长长的文字里,行走是不可或缺的一章,为此我很犹豫。当然,我想记录的不仅仅是至爱的事物,而是生活的某一部分。关于行走中的目光已经在所有的文字中澄清了,在某段旅途有过如何感受也成了确凿,我没有一个更高的角度纵览小半生的痕迹,那么,权当是一纸索引吧。让我引以为荣的旅途文字是《西行漫记》,十一章,时间、地点、目光所及。现在想来,那几乎是为了文字而走的一条长路。在颠簸的车里,细沙呜咽的苍原,阴云密布的草原上一束圣洁的光,百年沉睡的胡杨林得到的那一篇是豪华至极的写作,在小城微笑的眼睛里微笑,在西域亘古的城池里漫步,我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声不息。心底却没有任何感慨,走了,就不再回来,每一站都是结局,文字就是结局之后的空白。
不知怎么回事儿,在许多陌生的地方都有人向我问路,在云南有人向我打听西山的景区,在海南有人问我港口在哪里,在威海有人问我韩国城的方向,在内蒙有人问我九道桥的位置,在缅甸还有人问我金殿怎么走……我从背包里拿出地图说,我们一起找吧。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在路边席地而坐,并且我从不带大大的背包,或者仅仅出于我安静的神情。不论去哪儿,都是一个深蓝色的自由马的帆布包,我不需要背负什么,在路上,什么都可以自行解决。我欣赏的行走是一种放逐,自我放逐。我的祖先逐草而居,我连草都不要,是一心一意地行走。已近中午,虽说雾散了,天色依旧。
你看见过如此昂扬的行走吗?昂扬,没有其他字句来替代它。他的脸映着高原的阳光,双臂在缓缓舒展,似乎借着一阵风就可以逃脱地心的引力,那是比“飞翔”还要自由的状态,飞或不飞都不再需要某一个理由。他的脚步坚定而轻飘,走得很快,却不是为了奔向哪里,只有行走——才是《行走》的主题。他的身影被牵扯得细细长长,路过的土墙和他一起浸润在纯净的阳光中,是和草一样的坚强。
行走,更多的时候不是“看见”,而是“想见”。同一个人,同一种心思或目光,把不同的山水看成一样的风光,一样的平静和坦荡。他还在行走,在内心行走。
这不是行走中的某个段落,是终极。
如果说那幅书法作品是开篇,是结局之后的留白,那么现实中的行走应该多一些断定了。真正的旅行是精神上不断延伸的地平线,不需要归属感,也许,连“记得”也不要——这是我听见或感受到的——关于行走最“冷酷”的断言——连“记得”也不要的旅行,那么只剩下走了吧。
也许对每个真正的行者而言,旅行的唯一通途就是不断前往,他只有“出发”,没有“回来”,不存在通常意义上存在的这个圆。
精神上不懂得放弃的人也许根本不懂得旅行。如此想来,一次旅行有了些许“悲壮”的意味。但是能够发现这种视角,却不是一次旅行所能达成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另一层面或另一高度上的旅行,可以引入哲学的意境。
在当今旅游繁荣,温情款款的行列中,一个不要归属,不要记得的人显然是另一个疏离、异端的存在。那个正在前往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原乡。
在“旅行,怎能没有这温柔的心意”或类似的软语呢喃中,如果完全接受这种“真正的旅行”还真的不容易,那是需要阅历、胸襟和性情衬底的。
为什么酷爱行走呢?我想是为了获得或体会一种最大程度上的自由。从起初的见山见水,到后来成为一种日子,一种如约而来的节气。人在旅途,应该是一种敞开的状态,因为陌生,所以能尽情吸收,因为融合,所以能达到如鱼得水的宽阔的快乐。
我们不断地寻找更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个“更”字既是源泉,也是动力——热闹的、安宁的、需要许多诉说和聆听的、需要许多陌生的地方来敞开内心的、富足的、知足的……不一而足。反正都是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的生活方式。
你找到了吗?期待变化是一种本能,当然这种变化更多时候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授意于我们的。有时干脆想,其实改变我们的仅仅是时光。
《春——夏——秋——冬——春》……这部电影被译成了《春夏秋冬又一春》,虽说朗朗上口,可毕竟少了一些韵味,少了一些过程渐变带来的停顿和畅想。从前,常常去扫院子里的落叶,它们甚至都变成白色了,仿佛已经吐尽最后一抹绿意,变得轻脆而短促,它们窸窸窣窣地聚成一堆儿,随后被清理干净。我经常把落叶埋在土里,当然这比倒掉麻烦一些,是想让它们继续生存,用另一种方式。
当落叶化作泥土时,才完成了真正的使命,可是它们的心里还会有花儿吗?一直在寻找,生活因此多了许多意味,你找到了吗?找到的人应该庆幸找到了,还在寻找的人也应该欣慰找过了。
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定格在路上,我喜欢在异地的街上游走,透过一扇扇小窗打量另外的生活。窗子是必要的,正因为深知这里不属于自己,所以才多了一些肆意和松懈。人在异乡,更容易发现自己——不被人知的,自己也不常追究的,或者视而不见的——坚强和脆弱。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那么至少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这个“宽”字,既是眼界,也是心胸。走的地方多了,自然也就增强了面对困难的韧性。人这一辈子,仅仅在大平原上纵横是不够的,还应该置身一种生命的高度,放眼望去,云海一色,那时候我想应该能放弃困扰你的小恩小怨,潜心体验无风无浪的平静。
这种寄望追求宽阔和体验的过程,是旅行的前提。真正走在大地上也只有不断延伸的地平线,一个不要“记得”的人一定会完整地投入到当下的行走之中,因为深知不可重复,不可描摹,甚至连记录都是可有可无的,我能想象到他的宁静——更远,更行,还生——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