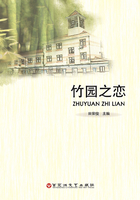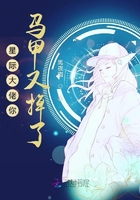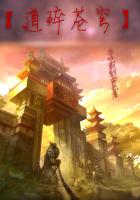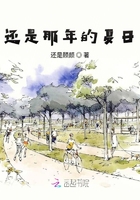在乡里,我的爸爸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有志青年。这有志主要表现在他的不甘穷困,除种田外,兼做过种种营生:养鱼,养鸭,养蚕,种西瓜,以及其他长长短短许多事情。这些事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每一样都把原本已十分为难的家计变得更为窘迫。我们读三四年级时,养蚕热曾风靡全乡,听说蚕茧能卖钱,许多人家把水田晒干,翻成地,种上桑树。而原本,村里是一棵桑树都没有的。有一天爸爸回来,兴致冲冲告诉我们,他把上面李家村一个荒坡承包下来了,准备种桑树。春天里别人家的桑树已经开始长叶子,等到星期六星期天不用上学时,我们姐妹五个才跟在爸妈后面去坡上挖地,把柔弱的桑树苗种下去。然而山上没有水,离得又远,不能像田畈那样从塘里抽水浇地,这地后来只好任它荒芜。等到秋天,我们一家又上山去,把枯掉的桑树根挖回来。那一年蚕茧价格大跌,村里人也纷纷砍掉桑树,重新种田,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堆满了晒干的桑树根,用作冬天烧火的硬柴。
承包鱼塘是爸爸做得比较长久的一件事,从我记事起直到如今。虽然五六年前他已离开村子来到南京,村里却还有两口鱼塘是由他承包着的。这大概出于一种习惯的不舍,他总是说,过两年他是要回村子的。种一两亩田,养猪养鸭,养一塘鱼,种一些蔬菜。这样女儿们逢年过节时可以有乡下的东西吃。我希望他的理想会实现。我们村子多水塘,上上下下有十来个。在爸爸养鱼的全盛时期,他最多曾承包了附近的五个大水塘:草塘、三坝子、四坝子、四安塘和大叶菜塘。这不包括家里另有的两个小水荡。草塘在村子东南面,有三四亩大。大叶菜塘与草塘一边紧紧相连,是所有水塘里最大的一个,有八九亩地。三坝子和四坝子连成狭长的一带,加起来十几亩地,绵延在村子西北面的田野里。四安塘在村西,离村子稍远,是一个三四亩大小的四四方方的水塘。早先三坝子还没有被爸爸承包时,算作村里公共的财产,每年腊月将尽,村里的男人就要打水,分鱼。几架水泵架在塘埂上,从早抽到晚,第二天早上,水就抽得差不多了。灰色的塘泥裸露出来,渐渐被吹成土白,风一缕一缕的,钻进人棉袄里,冷瑟瑟的。男人们穿着高帮黑色雨靴下塘捉鱼,有时干脆就赤脚。鱼捉上来,村中所有人家,一户一户按人口平分,鳏寡老弱者额外多添一两条。
有一年捉鱼是在盛夏,因为天不下雨,要种晚稻秧,三坝子的水被抽得只剩下最深的两个荡子还蓄着薄薄一层。壮年主事的男人提议,干脆把最后一点水抽掉,大鱼捉上平分,小鱼归捉到的村民自有。消息一出,满村无论男女老少,提筐携笼,统统拥到塘里逮鱼。那场面比冬天分鱼热闹得多,壮年的男人把大鱼一条一条扔进稻箩,拖上岸来,一担担挑到村里一户人家的门口,倒在空地上,小孩子和老人都糊糊涂涂陷在烂泥里,满心欢喜叉出一双手去摸小鲫鱼、鲹鲦、小虾子、乱七八糟的小野鱼,带抓几颗无辜的螺蛳,投进腰上系着的小竹笼。有的妇女,因为鱼笼全被丈夫小子拿去了,拿一只瓷脸盆在身边,一面捉小青虾,一面指挥儿子:“麻虎子!常华子!那块那块!一条鲫鱼!一条鲫鱼!”她的小儿子慌慌张张扑过去,跋泥涉水,终于合掌扑住,一条小鱼逮在手心,笑逐颜开。
大鱼都捉上来了。一村老小沾着泥巴跑到场基上围看,村里最大的一杆星秤被借出来。秤鱼。一条扁担穿过秤绳,两个男人把装满鱼的稻箩抬起来,第三个男人移秤砣,一个做会计的记下每箩鱼的重量,最后统计人头:今年谁在家,谁没在家,没在家的要不要分鱼?一番口舌之后,终于算好每人得鱼几斤几两,家里人口多的这时要欣然接受众人的妒羡。鱼按种类和大小一条一条平排在地,随后逐家秤鱼,喧声不断,他家秤的是青鱼我家怎么就是鲢子啦,零头的鱼是要切鱼头还是切鱼尾啦,那条鱼真是最大啦,晚上家去怎么烧啦。渐渐鱼少起来,太阳已经西斜,屋宇和园墙都黄黄的,最后一家的鱼也穿着稻草拎走了,地面上只剩刮落的鱼鳞和血水,烟囱放出白烟。当天晚上,家家桌上都有一碗辣椒煮鱼。
这样热闹的分鱼场面,记忆里似乎再没有过,虽然这离爸爸承包三坝子还有好几年。草塘和四坝子是从我记事起就承包了的,也因此是我记忆中最为亲近熟悉的两个塘。年年初春,爸爸要去长江边买鱼苗。如今想来,大概就是去芜湖。那时却是无法想象的遥远,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以为爸爸一天回不来,要到第二天才能到家。爸爸有一个习惯,不管去哪里做客,夜里无论多晚,路多远,无论喝了多少酒,总要回家来睡。有几回深夜跌跌撞撞摸回家,裤腿上沾满山泥,手心都擦破了。乡下男人没有不喝酒的,否则要为人看不起。你要是一天清早看见村里某个男人变得鼻青脸肿,不是晚上和房里打过架,就是喝多了撞的。他们调笑喝酒喝多的,总要说,“不要晚上家去一头栽到塘里淹死了!”小时候夜里我在家里等门,心里未尝不起过这样的害怕,等啊等,夜太黑了,终于听见屋角爸爸的一声咳嗽,赶紧爬起来去开门。有时他是去远处吃喜酒,从口袋里掏出两包喜糖,拆开一粒一粒平分,看我们高高兴兴马上含到嘴里。有时喝醉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们很害怕,赶紧给他打水洗脚,然后躲到房间里。他却不依不饶跟进来,舞着手,抑扬顿挫地教训我们: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懂的不要装懂,这才叫真懂,懂不懂?——不要虚荣,不能扯谎,不懂的东西要问!”
妹妹只是装睡,我只好点头,唯唯称是。心里巴望他马上去睡觉。
爸爸初春时去长江边买鱼苗,很早就出门。我从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走的,多数时候半下午已回来了,挑两只装满水的鱼桶,清水里是两三厘米长的各色鱼苗。鱼桶是鼓腹的木箍桶,形制比平常的水桶要矮胖。没有柄,桶身钉有铁环,穿两根尼龙长绳。我们叫鱼苗“鱼花子”。常见的鱼花子有鲢鱼、青鱼、鳊鱼、胖头鱼、鲫鱼、鲤鱼。放得最多的是前两种。有时候也带回将孵化的鱼子,一颗一颗附在褐色的湿棕榈衣上,并不可爱。我们在村东有一口三分田大小的浅水方塘,爸爸把这里辟作专门养鱼苗的地方,砍净杂草,捞走长着两只大夹子的水鳖,鱼苗挑回来就放到三分塘里去。我们伏在鱼桶沿上看鱼,怎么游都密密的,聚成一团,热闹极了,真有如花的意思。爸爸用红塑料瓢舀鱼苗,一三一五数,舀进脸盆,再缓缓倒到塘里。他做着这些事,熟练而小心,不许我们把手放到鱼桶里玩,一面却教我们认鱼苗。棕榈衣上的鱼子用一根竹篙搭在塘上,棕榈衣浸到水里,下面兜着绿色渔网。等小鱼孵出,把揉得稀碎的油饼撒下去喂它们,长得稍微大些,才把渔网撤掉。有一两年鱼苗是装在密封的透明塑料袋里挑回来,里面是有氧水,我们很稀奇。这里面的鱼苗要小得多,几不及寸长,近于透明,只眼睛两只黑点,倏地就游转个身。
寻常日子爸爸时常砍一担草去喂青鱼,它们自己也吃塘里自生的水草和螺蛳。偶尔的清早,似乎也曾撒过糠米和油饼给鱼吃。渐渐鱼长大起来,我们就要跟着爸爸去打鱼。家里有很多渔网,一种有浮标的透明丝网,放在塘里成一线,鱼穿过时就被困住。这网是放较大的鱼时才会用,比如夏秋天农忙,哪一天晚上我们打算吃鱼,爸爸中午就去塘里,涉水把渔网放下去。到傍晚时收起来,总有一两条两斤重的白鲢。又有一种五角三面的绿色“赶网”,比较结实,用竹子撑起网缘,再把一根细竹子烧热擗弯成三角形,用作赶鱼的工具,用时笃笃笃在渔网空的那一面把鱼赶进去。这渔网一般是在水沟或浊水荡里赶泥鳅或龙虾时用。爸爸最常用的是一种白色“夹夹网”,形如弯月,约有两米长,两头系上两寸粗的长竹竿,打鱼时人站在岸上,把渔网叉开扬入水中,将竹竿慢慢在网前捣合,再用力将渔网拉起。一般有鱼塘的人家都有一只完好的竹子编的鱼篓,鱼篓上结着稻草绳,打鱼时系在腰上,抄手一条鱼,投进去便是。我家却没有,也许是太穷了,连这样的钱也舍不得花,正如别人家有好好的竹篮子,我家的竹篮却常常底上破个洞,就垫上稻草接着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