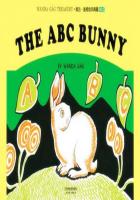到了1800年,伏打组建“伏打电池”——第一个可以使用的电池。在他的发明之前,科学家既不能真正地研究电,也不能利用电,因为他们充其量只能于瞬间捕捉到少量静电或瞬时放电现象。现在他们有电流了。于是,奥斯特恰好就发现了电与磁的相互联系,1820年公布于众。重大突破从法拉第和安培等人的实验室及计算中频频传来。19世纪的许多科学发现源于电磁理论,而电磁理论又是化学中应用电解方法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一个科学新工具是如何打开瓶颈的。
电、磁和光都是物理世界中同一能量不同的表现形式。实际上,研究者发现,能量可以转变成许多不同的形式:热、机械运动、电和光。许多科学家相信,能量是这个世纪大统一的主题,每一件事情的答案最后都归结于能量的统一理论。19世纪已有如此之多进展,以至于许多物理学家都相信,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只剩少数几个了。他们宣称,物理学的研究即将到头,因为有待发现的东西已所剩无几。(当然,他们错了。)
意欲包容一切的伟大追求并不只限于物理科学。生物学也有这样非同寻常的原理,由达尔文和华莱士所提出,用以解释如此多样的物种何以形成。随着每一次新航路的开辟,人们得以来到人迹罕至的地区,生命世界那丰富的多样性日益令人眼花缭乱。但进化论却有望解释这一切。再有,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对性状的逐代传递机理也提供了新的见解。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科学的统一可以通过理论的汇聚而得到。有些学者,像麦克斯韦,就认为科学的统一有赖于研究方法,而不是任何一种理论(不可思议的是,他本人正是电磁理论的创建者,而电磁理论正是有史以来伟大的统一概念之一)。特别是在英国,最常用的方法是类比或者模型,由此引出一个概念。(法国人则认为这种方法有些幼稚,过于简单。但是在英国,不同背景的科学家都发现,通过建构一个机械模型,一系列的概念就会源源不断出现。道尔顿、法拉第、汤姆生和麦克斯韦都发现模型非常有用。)
19世纪还见证了炼金术及其神秘主义的消亡,它曾阴魂不散,历经许多代,阻碍科学前进的步伐,尤其体现在化学领域。到了19世纪末,不会再有化学家提起某类神秘兮兮的物质,他们的前辈称之为“不可称量的”物质。就在18世纪,炼金术的残余几乎还在唱主角,并指导人们去探索化学反应(包括燃烧现象)的本质。热、光、磁和电都被看成是无重量的流体,可以从一种物质流向另一种物质。它们的存在不能根据重量检测,因为它们没有重量。拉瓦锡已经在怀疑“燃素”说,认为这是用以解释燃烧的另一种不可称量物质但除此之外,其他不可称量物质仍然是科学理论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接二连三的新发现才导致更为合理的解释方式。神秘主义的残余终于被科学彻底抛弃。
当科学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其力量和内在一致性时,争论也就随之而生。有些人不满意于科学抛弃了长期以来拥有的信念,这些信念包括炼金术、神秘主义和占星术。许多人不愿正视新理论,特别是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似乎与圣经的解释唱对台戏,并且抛弃了长期公认的等级体系,于是人就成了动物世界的一部分。
欧洲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思潮也反对科学,认为科学完全扼杀创造力,刻板僵化令人压抑。在德国,歌德和黑格尔成为主要反对者,他们把科学等同于机械论和唯物主义。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唯心论和浪漫主义的德国自然哲学风行一时。在法国,随着波旁家族在1814年东山再起,反科学的浪漫主义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思维方式,正是雄辩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在18世纪撒下的种子从而催生了这种流行风尚。卢梭曾为理性主义的《百科全书》写过很多文章,后来却信奉浪漫主义,宁可捍卫主观经验而不是理性思想。
有些知名的19世纪作家,诸如德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ёl,1766—1817)和卡特布朗德(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嘲笑“整个一帮数学家”,而法国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96)则陶醉于人类情感的力量,傲慢地写道:“数学是人类思想的锁链。我自由自在地思考,从而挣脱了这些锁链。”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类情感和个人主义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他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机器。他们看重具有主观性的“心灵”和想象能力,拒绝更具客观性的科学思维。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如此表达浪漫主义的心声:他“只确信内心的感受和想象的真实。想象中认为美的就一定是真实的……”。
有关进化论的激烈争论表明,科学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间已在开始发生一场较量。许多人对达尔文的解释感到心神不安,因为这一解释暗示,自然界众多物种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从共同祖先演变而来。英国几乎每份保守的报刊都登载过漫画,讽刺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赫胥黎,把他们画成猿、猴或大猩猩。但媒体对此的高度关注恰恰表明它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
16世纪哥自尼的时代已经远去,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受过教育的学者有望跟踪科学提出的辩论,大众不会有此兴趣。当科学,或者至少科学的一个公开角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时,这就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随着岁月——和发现——不断向前推进,焦点的强度也将随之增加。
结论
还有多少是未知的
幸运的是,科学,就像它所属于的自然界,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它属于世界,没有国家也没有年代。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无知,越感到还有更多仍然是无知的……
——戴维(Humphry Davy,1778—1829)
19世纪在科学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诸多重大发现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其中有:原子理论和几十种新元素,热力学、电和电磁学,多样化的、演变的物种和恐龙骨骼,动植物细胞和传染疾病的微生物。新工具和新方法不断涌现,例如电解和光谱仪,提供了通向元素、恒星和宇宙之门的钥匙。科学家相互启发(如法拉第与戴维,麦克斯韦与法拉第),互相竞争优先权(如戴维和周围几乎每个人),互相尊重(如达尔文和华莱士)以及诚恳地辩论(如赫胥黎和莱伊尔、阿加西等人的辩论),使科学思想百花齐放。这是一个科学终于使自己成为一门职业的时代。
但是到19世纪末,科学的核心已濒于变革的边缘。道尔顿、法拉第、威耶、麦克斯韦和亥姆霍兹所认定的绝对的终极真理,一种高贵的追求,看来将经受重大冲击。19世纪90年代正当新生一代就要脱颖之际——普朗克、卢瑟福、玛丽·居里、伦琴(Wilhelm KonradROntgen,1845—1923)、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和爱因斯坦,有某些绝对的东西似乎稳定不变:牛顿力学和它的三维空间及线性时间、热力学定律、被以太所包围的麦克斯韦电磁波。但是,20世纪的到来却带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也许所接触到的只是科学冰山之一角。
当普朗克在19世纪70年代末学习物理学时,他的一位老师曾劝他不要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只有少数几个遗漏的问题没有解决,总的说来,主要的发现都已经做出了。但是,后来证明,科学确实与它所考察的时间与空间一样,是无限的,而上文戴维的话,在19世纪末仍与19世纪初一样有效,直到今天这句话也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