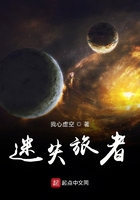答非所问的一句话令空气骤然凝聚,床上昏睡的人仿佛震了一下,攥着被褥的手哆嗦着,下意识的抓的更紧,而御妃落英脸上的笑却更加舒畅。芸桐锐眼低垂,歪靠在一旁的伏案上,注视着床上的一举一动。余光瞥见那女人的细微动作时,心头划过一丝冷意,唇边的情绪也越显意味不明。
“不认识!”
“也对,一百五十多年了,不怪没人记得。只不过,要是你能记得,说不定可以令她轻松一些不再压抑,倒还能多活几时。”
芸桐瞧见阿睇手臂上斑斑裂痕,犹如蜿蜒丑陋的虫蛇,潜伏盘卧着,好似随时准备要吞灭那个沉默的女人。他总是觉得,这个女人在用着一种他不能想象的方法折磨着所有人。
望了一眼窗外的天,御妃落英笑意更浓,好似在等待什么一样。云越积越多,风裹着尖利的呼啸横冲直撞,漏进室内的天光逐渐退去,冷寂凝肃慢慢扩散在空气里。窗前的条案上放着一只翻敞着盖子的锦盒,盒子里躺着一把乌黑古剑。长剑末端,猩红色的剑穗静静垂在边缘,风遛进窗缝时,它便幽幽摆动。
御妃落英盯着芸桐迷茫犹豫的侧脸,忽然扬手,一道飞虹射出,将对面条案上的剑穗割断,镖头飞出窗外,叮的一声不知碰落在何处。芸桐看着那猩红落在地上,忽然想起了阿睇袖口的鲜血。不知何故,他觉得好眼熟。
“如何,想起什么了?”走上前,弯身拾起地上的猩红之物丢给芸桐。那厢伸手接住,丝绒丝滑冰冷的触感像极了女人僵硬的肌肤,芸桐蹙起剑眉,心中泛冷。
“顾卿旸。”低声念出用黑线绣在上头的三个字,忽然眼前一黑,仿佛被人用黑纱遮了眼,脑海中骤然响起一句话:花暖夜相逢,同鸾未相知。
御妃落英低笑,猛地推开一扇窗,让强劲的风裹着一股腥湿气涌入,如同沉积了多年的腐朽一般,风中的气味让人心悸。
沉默。室内香炉中留下的灰烬偶尔还会散出些淡淡的香烧味,麝香的味道被卷进的异样阴冷冲淡。
良久,芸桐张开眼,脸上的紧绷悄然退去,径自一派道不清的沉默。背抵着条案,御妃落英颀长的身躯挡住一片光亮,笑嘻嘻的看着他缓缓抬首,看那深眸中敛住窗外最后一抹娇艳欲滴的血红斜阳。银眸流转望向那厢手中物,两根俊秀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上的长剑,一下一下,似在惬意等待。
芸桐瞥了一眼那锃亮沉黑的古物,云白长衫清逸飘动,长身走入一片孤风之中。
“就算我记起了这个人,又待如何?”
“不如何,小生只是好奇公子会如何看待此人。”
芸桐掀开床帏,床上的人依旧喃喃痴言,一只枯瘦的手摩挲在被褥间,似在找寻。垂眼冷瞧,紧蹙的眉毛拧起莫大的厌倦。
“此生,我只是个凡人……”他的话语间似有叹息。
御妃落英身后的风不知何时微弱下来,轻轻一笑,唇畔滞住轻微不屑,低声笑道:“好个此生为凡人!若说你芸藏皇族为世间凡人,那些平头百姓岂不就如同蝼蚁,这小小的萝睇也就是几两不知死活的尘埃!”
“皇族……又是芸藏皇族!”
“还记得不,那顾卿旸是如何待她的?”
呲啦一声,好似被刮掉了什么,芸桐呼吸一窒,甩过不善的眼色,却惹来对面更恣意的笑意。窗外淡月初升,映在闪过嘲讽的银眸中,月白的颜色显得越发沁冷。
“你到底想说什么?”
“呵呵,只是好奇而已。”然后,浅笑的人晃着袖子走开,不再多言。
“呜……”阿睇躺在床上似是不甚安稳,忽然伸起手开始在半空里划拉,抓住芸桐垂在罗帐前的衣襟便拼了命的攥着,嘶哑且模糊的低叹道:“别走……不要走……”
暗下眼中的波澜,芸桐扯起一边唇角苦笑道:“我若真能一走了之,又岂会拦不住你纠缠了这数百年间……”
寒山城距沧镇约百十来里,快马加鞭走个一天半天的便到了。虽说是近镇,却不若沧镇富庶安宁。到底是战事四起的时节,若没点底子也没得消耗。
夜晚,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虽然心里都知道一扇破门挡不住什么,可依旧将门锁上的死紧,想着能抵挡一阵便是一阵。风一吹,空荡的街上似乎马上便散开一声惶惶惊恐的哀叹,漫延在寂静的街巷里。
黑夜中慢慢聚集起了厚厚的云,隐隐听见闷雷在天际中滚动。要下雨了,丫鬟轻轻关了窗户,又悄悄为阿睇房中的灯添了灯油。芸桐吩咐过不要用蜡烛,那种虚晃脆弱的光亮不适合放在病榻前,总是会让人想到不好的预示。
照上玻璃灯罩,油灯的光亮昏晕古老,却很明亮。丫鬟转身出去,蹑手蹑脚的怕惊扰了坐在床边看书的主子。翻页时芸桐瞧了瞧床上,女人睡得很沉,似乎比傍晚时分安稳许多。
渐渐的,已经可以听到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像人在檐下低语。山城夜里的气温低,不比平壤之地,在街上泼一盆水,马上便能漫在空气中,冰冰凉凉的沁人发肤,雨一下来便更加觉得寒冷。
“少爷,您找我。”寒山城内芸府的周管事隔着蓝色丝绒的门帘,站在门口低唤。
“进来。”
周管事低垂着肩膀走进,芸桐未曾抬眼,他便恭敬的站在门口等着。一身旧衣裳,脚下湿了一半,显然浇了些雨水。虽早已到了春天,可雨天的阴湿冷寒却依旧逼人,管事从外边走进,周身带着沁冷的寒气,屋内虽然点了一个炭盆,也不见他觉得暖和。
“小人周福,给少爷见礼。” 周福低垂的眼斜斜的看了一眼那盆中的旺火,自往门边挪了挪,好似怕自己带进的风寒误了主子,便缩在门口毕恭毕敬的行了一礼。
看了一眼瑟缩在门边的乡下汉,五短身材却穿着一件灰旧长衫,被雨水涿湿一片,长长的拖在地上盖住了双脚,与那粗壮丑陋的身体极不相称。芸桐放下书,端起热茶饮了一口缓缓道:“天冷,近前回话。”
周福顿了顿,没往前走反而向窗边蹭了两步,一边傻笑道:“俺是乡下人习惯了,可别叫俺身上的寒气沾了主子的身,俺还是站这给少爷挡着风吧。”
芸桐不置可否,一边避着茶末,一边看像站在窗边的周福,问道:“你什么时候坐上的管事?”
“俺是去年接了自家大哥的班。”
“你哥是哪一个?”
“周安,前一任的寒山城芸府的大掌事,去年闹灾的时候病死了。”
“你家就你们兄弟俩?”
“还有俺爹,俺爹以前也是管事,就是出了那档子事后疯疯傻傻的不成样儿了。”周福说着,揪着袖子抹了抹眼睛,面露苦色。
“哪档子事?”
“这……”周福抬眼偷瞧芸桐的脸色,心中犹豫。一只粗黑的大手紧张地抓了抓腿,不知道该摆在哪儿。
“我不怎么来寒山城,对这的风土民情并不熟悉,你直说无妨。”芸桐温和的笑了一下,一对厉眼敛去光芒,白皙俊逸的脸微微侧向一边,盯着墙上挂的乌金古剑。周福闻言偷偷吁了口气,旋即也发现了静静悬挂在桌案旁的那口宝剑,下意识的吞了吞口水,说起话来开始有些吞吞吐吐:“就是……就是澜沧十年,我爹在后山上看见了活鬼吃人,还带着人上山做法驱邪,没想到回来后人就疯了。”
“噢?有这种事?”
“可不,对了,您知道这活鬼说的是谁吗?”周福忽然压低声音阴惨惨的说了一句,芸桐挑眉,看着眼前不知不觉已经走近自己的周福,沉声道:“谁?”
“就是一百多年前,忽然失踪的寒山城主顾卿旸!”
咣当一声,周福猛地将脚边的火盆狠狠踢翻,几块火炭翻出来掉在地上“呲呲”的叫着。周福吓的连忙退后,伸脚就要踢开芸桐面前地上的火炭,却被一柄乌金古剑横在跟前,挥开了他冒失的脚。芸桐不知何时已将那口剑提在手中,冷冷的声音像从阴间传来:“荒谬!既然是一百多年前的人又岂会活到现在?”
险些碰到那把漆黑的古物,周福有些忌讳的退了一步,五短身躯隐藏在长衫之下,脚下显得空空荡荡。
“回少爷,俺祖上十几代人都住在寒山城,那顾卿旸在一百多年前饮万人血炼不老丹的事很多人都知道……”
屋外,风雨飘摇,雨越下越大,积水自屋顶顺着廊檐流下,应和着周福那压抑低沉的嗓音,显得格外异样。芸桐脸色微微沉下,拿起桌上的一块丝绢轻轻拂过手中通体乌黑的剑身,将那剑鞘擦的锃亮。
“饮万人血炼不老丹?”
昏沉沉的灯光下,一旁翻扣住的火盆失去了生气,阴冷潮湿渐渐漫入屋里。长衫将周福粗短的身躯完全罩住团成一团跪在地上,细窄的眼睛偷偷看了看主子手中不断摆弄的长剑,黝黑的圆脸上泛着异样的光。
芸桐瞥了一眼他的神色,淡淡的问:“怎么?你害怕这口剑?”
低垂着脑袋,似是考虑了一下,中年汉子的脸上渐渐没了表情。许久,他才拖着长音冷凄凄的开口道:“俺自幼体弱胆小,最怕刀光剑影。这些年又有旧疾在身,所以才会害怕您那口宝物的剑气……”
“哦?你有什么旧疾?”
“少爷请看。”说着周福缓缓拉起一边袍袖,露出自己半截胳膊。芸桐顺势看过去,就见他手臂之上蜿蜒盘绕的竟是与萝睇十指之间流泻而出的那些藤萝如出一辙的图案。细看之下,又发现那缠绕在整条手臂上的藤萝之中,隐隐约约还有一些含苞待放的花朵。周福一边挽起袖子,一边又拉起另一只袖子,一模一样的图案爬满了他的双臂,自手背起延绵不断向双肩伸去。
“这是什么?”
“这是芸藏花呀,少爷!”周福低沉的声音中忽然掺进一丝不易察觉的阴惨。他双臂间乌黑的纹路并非是纹在肌肤之上,而是如同血管一般化在血肉之中。
“芸藏花为旧朝帝后之花,怎么会是这般模样缠在人的身上?”
“回少爷的话,小人祖上十代举凡男丁,必然生来双臂缠绕此花,随血肉之躯生长,每年花开一次,每次花开便要饮肉身血液,如此循环反复直至生命终结。”
“何故患此恶疾,可有法子医治?”
“这是萝族的芸藏血咒花呀,是世间最狠毒的符咒啊,少爷!可怜俺家原本就人丁不旺,俺的大哥便是因为气弱体虚禁不起每年受这妖花的侵蚀,最后气血衰竭而死的啊……”周福说着,原本低垂的目光一晃,偷偷望向芸桐身后的床帏之中,好似想起什么似的又道:“听说当年那位赫赫有名的城主曾捉回一名萝族女子想要探得萝族嗔咒中的奥秘……”
顿了顿,瞧了一眼桌上的灯,那灯火的光晕荡漾在寂冷的四周,晃动得人心都乱了,汉子眼角的皮肉忽然跳动了一下,仿佛不太适应直视那样的光亮,忙低下头又道:“只可惜,他虽然能找到甘愿为他舍掉性命的神族血脉,却始终得不到那至关重要的命玉……”
芸桐乍听他说起那块传说中的天石,厉眼之中不由得闪过寒光,冷下声音道:“你竟然知道命玉的事?”
那憨厚的汉子忽然抬起头,乡气很浓的脸上面无表情。他缓缓举起布满盘根错节枝藤的双臂伸到芸桐的眼前,早已没了方才的恭敬卑微,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阴戾神色。
“俺家的男人受萝族人的毒咒所害已有十几代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是靠着什么来施展浑身的妖法?少爷,俺是乡下人或许没见过大世面,可是要说这历代萝族之中的事,俺可是知道的多着呢!”
瞥见那乡下汉悄然握紧的拳头,芸桐的眼底划过一道暗流。手指撩起系于剑柄的那一截猩红的剑穗,状似无意的说道: “既然你知道那么多,不妨逐一说给我听听……”
风送夜寒,不知过了多久,周福才自房中退出。低垂的眼中漾起的笑意衬在他那张黝黑的圆脸上,说不出的别扭。屋内,一片死寂冰凉。芸桐依旧坐在阿睇床前,手指捻过那凉凉的一截残旧剑穗,心中如同豁开了一道口子。
一晚之间,有些早已不知从何说起的话,以及那些藏在心中不愿提起的事,便如同水中月雾中花,重重印上心田之后却免不了化作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