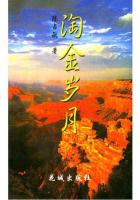我的任务是在百花宾馆门口阻住嘉城电视台的记者。
老孙昨夜十一点多打我电话,我正在看《苏东坡传》。他在那边兴高采烈地说,老方你在干吗呢,你知道俺老孙为什么这时候还打来电话吗?我说,我在火车上,要去南宁。我用笔连续顿在桌面上模仿出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音。老孙沉默半晌,我能想象出他眉头紧皱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来的样子,但我同样知道他将冒出来的仍然是陈词滥调。老孙说,这次非你出马不可了,没有人能搞掂了。我说,要不要给你带点土特产回来。老孙说,把所有真哥们都想遍了,俺老孙觉得除你谁也不行了,你不是在嘉城电视台法制频道做过一年嘉宾吗,他们居然要来采访我。我说,曝光吧。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如果是面谈,他肯定又会摆出一副夸张的忧伤无着的样子,我肯定又会因此手足无措,恨不得立即答应他,好让自己也轻松些。老孙突然十分爽朗地笑起来说,当然是曝光了,不做媒体的正面人物很多年了,可俺老孙明天要开全国招商会啊,你知道现在搞这么一次对我来讲多么不容易,我就指望它翻身了。我沉默。老孙说,土特产我明天就派专人去南宁给你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我骂道,救你会坑死更多的人呢。老孙嬉皮笑脸起来说,谁叫你认识俺老孙呢,我警告你,若帮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若不帮,我天天骚扰你,你换手机我天天去你单位去你家,你换单位换家反正我就是有办法让你逃不掉骚扰。我正看到苏东坡第一次被贬黜后游历密州,顺口给他朗诵道: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老孙在那头叫嚣起来,什么?记住,明天八点,百花宾馆,你把所有的龟孙子记者都给俺老孙轰回去。你一定得来,不然我死定了。
老孙可谓狡兔三窟,他对外宣扬的招商会地点是希瑞特大酒店,离百花宾馆几乎半城之隔。早上七点,老孙就将全国各地来的小商人和农民从下榻之地一车运到百花宾馆五楼。现在,五楼之上,老孙正西装革履苦口婆心地给他们洗脑,怀着悲天悯人的表情痛斥他们多么没有经营头脑,竟甘心错过天上掉馅饼似的发达机遇。我相信,老孙的不少员工现在还蹲伏在希瑞特的门口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知道这里的人少之又少。我站在初秋清晨的阳光里,无聊地寻思着自己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意义。
我曾经批评老孙,他底下那些年轻人一点用也没有。老孙扬着眉毛说,我想啊,但你这样的人才不是很贵么。他还看着我兀自点头说,谁能把握住你这样的呢,什么时候被你玩了还不知道。玩,是老孙唯一信奉的哲学,他要尽可能地玩人,并警惕不被人玩。面对老孙的现实状态,我找不出反驳这种实用主义理论的理由。老孙又不无下流地说,其实很有用的老方,年轻姑娘就是好,你今晚要不要。老孙底下百分之八十是刚毕业的女大专生,而且他最会装的就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尽管他以前真可能是),虽然近来我偶尔会看到,他一个人夹着小包,脚穿跑鞋偷偷摸摸地赶公交车。
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年头,穿警服的很多不是警察,扛摄像机的很多不是记者,尚还清纯的女学生们都露着大腿在街上、歌厅、酒吧里逛来逛去,而淫心勃发的中年男人们却严严实实正襟危坐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面对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我只能以摄像机为唯一判定标准。但针孔摄像机和袖珍录音笔本是我这种职业的必备用具。
我注意到,一个扛摄像机的人行进在一对迎亲队列中,八辆黑色豪华轿车停在百花宾馆的门口,新娘从宾馆里走出,迈着跳跃的步伐钻进彩球飘飘的车里,没有人欢呼,甚至没有人面带喜悦,除了鞭炮的轰隆噪音外一无所有。这位新娘是从宾馆里走出,然后在鞭炮的烟雾中绝尘而去的。
老孙正在五楼之上为他梦想中的富足口沫飞溅地挣扎,这位新娘正在为某种憧憬从此为人妇。初秋清晨的街道安静祥和,阳光温暖地抚摸在屋顶、电线杆、早点摊蒸腾的雾气和每个行人的额头上,一切都显得不动声色。那位摄像师可能想不起来为新娘纪录最后的这样一个安静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