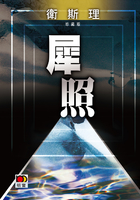是的,这的的确确是一群来自邻县的人。他们上山来的目的,是要给刚刚属于自己家的承包山划界的。就在几天前,这些人家通过抓阄的方式,分到了这一片偏远的“荒山”。由于路途遥远,山上多岩石多杂木,这片“荒山”远没有村子附近的杉树林、松树林、毛竹林受欢迎,所以他们抓阄抓到这里,连连叹气。
他们是背着背篓、石灰、油墨、柏树苗、锄头、斧头来山上的。他们显然在山下就分了工,谁用石灰标出各家承包山的分界,谁用斧头在立于分界线的树干上劈出一块白皮,写上一个“中”字(即“界”的意思),谁用锄头在分界处的空地上栽上一棵柏树苗,各司其职。然而,他们这一天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就被张德旺的出现打乱了计划。
他们听到“野人!野人!”的呼喊,赶忙丢下手中的活,从不同的方向,追赶起野人来了。没想到这一追就追了大半天,当他们终于追到野人的“老巢”,天色已经黯淡下来。抬头仰望,可以看见高高的悬崖上有一个不规则的岩洞,洞口被青藤遮盖,谁也不敢轻易爬上去。
“野人呢,野人长什么样?”
“长头发,黑色,披在肩上,脸长,上宽下窄,像马脑壳……”
由于当时目击野人的距离较远,大部分人都没有看清野人的真面目,有的说它个子很高,将近两米,有的说它跑得很快,一个跨步能达三米,有的说它浑身长毛,无尾巴……它长得像个人,但绝不是人,是一个公的……
总之,那个晚上,山洞下面吵吵嚷嚷的。那些来自邻县的人点起了篝火,烧起了吃的东西,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欢乐与成就中。他们已经派人回去借猎枪了。他们都在说着,自己一路上追赶野人的功绩(仿佛整个追赶过程,他才是最关键的),或者议论着,抓到野人后可能会得到很多奖赏。
“你们还不知道吗?听说许多年以前隔壁县有一个人,光是远远地看见了一个野人,国家就奖励了一千元!”
“是嘛?那我们大家都看见了呢。”
“要是活捉了这个野人,那该奖多少啊?”
“至少上万吧……”
他们越说越激动,觉得这个月光如洗的晚上,既新鲜又美好,有几个年轻人已经唱起歌来了……
可是,就在这些邻县人如过节般高兴的时候,对于躲在山洞里喘息的张德旺而言,则是活在另一个世界。
是的,蛇毒在他的体内扩散了,他的整条手臂发黑了,皮肤胀得裂开了,浆状血由伤口渗出,他感到浑身灼痛,他努力地支撑着自己,咀嚼蛇药,却吞不下去。他张着嘴,嘴唇抖动着,视线变得模糊,他能感觉到死神在召唤他。死神,跟野人一样浑身长毛,像猿像鬼又像人,狰狞地笑着……
不,不!我不是野人,我不要作为野人死去!我也是人……张德旺振作起来,他要爬到洞口去,说出他是谁……
然而,他的身体,万分沉重。像溺在水底。他东倒西歪,倒了下去……
他是被那些邻县人抬回去的。没有人以为他还能活过来,他们是把他当做尸体抬回去的。他们把他扔在村口,供那些闻讯赶来的人参观。人们拥挤着,伸长脖子,里一层外一层,高声地议论着他们看见的事实:一个传说中的野人。
这个野人虽然不像传说的那样高大、吓人,但是,它与常人比起来,的确要丑陋得多:首先它不穿衣服,只在身上吊一张兽皮,以此遮住羞处;其次是它的皮肤,就像树皮一样粗糙、发硬,汗毛更是要比人类浓密得多,简直就像稀疏的头发一样;还有它的脸,一张脸上沟壑丛生,嘴巴突出,颧骨很高;以及它的手掌、脚掌都很大,关节的弯曲也与常人不同……
一时间,张德旺的四周围满了人。人们一波波地涌来,对着张德旺指手画脚,议论着他与人类比较有什么不同。这个过程中,那几个参与了追捕野人的年轻人,一直高声地向新来的人讲述着追捕这个野人的过程。人们听了又听,简直比听说书更着迷。毕竟,这不是一头野猪或是一头熊,而是一个野人啊!只要想一想这辈子能亲眼看见过一个野人,就不枉来世上一遭……
只是,这个野人要是还能活过来就好了,说不定野人比猴子要聪明许多呢。说不定野人还会说话呢。有人就是抱着这样猎奇的心理,趴下身去探了探张德旺的鼻息,似乎还有一丝气,又掰开张德旺的嘴,发现舌苔又黑又紫,接着,他还把张德旺的眼睛翻了开来,没想到,张德旺的眼睑翻上来之后,他那足有乒乓球那么大的发红的眼珠子,就一直瞪着他了。
“啊!野人醒了!野人活过来了——”
那呼喊,又恐怖又尖利。所有人都跑开了。
跑开,又重新围拢来。
张德旺就这样陷于惊恐的目光和“嗷嗷”的起哄声里,他已经有太长时间没有见到如此多的人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感到很恐惧,挣扎着,想坐起来,重新逃到山上去。但是,他犹如坠入一个噩梦之中,动荡不了。
有胆大的人,试探性地问候他:“喂喂喂!野人,你好啊!……”见他直着眼睛没反应,以为他愚钝得很,就捡起一块小石子扔过去。
“喂,喂!野人!你不穿裤子,都露出你的小老弟了,你的小老弟倒是不小啊,哈哈哈……”
经他这么一提醒,大家都朝张德旺的两腿根望去,只见他的两腿根,真耷拉着一根和人类一样的生殖器。这一极不雅观的情形,让许多妇女羞红了脸,她们正要去骂那个与野人打招呼的人。没想到这时,野人突然张开嘴,“哇”地一声长啸,把所有人吓得没命地逃。
逃了好一会儿,才发现野人并没有追上来。但是他们都不敢走回去了,远远地看着野人扭动着身子,嘴里喊着他们听不懂的“叽叽哇哇”的话。那声音难听极了。
可是,尽管,被邻县人当做野人抓回来的张德旺,竭力呼喊着什么,试图证明自己也是人,就是许多年以前第一个发现野人的人。然而,此时的张德旺,已经有许多年与外界失去了语言交流,他的语言功能退化了,再加上隔着大山的两个县方言不一样,就算从“叽叽哇哇”的吼叫中偶尔冒出一个词汇,邻县人也难以听出其中的含义。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张德旺喊着喊着,眼泪就像瀑布般地泻下来。
“野人哭啦!野人哭啦!”
“野人也会哭呢,野人跟我们一样,哭得可伤心啦!”
那些翻来覆去看他的人,你推我搡,又往前挤,想看看野人哭的样子,但是又害怕野人突然挣脱绳子追上来,结果闹哄哄的,差一点打起架来,直到从他们的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铁笼子抬了过来。喧闹的人群才肃静了。
那铁笼子,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许多年以前大队熊场里用来关熊的。那时候,人们把熊关在笼子里,隔几天提取一次熊胆。现在这个笼子,已经抬到了他们的跟前,接着又抬到了野人的跟前。那野人一看见铁笼子,又拼命地挣扎起来,“叽叽哇哇”地吼叫着。可是,有几个胆大的人突然扑上去,狠狠地抓住了他杂乱的头发和乱踢乱蹬的脚,将他拖进了笼子里。
“哐当”一声,铁笼被一把大锁锁上了。
就这样,张德旺简直傻了眼,他被那些邻县人当做真正的野人关起来了。
我不是野人!我不是野人!放我出去!……
张德旺张着嘴,却喊不出这一句话,那些曾经属于他的词汇,都背叛了他。张德旺愤怒地用那只剩下来的手(另一只手因为被蛇咬伤麻痹了),使劲地摇晃着铁栅栏……
他嚎叫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