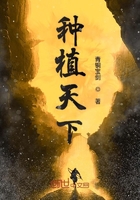那时候,年月不太平,孩子他爹白天要去干活,晚上还要接受批斗。那时候还没有电灯,我手拿煤油灯上楼,只看得见很小的一圈地方,风吹着灯火,忽明忽暗,一切都在灯光中幻变,像水底的树影。孩子们都出去了,每晚回来都要问我他们的爹怎么跪在台上。他们是不懂事的孩子,老大当时十多岁了,老三也四岁多,他们听说父亲是“地主走狗”,也跟着村里的孩子向他们的爹扔砖头。那时候我怀孕已经有五个月,我怕批斗的场面吓着腹中的胎儿,就偷偷地呆在家中——按规定,村里所有人都是要到大会堂里去听汇报、听指示、看批斗的。
我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扶着墙,慢慢地往上走。屋子里很静,静得仿佛吴村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不免让我产生了一丝恐惧。这幢老屋还是孩子他爹的曾祖父留下来的,结构复杂,潮湿腐朽,冥冥中能闻到一股阴气。仿佛这是来自地狱的气息。楼梯虽然不陡,但由于日深月久,加上潮湿和不通风,造成榫子松动、吱嘎作响,有几处不小心还会陷脚进去。本来,我说什么也不愿意睡在楼上,但孩子们大了,同住楼下那间房已不方便,再说,孩子们害怕楼上的棺材,怕得叫他们上楼拿一件什么东西,非得用很大的力跺楼板、喊叫,给自己壮胆,等到下楼的时候,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往楼下蹿,跌得头破血流。所以我和孩子他爹就将我们的床搬到了楼上。
听孩子他爹说,那棺材并没装过死人,是孩子他爹的爹的爹的,他爹的爹在我还没过门的时候年纪已大,有一次在河边洗澡,洪水滚滚而来,因为耳背没有听到,就被洪水卷走了。村里人沿河找了三天,连他的衣服都没有找到,以为他还活着,还会回来,就一直不敢将他的棺材挪用,所以他的棺材就一直留了下来。尽管这样,每回上楼,我还是感到害怕。
有一回,我终于忍无可忍了,那种担心棺材里会爬出孩子他爹的爹的爹的念头就像蛇一样缠绕着我,使我的神经近乎错乱,我歇斯底里,用离婚来威逼孩子他爹把他祖父的那口棺材劈掉。但孩子他爹这样骂我:“劈掉?你烧踝子骨啦?把这么好的一口棺木劈掉你他妈的想长生不老啦?你死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装你!”我已不记得我用什么话回击的他,只记得他平生第三次打了我,把我按在棺材板上,仿佛真的要把我推到里面去。到这时,我才突然清醒,有一天,我们都是要死的,死亡离我们很近,近得就隔一层棺材板这么近。所以后来,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它,想象自己两脚笔挺地躺在棺材里。
这时候,我一步一步总算走到了楼梯的半腰,好像是刚刚意识到似的,我那只扶着墙的手感到冰凉,墙好像是湿的,但我并没有往深处想,所以等我走到楼梯的尽头时,出于让自己适应一下楼上的环境——因为光线所及的空间突然增大,光线就像血滴到水里去一样散开了——我就利用刚才扶着墙的那只手去遮光,这时……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的手上全是血!再一看,只见整堵墙就像漏水的堤坝一样在流血!有几处血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我吓得半死,我简直瘫了,连自己有没有叫喊都不知道,就从楼梯上咚咚咚地滚下来了……
直到很晚的时候,孩子他爹从大会堂回来,才发现我晕死在楼梯上,幸好没酿成火灾,孩子也没有流产,但我的胆好像吓破了,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
那时候,座落在村下首的大会堂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那时候大会堂还非常新,里外都刷了白灰,不像现在,被人包去养了猪,臭哄哄的。那时候,也就是现在供种猪交配的地方,搭有一个很高的台,没有电灯就用那种点着以后会把煤油变成蒸气发出白色亮光的汽灯,左右两盏,亮得低着头认罪、胸前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像跪在天上。
我已经记不清每次批斗前大队干部,有时候也来公社干部,向我们宣读的“思想”啊“指示”啊,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用皮鞭抽我的丈夫,用拳头揍他的脸,要他认罪……当然,孩子他爹的罪是很轻的,不过是在非常年月贪几斤毛芋,帮地主家藏了家谱,但皮鞭和拳头是无情的,它们抽打在我丈夫的身上,但疼痛却在我的身上蔓延……啊,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昨天:绿军装,红袖套,会扩音的喇叭,反复无常的口号……
几个月后,就在一个一如既往的晚上,地主夫妇被村里人绑在了门板上,他们赤身裸体,肌肤被烧红的烙铁烫得又红又黑,这场面让我实在难受,就站起来想走,这时候,我没想到我迟迟不来的分娩突然像一场暴风雨一样来到了,开始那几下子,我靠在墙角,我还忍得住,但我终于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剧痛击倒在了地上,我哭了起来……
人们七手八脚,企图把我抬到家里去,但是来不及了,我下腹的血水已经像几个月前我在老屋墙上看见的血水一样往外涌,我能做的只能是拼命地张开我的双腿,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一团热辣辣的东西,它奋力地挣扎着,拼命地往外挤,仿佛要把我撕成两半……我听见有人在喊:“快去烧热水”“要生了,要生了”“男人别过来,不要过来”“露出一个头了”“快,快去拿一床棉被来,还要一些布,一些布”等等……在这之前,我已生产过三个孩子,老大是在土改的时候生的,老二是在炼钢铁的时候生的,老三是在生产队里剥花生籽的时候生的,所以我听到这些忙乱的声音,就知道我和孩子他爹的第四个骨肉就要在人声嘈杂的大会堂里诞生了,冥冥中,我竟看见自己自豪地笑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谁也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社里的干部就在这时候突然从门外冲了进来,他们听见批斗台上凄厉的嚎叫,以为阶级敌人企图撒泼、反抗,就随手举起步枪放了两枪,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我仍能回忆起我腹中的胎儿或者说是我的下腹猛烈地收缩了一下,我在惊吓和剧痛中晕死过去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胎儿并没有顺利生产,它又回去了。孩子他爹眼泪汪汪,为我从邻村请来了一位年纪挺大的接生婆(我们村里没有接生婆)。她听了我的肚子,对我说:“孩子,你别紧张,胎儿还活着。”为了安慰我,她还笑了笑。那真是一个异常慈祥的老太婆:干净的衣裳,瘦小的身子,满脸皱纹,眼皮浮肿,头上戴着发髻,爱抽旱烟……
她在我家等了三天,但婴儿还是迟迟不肯降临。她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我烧香、祈福,求菩萨保佑。并用一种自称“神油”的东西(也就是她烟杆里的“烟油”),涂在我胀鼓鼓的肚皮上,为我催生。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腹中的胎儿还是迟迟不肯降临……秋去冬来,风儿吹来了山顶上的落叶,纷纷飘过屋顶,墙缝里的蝙蝠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致使泥灰掉在我的头上,灶膛里一片黑,炉火早已熄灭,天空中布满了沉重的乌云,像一团团焦灼的愁绪......老太婆开始变得神神叨叨起来,她相信我是中了邪,触犯了天律,她指着屋顶越来越暗的天空说:“孩子,我帮不了你,看来一切都得听天由命,孩子。”说完,她就收拾工具,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时,大会堂里的阶级斗争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接生婆一走,家里又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的孕期已经远远超过半个月。我虽然万分担心,但由于他在我的腹中很安静,就慢慢习惯了,或者说,我已经忘记我是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了。但与此同时,我的营养又开始不良了。那时候根本吃不到我想吃的东西,譬如橘子、大豆、海带。我的牙齿几乎在一夜间掉光了。
有一天,我又一步一步艰难地上楼,我虽然害怕一个人在家,但我只想早一点躺在床上,因为我饿得太快,头晕眼花——但我忘不了五个月前,别人说我是“看花了眼”的一幕——我的手根本不敢扶墙,我的眼睛也不敢盯着灯火看,我小小心心,唯恐又出乱子。可就在这时,我仿佛听见头顶有什么东西飞过,我虽然吓得抖了一下,但继续向楼上走去。我以为,刚才从头顶飞过的肯定是蝙蝠的声音。可就在我迈进楼房的一瞬,我分明踩中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我吓得退了一下……原来是一只谁家的黑猫!
我举着灯继续向阁楼深处走去,经过这一吓,我感到更虚困了,我非常渴望躺在床上,于是我将灯放在柜子上,掀开棉被,可就在这时……这时从棉被里突然蹿出了两只身子比狗还大的猫!也是黑的!我又怕又恼,拿起枕头就向它们扔去,可是……天哪!……我看见整个阁楼上呆满了猫!
我不禁害怕起来,我的心都要蹦出胸膛了,我昏昏沉沉,两腿发软,感觉自己就像坠入了噩梦的深渊: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它们已经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无声无息,眼珠犹如萤火,胡须闪闪发亮!……我害怕它们向我扑来,只好向楼梯口退去,我对自己说:不用怕,不用怕,没事的,没事的,说不定又是“看花了眼”……可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身后站立着更多的猫!
我不寒而栗,心又一次悬起,我已经完全被这些来历不明的猫包围了!……它们开始一只接一只地向我扑来,我四处闪避,一次又一次稳住脚跟,但我的衣服很快被它们撕破了,鲜血直流……这时,我终于摸到了一根木棍,不顾一切地向它们砸去,只见满地的黑猫就像巨石落下的波澜一样荡开,荡开又聚拢……它们开始同时向我攻击……我简直快要被这些黑猫逼疯了!我多么害怕!多么恐惧!我发疯般地将手中的棍子,就像闪电似的在空中飞舞!我尖叫着,声音仿佛从黑色的发尖里迸出……但它们并没有退去,相反,它们的攻击越来越凶残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终于感到筋疲力竭,腹中好像在翻江倒海,皮肉仿佛石榴一样裂开……我挣扎着,抽搦着,忍着针扎火燎、撕心裂肺的疼痛……但我再也坚持不住,我感到我就要死了,我感到一切都坍塌了,熔化了,沸腾了,成了游动的泡沫……红色的泡沫……时间滚滚涌来,黑猫像鱼儿在水里跳跃,我感到一切都崩溃了,颠倒了,破碎了,流出脓血,成了泡沫……红色的泡沫……我竭尽全力呼吸,直至我抓住了汹涌波涛中的棺材,我终于倒在了它的怀里,拼命地叫喊着:“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孩子他爹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第四个儿子——阿生——已经安全地在他祖宗留下来的棺材里诞生了。仿佛一切都已经结束并将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