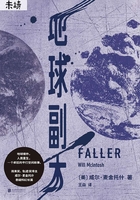大
部队进城十分壮观。
小菲惊奇地发现这座小城蝇营狗苟的乌合之众一夜间洗心革面了。破烂的街面铺板也漆了一新,贴着红纸绿纸的标语。汉子娘们儿用于骂大街的嘴巴现在用来欢呼口号。举彩色三角旗的手,或许正是掏腰包、拍花子、拾菜帮、打卦算命、撒狗血、卖假药的手们。怎么也会有正气昂然的样子?小菲心里先是不肯信服,慢慢变得有些感动。女学生、男学生们穿得整齐干净一派深蓝,几百面腰鼓打出一个动作、一个点子,小城散漫流气惯了,这回可真的改了坏习性。革命就是厉害。
“田苏菲!”
小菲扭头一看,没找到叫她的人,但已认出那嗓音:孙小妹。扭头时她走错了操步,鞋给后面的人踩下来了。她跳一只脚到队伍边上去拔鞋。刚直起身,一只手拍在她肩上。腰鼓队散出个豁口,让一个年轻女兵和她的旧日同窗抱成一团。
“你妈后来找到我家来了……”
“真(蒸)的呀!”
“煮的!”
这时政治部过来了。小伍大老远就张开双手冲过来。三个女孩眨眼抱成一个人。
“我们学校就来了你一个?”小伍问孙小妹。
“还学校呢?人家都毕业了!这是纺织学院的学生!”
小伍说:“不行,回头再谈吧,不能掉队!”她见小菲还想继续掉队,厉声喊道,“小菲!跟上了!”
小菲紧跑几步,上半身还扭向孙小妹。
“话别没个完。”小伍小声说,“知道她政治面貌吗?这个城市的三青团员多得很,尤其是大学生!”
小伍才十九岁,政治上进步飞快,一礼拜不见小菲对她就得调整一次认识。小菲常要接受她教育:
“小菲,要有点理想,你以为好好演戏就行了?”
“小菲,据说你入团申请只写了三行字。你平时多嘴多舌,废话连篇,让你说正经话,你就三行字?”
“小菲,眼睛别尽往文工团的男演员身上看,找对象要找军事干部、政治干部。男演员除了会演戏还会什么呀?”
……
有时小菲不服,回嘴说:“那军事干部除了会打仗,还会干什么?不打仗了,他们还能干什么?”
这种时候不多,但碰上这种时候小伍颇有些吃惊,觉得什么时候起她的权威性在小菲那里动摇起来了。小菲狂是因为外面传说都旅长看上她了?她对小菲暗暗敲打:别膨胀,都旅长常常跟文工团的女演员搞不清爽,捧完这个女主角捧那个。人家是女主角,你不过是顶替顶替。小伍说去攀都旅长那棵大树是不识时务,部队一进城,什么大美人、女才子没有?轮上你田苏菲做梦?
这天晚上文工团在城里的大戏院演出。这是进城第二天,票都是送给城里头面人物的。小菲早早接到通知,让她演喜儿。她以为听错了,跑去问鲍团长是不是A角、B角的喜儿一块儿病了。
团长说:“问什么问,走你的场子去吧!”
乐队也不拿小菲当回事,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找了板胡和笛子,来陪她走场。
其他人都说:“小菲还用走场?小菲是万金油,往哪儿抹都灵。”
到了化妆时间,团长跑步通知所有人:“还按原班演员上。小菲还是演群众!”
这可太意外了。A角临时顶替了小菲。她倒美滋滋的,因为她头一次作为一线演员、第一选择,而原来第一选择做了她的顶替。据说那天晚上都旅长点名让小菲演喜儿,但他临时有重大事情不能来看戏,文工团赶紧把A角和小菲对换回来。
其实都旅长已经把小菲变成他棋盘上的棋子,想怎样走她就怎样走她。他在那次打土围子与小菲“邂逅”之后,就已定局在握。他早就知道田苏菲的名字,不过他识的字里没有“菲”,因此他就在练字的糙纸上写“飞”、“飞”、“小飞”。警卫员们知道就知道,都旅长明人不做暗事,他老光棍一条,不想女人想什么?都旅长觉得小菲特别对他的胃口,白白净净、眉清目秀,三分憨态、七分俏皮,终生有这么个小花旦在身边云绕,武夫亏久的阴柔都给滋补上了。都旅长还看重小菲一点特质,就是真。这一点,连学问很大的欧阳萸都错过了。
都旅长安插的探子是文工团的舞台美术组长,叫邹三农。邹三农也是江西老俵,跟都旅长同乡。邹三农把暗地搞来的有关田苏菲的情报都汇报给了都旅长:家庭成分该算是城市平民,教育程度是女子教会学校高中水平。邹三农一心助旅长的兴,只讲好话不讲坏话,其实小菲只读了一个月高一。那个年月高中女学生相当几十年后的女博士,尤其在一个乞孩出身的老革命眼里。
进城之后,邹三农把小菲妈的住址也弄到了,都旅长叫警卫员给小菲妈带三盒烘糕、一封请帖,请她三天后到大戏院看小菲演《刘胡兰》。
小菲妈这时还没有改变对共产党的眼光。什么解放军?不就是土匪吗?她在南京住那么多年,把歹人一一排列下来便是:鬼子、汉奸、土匪、共匪、黑帮……她把烘糕好好地锁进了衣柜,把请柬撕了撕,备下做引炉子用。女儿是彻底白养了。十六年含辛茹苦,织毛衣、絮棉袄,抽断多少根扫帚苗子,结果养出个匪来。
伍老板娘跑来通风报信,说解放军可是不得了,把城里的婊子全收拾了,带到哪里治病的治病,学本事的学本事;解放军一进城就把东孝口的恶霸捉了,这些天到处捉恶霸。然后说到她家善贞:善贞嫁了个解放军大官,是个团长。伍老板娘走在巷子里人都高一截,有时指着巷口停的黄包车跟邻居说:“善贞接我们去吃饭,她忙!”
这些小菲一概不知道。她只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地推迟回家看母亲的日子,她怕死这日子了。跟母亲怎么解释半夜偷偷出走的事?为那件果绿色带黑绒球的毛衣就狠下心把妈丢了投奔革命?要是妈冷一张脸说:“哟,功臣回来啦?我们家庙小,装不下你哟!”她小菲该说什么?假如母亲说:“这位解放军女同志找谁呀?恐怕认错门了吧?”她又该如何往下接茬子?母亲有权力、有理由这样对待她。她最怕的一点是母亲什么话没有,劈头盖脸就是扫帚苗子。她肯定对这种疼痛受不惯了,扭头就会往门外逃。小菲一想到自己人五人六一身解放军军装给妈的扫帚苗子追得满巷子跑,就把回家日子推得无期了。
她哪知道母亲这会儿正在街上看解放军扫大马路,通臭下水道。母亲是直觉特灵的人,她一看就觉得这些兵一身正气。再说她最嫉恶如仇的东西就是妓院,一听共产党封了所有妓院,除掉了把男人引坏把女人弄脏的地方,至少得念共产党这一点功德。在城里兜一圈,她回到家就去柴篓子里掏,把那撕烂的请柬又扒拉出来,用饭粒子粘上,打算晚上上大戏院。她不知给她送请柬的士兵说的首长是什么官,他特地买点心特意送请柬恐怕和苏菲有点不一般的意思。“首长”有没有“团长”大?母亲们在攀比女儿时总是浅薄、虚荣,何况小菲妈生性那么要强。
小菲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她这晚上演刘胡兰。她还知道自己要演出欧阳萸的“含蓄”。欧阳萸在进城后影子都没了,小菲想到小伍说的满城大美人女才子就慌。她一面化妆一面打量自己,不难看吧?母亲一直骄傲她的鼻子,总说鼻梁是长相贵贱的关键,不算大美人,还是讨人喜的,多少分?打八十五?八十分?欧阳干事难道非得爱个一百分的?
进城之后文工团从城里京剧班子弄来些真正的化妆品,但文工团的人还用不惯,黑油彩描眼圈描成两个黑炭球。他们宁愿用自己的代用品。小菲把一根木签子在煤油灯火烛上烧一下,用草纸捻一捻,就是一支眉笔,描上两三笔,再去烧。她万万没想到母亲这时把最后一点家当披挂上了:身上是黑绒线的长外套,罩住里面的棉旗袍。虽然黑绒线是各色毛线染的,但在戏院的灯光里看,黑得很均匀、很笃定。她把两个翡翠耳坠子也戴上了,配上一个假翡翠镯,看上去贵而不华。她进场时还早,没有多少人,收票的一看她那破碎又重合的请柬说:“你是从戏院外面捡的吧?”
小菲妈笑笑说:“你看我像不像在街上捡东西的人?”她想起送烘糕的首长姓都。这个姓跟别的姓弄不混。她告诉守门的人说是一位都首长给她送的请柬,让家里的小捣蛋给撕坏了。
小菲妈坐下十多分钟,观众入场了。她的座位在第三排。人们把前后左右都坐了,独独空着第三排中间一行椅子。头一遍铃响之后,几个穿军装、穿长衫马褂的人走到第三排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坐到小菲妈左边,伸手过来说:“田妈妈你好,我是都汉。”
小菲妈打量他。都汉就是都首长。成了田妈妈的小菲妈不知他伸的手是干吗的,欠起身来,笑一笑,鞠鞠躬。刚要坐下,都汉首长把她右手握住了。田妈妈想这是什么礼节?手够厚的,倒是细皮嫩肉。都汉首长人很和气,一笑就腆肚子仰脖子,笑得四座皆惊。
“小飞你教养得好!”都汉首长跟别人谈过几句话,又转回来关照田妈妈。
大幕拉开了,田妈妈听惯京剧越剧黄梅调,心想这是马戏乐曲嘛。过了几分钟她才认出女儿,一认出就不知她唱的是什么戏文了,眼泪止不住地淌。
“田妈妈看看我们小飞长大了是吧?”
田妈妈点点头,觉得苏菲高了半个头,一双大脚片子走路扇风,解放军没亏待她,伙食好营养好,看她一瞪眼一牛吼全是气力。她原来是要把苏菲养得细细气气,现在一看,浑身蛮劲。不过硬扎壮实比什么都强,她就将就着看吧。
这天小菲演得轻松自如,假如她知道第三排中间的观众是两年前成天朝她舞扫帚苗子的母亲,肯定挺不起胸撒不开手脚的。她的笑和哭全是真的,不来半点技巧,什么含蓄?含蓄还不憋死她?
幕间休息十分钟,她想起晚饭还热在炭火边上,赶快跑去吃。鲍团长进来,说她唱得有点冒调。小菲满口米粉肉,使劲点头。不过大家都很感动,说小菲是真正的新时代演员,演出来新中国的形象。团长又告诉小菲,市里省里的剧团都来看今晚的戏了。他说着说着就不说了,看一眼吃得喷香的小菲,加一句:“算了,演完再告诉你吧!”
小菲说:“什么事?”
“等戏演完再说。”
小菲说:“你说一半我哪儿还有心思演呀?上台忘词算团长的。”
鲍团长眼睛不看她,眼光挪来挪去,没地方停歇。
“肯定是坏事!”小菲说。
“不是!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你早讲出来了!”
“是好事!”
“才不信。”
“真的。都旅长跟我正式谈话,说要娶你。”
小菲先一愣,然后嘿嘿笑了。团长想,她真把它当好事呢!
“我不让他娶。”小菲说。
“你别胡扯啊,旅长看上你!不是团长、营长。”
小菲突然问:“欧阳干事是什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