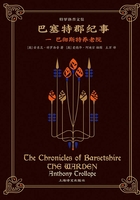包爷像是压根儿没理会他们的举动,也没听他们说话,独自念叨:“兄弟为了活命,多有得罪,莫怪莫怪。”说着向那插满了箭的东胡兵快步走去。说实话,对于眼前这惊异所见,我还是心存畏惧的,生怕做了不合章法的事遭到什么报应。我说不好自己是出于好奇,还是担心包爷作出什么太过出格的举动来,起身随着包爷走了过去。包爷在那东胡兵的背后停了下来,单腿蹲跪在地上,歪着头在东胡兵后背上看着,像是在仔细比较什么。他摆手招呼我过去,指着其中两支箭问我道:“这俩哪支扎得浅些?”他大致扫量了一圈,指着射进那人皮肉里相对最浅的两支箭。我没搞懂包爷的意思,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便应他:“差不多吧。”包爷又在那两支箭上面仔细比量了一番,像是确定了深浅,便挽起袖子迅速伸手抓在一支箭杆上,明显见他手臂一用大力,就飞速将那支箭拔了出来。几乎就在同一秒,阳光下一道血从那箭伤处喷飞而出,我下意识地向后躲了去。再一看,根本没有躲避的包爷脸上,一大道红色液体如血疤般横亘了他整张脸。包爷没有丝毫畏惧之色,甚至就好像根本没感觉到喷到脸上的血。他站起身来,拿起箭便回到了那画了一圈太阳的地方。
很快,我们再一次上路。包爷取的那支箭也派上了用场。包爷把那箭头按在地面上,撕下半片袖子缠在右手上,紧紧握着箭尾,按照刚刚确定好的方向与太阳的夹角,边往前行进边画着直线。原来他是怕我们因为太阳不断移动的原因,掌握不住前行的角度而走偏,用这支箭确定我们走的一直是直线。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绝望”这两个字离我们的意志也越来越近。可能是因为顶着太阳前进的缘故,再加上长时间饥渴,我鼻子前似乎开始萦绕着一股异常的气息,那股气息不是任何一种明确的气味,而是一种感觉,它从鼻孔随呼吸进到肺部,再弥散到各个器官,让我浑身上下都生发出一股无力感,强烈的无力感。我能够猜到,那是死亡的气息,距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气息。
“几点了?”
这是前进开始到现在的第一句话,是“花瓶”,她有气无力地边走边说着。
我正边走边翻电子表看时间,包爷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大约还有一个半小时日落。”
其他人并没有应话,稍过了两秒,“花瓶”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带着明显的火药味:“问你几点呢!又没问你日落。”
包爷没有再应话,大家依然无声无息地随包爷向前走去。“花瓶”的声音越发地有气无力,步子看上去也有些重,她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似乎有些耐受不住了。我侧过脸看见她焦灼烦躁的表情,意识到我在看她,她硬是在脸上拉起一道缺乏水分的微笑。那微笑,在日渐西沉的阳光下显得有些苍凉,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些酸溜溜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愧疚吧,毕竟她是追着我才跑来的。也不只是“花瓶”,欧阳他们三个从根本上说也都是因为我才过来的,现在这么糟糕的状况,万一我们真活不成,我岂不是罪大恶极了!
我知道,万一和一万,差别并不大。
“我要喝水。”这几个字像是呓语般在耳边响起,我本以为是自己热得渴得出现了幻觉,或者是不受自己控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理诉求。我用力晃了两下脑袋,可那声音又响了起来,只是更加有气无力,这次我听清了,是“花瓶”。但其他几人都没有理会,依然往前走着自己的。似乎一切节奏都变慢了,就连声音的传播都像是需要通过另一种介质才能传递进大家的耳朵,郑纲稍有沙哑地说:“不能喝。”我以为郑纲这小子气“花瓶”之前嫌他脏没喝水而说出这样的话,刚要替她辩解,郑纲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那口水,是救命稻草。”
我们依然往前走着,我上前扶着“花瓶”,“花瓶”的脸色已经白得有些发青,嘴唇已经裂开一道道口子,泛着层层白皮。
见她这糟糕的状态,我似乎被传染了,竟然觉得双腿有些无力。“花瓶”搭着我的肩膀,微微闭着眼睛停了下来,像是在养精蓄锐,舌头伸到唇边润着,舌苔上已经完全没有了正常的血色,而是有些蜡黄。见一个女孩这么筋疲力尽,我心里面多少有些难受。男人都是这副德行,见女生柔弱地出现在眼前,心里总会生出英雄主义来。我扶着“花瓶”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听我这么一说,“花瓶”冲我疲倦地笑了笑,正要弯身坐下来,一声难听的吼叫传了过来:“起来!”
这声大吼把我们俩顿时吓得精神了起来,声音刚落地的包爷快步走了过来,那样子简直像是一匹狼,一匹在绝境中变得惊恐而暴戾的狼。我和“花瓶”被他惊得还没直起身子,包爷就已经走近,把我们俩硬是拉了起来,大声喊着:“起来!起来!”随后他又解释说,“不能坐!坐下就难起来了!”
“花瓶”嘶哑地低声抱怨着说:“不渴死,也得累死。地狱,简直就是地狱!”
刚转过身迈开步子的包爷回头横了她一眼,坏笑着丢给她一句:“谁请你来的?拖后腿还抱怨。”包爷话里并不是抱怨,反倒像是在扯皮。他应该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几乎快要丧失生存斗志的我们精神起来,还有娱乐的情况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忘却已然没有了生存的必备条件。“花瓶”什么也没有再说,但我用余光留意到,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之后低下头,拉着我的胳膊往前走了去。
时间一秒秒流失,硕大的太阳离西山越发迫近,沙沙的脚步声似乎正在丈量着我们距离死神的长度。
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情景可以用来转移注意力,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无力而疲惫的躁动。
走着走着,“花瓶”的身子突然矮了下去。我往前迈出了半步后才意识到这个情况,就好像我的反射弧已经变成了正常情况下的两倍长。郑纲飞速跑过来,把水拧开,掰着“花瓶”的嘴巴往里面灌去,“花瓶”缓慢地动了几下喉结后,似乎恢复了一点精神。欧阳疲倦地看着郑纲,询问般建议:“歇会儿吧?”郑纲一边弯身蹲下来,一边说:“歇了就难活下去了。”说完拉过“花瓶”的胳膊就要背起她。
原则上说,这几个人都是陪我来以身犯险的,“花瓶”这个累赘也是我招惹来的,自然不能让郑纲背。我背起了“花瓶”,几个人继续开始漫长的征程。
又走上一会儿,“花瓶”无力地说:“让我下来吧,能走动了。”听她说话的力气,我就知道她在逞强,我也硬撑着继续朝前走着。
她没有再说话,把脸蛋儿贴在我露在外面的脖颈上,随后,我感觉到凉丝丝的东西从后脖颈慢慢滑了下来,一直滑到了胸口。“花瓶”这个疯疯癫癫的丫头竟然哭了,眼泪贴着皮肤,被蒸发掉,燥热得如红炭一般的皮肤感觉得如此明显。
前面是一个坡度很缓的山包,郑纲和包爷应该是急于去山包上寻找水源,步子变得越来越快。欧阳一再地问我用不用帮忙,一直保持着和我差不多的前进速度。
那个山包后面的状态几乎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希望。我边朝前走着边挑起眼皮看着已经爬到顶端的郑纲和包爷,他们正四下张望着。终于,郑纲突然兴奋得大吼了一嗓子,包爷兴奋地喊道:“有水啦!有水啦!我们活啦!”
“花瓶”似乎也被这救命的喜讯刺激着,执意要下来自己走。欧阳返回来,和我一起架着“花瓶”向前走去。身子刚一移动到山包上方,就明显感觉到一股子水汽迎面而来,潮湿而清凉。终于,看见了救命的水源,我能明明确确地感觉我脸上的笑是由内而外完全超出我能控制范围的,那种笑,恐怕只有面临死亡并骤然获得生的希望时才会有的。
“你笑得真好看。”
我歪过头,看着刚刚突然冒出这句话的“花瓶”,她笑得很淡,似乎突然间蜕变了,没有往常嘻嘻哈哈的样子,变得柔弱而细致。
欧阳催着我们快走。离我们几百米处,大片大片郁郁葱葱的蒿草间,那条银白色的溪正在阳光下闪着光。包爷和郑纲站在水草和山地的交界处,转过身子来催促着我们。“花瓶”虽然已经累得软绵绵的,但还是逞强着,一脸的不忿,走到近前时,她毫不领情地说:“你们先走呗,又没让你们等,催什么催。”
包爷和郑纲俩人对视一眼,淡淡地笑了笑。包爷有意吓唬她似的,念叨着说:“把你喂毒蛇,不知好歹的小丫头。”说着,包爷弯着身子在身前的蒿草上左右打着,打开一片后才往前走上几步,我们便也自然地跟在包爷的身后。包爷像是被这浓郁的水汽给滋润得有点兴奋,他边打还边说:“毒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受到惊吓后,会立即转移到别处。这一招就是那个成语——打草惊蛇最原始的意思。”几个人兴奋地朝着那救命的小溪走去。我从没见过这样美丽的溪水。
周遭的水汽很重,我甚至能感觉到脸上干瘪的毛孔正在大肆吮吸着空气中的水汽,疯狂地补水。包爷虽然要帮我们“打草”,但他在前面走得还是很快,草的尽头和那溪水之间还有一小块裸地。接下来的一刹那,我不得不对包爷刮目相看,距离那裸地还有四五米远的时候,只见包爷稍往下微蹲身子,如一头豹子般嗖地一下蹿到了裸地上,矫捷得远远超乎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