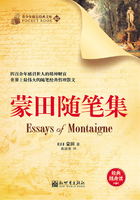汤姆是文明世界的反叛者,哈克则是乡野间长大的自然人,他们不找圣杯,也不寻宝藏;阳光之外,河水之外,两岸原野芳香之外,他们别无所求。
“激起梦想的月亮河啊,同时你也令人心碎。
不论你到哪里,我都跟随着你。
两个漂流者一起去看世界,那儿有许多世界奇景可以欣赏,我们在河滨外等着,寻找同样的彩虹的尽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歌词,一段令人心醉情迷的歌词,它表达的欲望,如一池的云影,一天的涛声,一舟的明月,一袭盈袖的暗香。
这种欲望,令我们有勇气和信心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痛苦中追逐欢乐,在贫瘠中品尝丰收,在屈辱中捍卫荣誉。
是的,无论在广博的密西西比河上,还是在狭小的欲望号街车里;无论在娓娓表述的时刻,还是在静静倾听的瞬间,我们拥有的都是同一种体验:赤足而去,留一双鞋在有情的人间。
杯中的酒已经干了,莲花也在火光中凋零。
待换上一盏新烛,另一支歌开始温柔地舔着我的耳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家在哪里?
家,太远了;或者,万里之外,家根本就不存在?
远方只有一棵倔强的橄榄树,谁能说出橄榄果的滋味,谁能走出橄榄叶的绿阴?
只记得树下有人轻轻对我说过一句:来生有约。
而此际,是不是相约的来生呢?
歌声像闪电一样打在我心灵的坚冰上,我分明听见了咔咔嚓嚓的破冰声音,就在这破冰声中,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唱歌的却是一位年轻得让我吃惊的女孩,黑白分明清澈似水的眸子里,哪有一点一滴我要寻觅的沧桑?
每一次的放弃也意味着容纳,每一次的回忆也意味着忘却。
时光总是在门槛上跌倒,跌得鼻青脸肿;我总是走到穷途才回首,回首时是否一无所有?
我想问,你是不是那“最是一低头的温柔,像是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的女孩?
你的歌是虎符的一半,而我的心是虎符的另一半,两半契合的时候,闸门开了,潮水汹涌而出。
追忆似水年华,原来我曾是一尊面目狰狞的雕像,怀着一颗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希望穿过海上的岩礁,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
然而,海上起风了,波涛澎湃中,船沉没了。
我沉入黑暗肆虐的海底,无寒无暑地过了一千余年。
当你的歌声像磁石一样把我从幽暗之中捕捞出来重见光明的时候,我的身上已布满海水任意琢磨而成的涡孔,而我面容的轮廓,已被冲洗得安详且柔和。
于是,我们的初识便是我们的重逢,我们的重逢便是我们的初识,千古又千古,该流转的依然在流转,不能流转的还站在那里,那就是橄榄树的根。
老实说,我是个对音乐的感觉很迟钝的人。
在拥挤的车厢里,我的精力往往集中在拉住昂环的那只手上,那只手保持着我身体的平衡。
无意中,窗外的风景也成了一片空白。
我只记得自己在行走,忘记风景也在行走。
我为自己的坚强而自豪,这种坚强足以抵御住任何一支荆棘的侵入。
殊不知,我却在最坚强的时候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一首名叫《橄榄树》的老歌。
烛光模糊了,像一团云霞一样弥漫着。
我又想起了那个叫三毛的女子,我又想起了那两个笑声飘荡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少年,他们都在欲望中燃烧,而我幸存下来,伤痕累累。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掌声中,你如蝴蝶般飘下舞台。
到了我问你从哪里来的时候了,我必须问,而你也无法拒绝,因为我们都是流浪者。
我们搭上的是最后一班街车,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走出灯光的包裹,走向寂静的角落。
潮落了,沙滩上留下那么多的贝壳,谁来拾呢?
整个地球都在旋转,地球就是一辆欲望号街车。
我们都没有带地图,只有那一纸无字的盟约。
窗外有一座亮着的灯塔,折射的灯光照亮了你的脸庞,也照亮了我忧郁的眸子,你走过来,对我说:每个受到伤害的人都能得到抚慰,每种欲望的背后都有一只飞动的青鸟。
这一刻,水近,天回,橄榄枝漂到我们的身边。
这一刻,花开,云飞,橄榄树在茂盛地生长。
这一刻,雪滑,冰融,流浪者与流浪者相遇。
那一夜,在遥远的东京,在异乡的客栈,从绍兴来的少年客,偶然瞥见了奉茶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
从此,这名唤作乾荣子的十五岁少女轻盈而白净的赤足,像一片幽香扑鼻的茶叶,溶解在这个中国人心中。
那一瞬间,意乱情迷的少年周作人朦胧地意识到,那是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那是一种纯朴率真的文化,那是一种活泼丰盈的生命,那是一种澄澈宁静的意境,那也正是祖国曾拥有过,却又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的东西。
若干年后,两鬓斑白、历尽沧桑的知堂老人依然动情地写道:“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赤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
我所嫌恶中国女子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脚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代殊不可多得……”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变态的部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却没有学习中国缠足的文明,所以日本女性保存了天足。
重读知堂文集的今天,缠足的陋习已成为记忆之外的记忆,然而女子的天足又被塞进一双双又短又窄又高的高跟鞋里。
大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总是一串串骄傲而艰难的步伐。
象征着现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时尚的高跟鞋,再次留给女性一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爱恨交织的尴尬。
步步生莲的梦想与“哒哒”的脚步声,与夜晚双脚麻木疼痛纠结成无法斩断的情结。
在男性一次次绅士风度十足地回首里,赤足的美丽对于穿高跟鞋的女子而言,陌生得像一双檀木制成的书签,寂寞地夹在一本盛唐时代的线装诗集里。
其实,真正的美丽源于自然,真正的优美得于天成,真正的高雅源于纯真。
哲学拒绝权威的枷锁,艺术拒绝金钱的包裹,生活拒绝物质的栅栏;同样,天生之足也有理由拒绝装饰它、约束它、囚禁它、折磨它的或精致、或华丽、或玲珑、或绚烂的鞋与袜。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千载而下,屈子兴之所至,赤足戏水的姿态,犹在眼前。
这是一种生命张扬的人才有的情致,这是一种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声音,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生存状态。
当云南边陲的一群傣家少女,穿着短短的筒裙,拎着小小的水桶,扭着细细的腰肢,赤着白白的天足,一溜烟穿行在小溪畔的石板路竹林间时,如画、如诗、如酒、如歌。
任何一个巴黎的时装大师看见了,恐怕也无法进入这赤足的氛围中吧?
为美丽而制造的美丽,就好像没有灵魂浇灌的音乐,没有香味萦绕的鲜花,没有露水滋润的绿叶。
而被财富奴隶的美丽,就好像古时候那位卖柑者筐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子。
好多女孩把自己当作丑小鸭,以为有一双昂贵的高跟鞋以后,才能变成天鹅,她们却没有反过来想想:自己原本就是天鹅,何须以高跟鞋作为标签来命名呢?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有设计师设计出了镶嵌满钻石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高跟鞋,谁有“福气”穿呢?)有个女孩说:“只有穿上高跟鞋,我和男朋友一样高时,我才有信心面对他和面对自己。
否则,我觉得,在自己的心中和在对方的心中我都少了几分美丽。”有这样想法的女孩绝不在少数,散步时走得气喘吁吁,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并美其名曰:为美丽受难。
然而,因受难而产生的美丽仅仅是一个苍白的外壳。
当一个男孩称赞你,“你的高跟鞋真漂亮”时,单纯的女孩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他是因物而爱人还是因人而爱物呢?
这双鞋穿在另一个人脚上,他会不会同样称赞呢?
当你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时,你就找到了发现自己的窗户:只有自己才是世间最美丽那一部分啊!
一双少女健美的天足,优美柔和的足弓、润泽的血脉、洁白的肤色、敏感的神经,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一件艺术品。
赤足之美,如池塘中亭亭的芙蓉,如竹林里悠悠的琴声,如陶壶内淡淡的茶香,如黄昏时柔柔的光晕。
赤足之美,在春则为鹅黄的柳芽,在夏则为润泽的梅子,在秋则为静谧的弯月,在冬则为轻盈的白雪。
赤足之美,却又在这一切比喻之上,连艺术大师罗丹也头痛地说:“塑像时,女性的赤足几乎令我无法复现万分之一的美丽。”因为每个青春女性的身体,都集中了山水的灵气、自然的精华、神灵的挚爱,而天足恰恰是长期被遮蔽的却又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一粒沙里见天堂,半瓣花上说人情”,知堂老人确实有颗慧心,有双慧眼,独辟蹊径地在一双赤足里找到了身体的神韵。
一向温文尔雅的他,之所以辞严色厉地反对裹脚,斥之为恶习之源、贬之为民族之耻,这与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审美体系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那位年仅十五岁便开始辛勤地操持家务,既天真可爱又善解人意的日本女孩,可曾想到自己那双在榻榻米上款款而行的赤足,居然成了那位惶惑而弱小的坐在几案边的少年一生珍藏的财富?
最美的东西往往被过分聪明的我们忽视、遗弃或者加工、雕琢,而加工、雕琢得面目全非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苦苦向往的却常常是美的反面。
手术刀下出现的双眼皮、嘴唇上如鲜血淋漓的口红、比皮肤还厚的脂粉,以及挂着沉重的耳环的耳垂,佩着金光灿灿的项链的脖子、戴着晶莹的玉镯的手腕,这一切都是时尚给“美女”一词所下的定义。
然而,“时髦”究竟是美丽的近义词还是美丽的反义词呢?
女性对高跟鞋的执著究竟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软弱呢?
对那些穿着高跟鞋艰苦地在人流里穿梭的女性,男性又该负多少责任呢?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了,于是,我们就像一只鲜艳的气球,在半空中为自己的美丽洋洋自得,却不知道自己占据的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空洞。
在这样一个包装泛滥的时代里,不管是穿高跟鞋的女性,还是不穿高跟鞋的男性,都该读读知堂老人的文章。
感谢冰清玉洁、宛如出水芙蓉的乾荣子姑娘,她留给知堂老人那代人的,绝不仅仅是一双“白如霜雪,不著鸦头袜”的天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