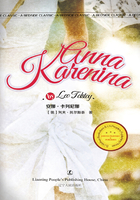初始——
南屏国,武德三年。
无风无云,天幕湛蓝,明丽的早春,街上的人们却个个紧锁双眉。南屏国的大旱从武德二年的夏末延续至今,马上就是播种时节,若还是滴雨不下,整个南屏就不知要饿死多少人。饥荒起,恐怕连南屏的社稷都会岌岌可危。
朝堂上,南屏王南宫峋在龙书案前焦躁地来回踱着步子,想要对着朝臣大发脾气,却又觉得没奈何。老天爷决定的事,凡人能有什么办法。底下的文武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有人提出祈雨,有人提出祭河,这些法子早就试过了,南屏王领着满朝大臣把有名的没名的神仙拜了个遍,可老天就是不买账。说来说去大臣们自己都厌恶自己提出的意见,有的老臣禁不住颤抖着胡须老泪纵横,南屏的子民啊,莫非上苍真的要降大难于南屏吗?太傅曲江白一言不发的站在大殿的一侧,原本润白的脸,如今已是苍白中透着枯黄,眼圈青紫,显然很久没休息过了。
“散朝。”南宫峋颓然的挥挥袍袖。
群臣们叹着气退出大殿。
刚出午朝门,只见一位家丁模样的男子慌慌忙忙地跑过来,边跑边喊:“老爷,老爷,赶紧回去,夫人要生了!”曲江白从同僚身边挤过,抓起那名男子就跑,连轿子都顾不得了。
刚跑到家门口,里面跑出来一个小丫鬟,曲江白一把抓住丫鬟的手,“采苓,夫人怎样?”
“恭喜老爷,母女平安,是个漂亮的小千金。”丫鬟采苓眼角眉梢喜气洋洋。
曲江白松了口气,大踏步的迈向门里。一丝凉意打在脸上,他抬头望去,凉意渐深,一道道银线越来越细密,一场透雨从天而降。“下雨了,终于下雨了!”曲江白望向天空的脸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全长乐都的百姓纷纷跑到街上,大笑着,哭泣着,狂欢着,感谢上苍降下的喜雨。
曲江白为床榻上虚弱的妻子理了理被汗水****的乱发,轻轻抱起刚出生的女儿。
“相公,为女儿取个名字吧。”
曲江白摸摸女儿的小脸百感交集,初为人父的喜悦混搭着旱情得缓的一丝蔚然,“叫秧歌,曲秧歌。”
……
我出生那天一场豪雨润透了南屏的土地,结束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大旱,为祈丰年足月,父亲便为我取名“秧歌”。流言总是如长了翅膀的鸟儿,扑棱棱的就漫天飞舞。尚在襁褓中的我,不知怎的,竟成了百姓口中上苍降下的吉兆,为南屏带来了那场解救万民的喜雨,俨然我就是南屏最受人们眷顾的女孩子了。连坊间三岁小儿都知道“曲家有女,名秧歌”。其实,一切与我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幼年时,父亲常抚着我的头,用他那清越的嗓音与我讲:“秧儿,你可知世上最动听的歌声来自哪里么?立夏分秧插田,盈塍接胧,以洒殽布地,农人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望见水中天,专心致志的并不多言。待到休息时便男女以歌相合,欢呼酣饮,歌声遍阡陌。那便是秧歌。”
我托腮静听,以为父亲口中的秧田就是人间极盛的景色。这时母亲就会淡淡浅笑,戏说父亲本就是一名山野老农,锄为妻,秧为子。父亲也总是故作有礼对着母亲深深一揖,“娘子,便是在下的糟糠之妻。”
别家女孩儿倚门而立手拂一枝春花,背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却在院子里跳着,背着“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想着父亲口中茂茂秧田,水中青天。那世家公子小姐口中的风雅,于我是如何也弄不懂了。
满月那天,父亲和母亲在自家院子里备下了一桌家宴,只于家人仆妇一道庆贺。彼时南屏刚从大灾中解脱,而身为太傅的父亲又素来清简,桌上不过几碟寻常小菜,一壶薄酒。谈笑间,家人来报:“启禀老爷,都中百姓聚在府门前要为小姐献贺礼。”
父亲大惊,携了母亲与我来至府门前,果真全城百姓都围在门口。
父亲在阶前对着百姓们深深施礼:“乡亲们,江白诚恐,代小女谢谢大家的一番心意。小女秧歌本就是平凡女孩,受了大家如此眷顾已是莫大的荣幸,又怎么能收大家的礼物呢。大灾刚过,又怎能因小女而使大家破费,这万万使不得的,乡亲们请回吧,乡亲们的心意在下和小女铭记在心。”
一位老阿婆颤颤地对父亲说:“无论如何小姐在我们心中也是天女一样的人,若没有那场雨,南屏都不知要饿死多少人,这全是小姐带来的吉兆。素闻太傅大人清名,送与小姐的只是些自家做的小东西值不了几个钱,断不会辱没了大人的清誉。大人收下吧。”
“大人收下吧!大人收下吧!”
对着长乐都百姓们的质朴眼眸,父亲再不好推辞,命家人把礼物一一收了。父亲湿了眼眶对着百姓郑重地一躬到地。礼物确实不是什么贵重之物,心意却千金难比,女人们做的小裳小袄小鞋子,普普通通的家织布,细细密密的针脚,可爱的绣花,小盘扣;男人们刻得小鸭子,小兔子,小波浪鼓,一件件的竟堆满了整间屋子,于是我成了长乐都中礼物最多的小女孩。母亲红着眼睛抱着我也对着大家施礼。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和母亲每每于我提起当日,依然会泪流满面。若我是男儿,从文或习武定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筹百姓们当日的深情厚爱,纵是女儿身,这情也已然流入骨血中,怕是要至死方休了。
我的生命中总是汇聚着各种各样的巧合。人群刚刚散去,一位云游的行脚僧停在了我家门口。“施主请留步。”
父亲母亲转身,见是位年轻僧人,有些莫名,忙对他施礼。“不知大师叫在下留步所为何事?”父亲答话。
“敢问女施主手中抱的可是令千金,长乐都中人人口中的天女?”
“正是小女,天女一说不过是百姓们的错爱罢了,小女平凡无奇。”母亲依然恬阔浅笑。
僧人微微蹙眉,“贫僧失礼了,观令千金面相自是一番清奇的命格,养在红尘中难免不天涯漂泊,恐福无永寿。若二位施主舍得将小姐舍与贫僧,方可保令千金一世安然。”
母亲听罢只是略略一怔,不以为忤。
“疯和尚胡说什么!”一个家丁听不下去冲上前就要对那僧人推搡,被父亲一把拦下。
“不得对大师无礼,退下!”
家丁只好嘀咕着退到了父亲的身后。
父亲又一施礼,“多谢大师。人本是尘世中人,生而入红尘,灭而湮于土,何惧惹尘埃。然父母若为自己安心就夺了孩子的境遇种种,那便是私心了。”
僧人朗声大笑,眼中有了一丝了然,“见闻自在,不住无为,施主大智慧也。”
“相逢便是有缘,施主可否愿意让贫僧做这孩子的师傅?”
父亲母亲点头微笑,忙把僧人请入家中。于是,在满月那天我有了一个和尚师傅。
师傅萍踪云影,游走四方,但每年都会来太傅府上看我两次,每次住上那么十几天,有时对我讲四海见闻,有时也对我讲些佛理禅机,有时干脆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我疯玩。临走前也总会给我留下些小礼物,有时还会留下些功课。
和尚师傅做我师傅那年才三十出头,样子却比父亲要年轻很多,不像师傅倒像是哥哥。家里的小丫鬟们每次看见和尚师傅都会慌慌忙忙地施礼,低着头绯红着脸颊匆匆跑掉,远远地再怯怯地瞟上一眼,一溜烟的不见了。我禁不住暗暗称奇,太傅府上的规矩礼数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于是,小小的我常拉着和尚师傅的手,得意洋洋的对着丫鬟们扮鬼脸。
长大些,我才知道和尚师傅竟然是名满天下的净土宗高僧,法号名资云。自二十五岁比丘戒满后便云游四方,彼时还有国君延请他去皇家寺院当住持也被他辞了。可谁料想就这么是个高僧会千山万水地跑到长乐都来,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当起了师傅。师傅的名头太大,年幼的我竟也心虚了,可又偏偏大不敬地跑去问父亲,当年怎么就轻易同意让我拜师,不怕和尚师傅是个江湖大骗子么?父亲一巴掌拍在我头上,“疯丫头。”而后极其认真地对我说,“识人,看清他的眼眸就可以了。”对这事我也问过师傅,怎么一冲动就收我为徒了?师傅又端出相逢便是缘的说辞,我便扁着嘴看着他,分明就是不信。于是,他又说,当年见我的目光澄澈,忽而又狡黠灵动,便断定是个极有慧根的孩子,又观我父母都是恬淡之人,料想我的性子也会不错,就这么收我为徒了。说到这儿师傅轻叹,我却在心里想和尚师傅定然不愿承认自己看走了眼。等到多年后我真的淡了性子,师傅却又感叹,原是做个疯丫头更好些,这便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