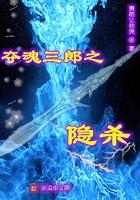韩松换了身干净衣服,清洗了一下脸,径直向南。
离天亮还有不到一个时辰,月色已经黯淡。
韩松取了章凯和曹骁的背书,一路疾行。
营盘东边的巨大骨弓已经被当作战利品送往京都了。韩松眼看着就要到了山下,突然一个身影把他给截住:
“嘻嘻,这下姑奶奶看你往哪里走!”
韩松愣了愣神,张笑笑?她怎么在这里?
张笑笑嬉笑着说道:“大叔,你是不是要去杀人?带上我吧……”
她突然愣住了,黯淡朦胧的月光下,韩松的身形没多大变化,但是他的脸色很差,或者说,很吓人。
“走开!”
韩松怒吼了一声,他脑中全部都是杀戮和复仇,所以不高兴时语气格外暴戾:“谁踏马让你来这里的?”
张笑笑第一次被人骂脏话,委屈得一下子没说出话来。
韩松则是脚步一错,便从她身边走过。
那是山下大军,盔铠碰撞声、号令声已经隐约能够听见了。
韩松冲到了大军后方,高声喊道:“骁字营请见!勇字营请见!”
有兵士来验了信物,放他进去了;张笑笑则被刀枪拦在了外面——这几天她一直在这里,因为韩松肯定会来,但是她也不敢直面无穷无尽的军队——那是沮渠夏也只能束手的武朝铁军。
她只能等。
韩松见到了临阵指挥这次围剿的大将军赵括,两人其实是旧相识——赵括其实是“竹先生”孟宗的兄长。
韩松指了指自己发青的眼眶,说道:
“没时间解释了,带我去杀人!”
赵括点点头,说道:“皇上招募了几个好帮手,就等你了,这次他们会助你一臂之力。”
韩松皱了皱眉头轻蔑地说道:“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宗师境界有多可怕吗?他们要是有一口喘息之力,就能够创造出无尽的可能——我不认为除了宗师还能对抗宗师。”
韩松入魔,自身内力和匈奴人的血气合二为一,才勉勉强强算是达到了宗师的层次——但是经脉大脑无时无刻不在传来灼热的痛感。这种病痛无法解除,这种方式无异于自杀。
赵括:“去请那几位进来。”
闻声而去的士兵带了几个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的人进了营帐。赵括道:“我来给你介绍下。这二位是王满、张俊彦,江南来的武道强者,其中张老弟还是你的老乡,他祖籍也是白州人……”
张俊彦盯着韩松的眼眶,看得韩松心里一阵烦闷。
“……还有这位,是圣上派来的,金大师。”
“金大师?”韩松听到这个脑子里居然有点惊讶,这位可是一直呆在皇宫里,怎么肯出来?
金大师,全名叫做金印,因他极度爱财和惜命,所以一直有个外号叫做金银,金银财宝的金银。当年被徐阳以重金和养生方子聘请,怎么这次会出宫来?
金大师道:“这次皇上给了很多的赏钱,所以老朽还是来这一趟。”
他对韩松说道:“这两位你可不要小看,其中王后生的外功、张后生的剑法,都不简单呐。”
韩松这才收起了对两人的轻视之心,的确,有才之人太多了,虽然他们不能够早早就达到宗师的水平,但是完全可以在某个方面无限地接近宗师。就像张笑笑,不也是轻功身法和内力天赋异禀,不亚于宗师的吗?
该死,我怎么又在想张笑笑?
十九呢?
韩松沉默着,头脸稍微向下,似乎在想什么事情。另外的几个人:赵括、金印、王满和张俊彦则是神色各异。
赵括脸庞上满是凝重,要是这次袭杀失败,沮渠夏就会在短时间内没有任何的同级别的敌手,届时,只能用成千上万的人命去填、甚至全军都可能被全灭!
金银则是为一个天价的赏金暗暗自得;他浑身上下都是保命手段,那些看起来很扎眼的金银饰器其实是重金打造,各有妙用。
王满则满脸阴沉——虽说确实是效命皇家,但是他没想到第一次便是让他去迎战成名的武道宗师,虽然有四个人,但是他和张俊彦无疑是最容易最先被杀掉的——那可是武道宗师!即使皇上特意抽出了时间劝慰他们,许诺下了极为丰富的奖励,但是不同于兴奋起来的张俊彦满脸的“士为知己者死”,他王满最先想到的,便是这天大的富贵,自己到底有没有命拿!
张俊彦脱口而出:“你可是魔道中人?”
这话中的你,便是指的韩松。
韩松这时受不得激,豁然起身道:“那又怎么样?”
张俊彦:“正道有约:‘凡是修炼魔道者,都是正道死敌!’我不愿与你合作!”
金印出来打圆场了:“两位冷静,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啊。”
张俊彦则不依:“魔道功法杀戮过重,当年两位宗师出手,魔道早该死绝了,为何你还能有传承?”
韩松哂笑一声,问赵括道:“赵老哥,皇上就派这么一个固执顽固、不识时务的废物来杀沮渠夏?”
赵括还没说话,韩松便道:“国难当前,沮渠夏若是不死,我武朝必将生灵涂炭,枉你自称正道,连这天下苍生都不顾了吗?”
他声音已经有些尖锐刺耳。
张俊彦想反驳,但是一下子说不出什么;他徒然地张开口,憋了半天说出一句:“反正,我是不会和你一起上山的!”
韩松看了看沉默的王满和赵括,摇了摇头,说道:“金大师,我们走吧,时辰不多了。”
他又丢下一句:“现在匈奴的宗师杀了二千二百多人,你刚刚口中说的,杀了我兄长的两位宗师,现在在哪里?我朝将逢大难,正道有几人来边关?”
月已沉,天未亮。
————
白州,宋氏医馆。
十九还在沉沉睡着。这几日来,他睡睡醒醒,体温烫得吓人,宋清扬花了好大的劲,现在烧是退了,但是又吃不进东西、吃多少吐多少。
水都不能喝。
而十九自己说,口中会流出涎水,而那涎水一触喉咙,胃就翻涌想吐。
另外,想将涎水吐掉时,也会牵扯到胃,同样作呕。
宋清扬愁肠百结,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医这么多年,看过这么多医术典籍,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提到过类似病症的只言片语。
十九的身体越来越差,七八天来,这消息实在是瞒不过,十九他娘听说了,急急忙忙赶来了医馆。
十九已经呕不出东西来了……喉咙被胃酸腐蚀,疼痛不已;最后苦涩无比的胆汁也通过食道口腔被呕了出来、整个腹部内部纠结着抽搐式地疼痛——那一瞬间十九觉得自己是真的已经死了吧。
生无可恋。
但是十九没死,事实上,宋清扬看到了他吐出绿色的胆汁时就已经慌了手脚,连忙点了他的昏穴。
但要是只靠点穴就能够解决问题就好了。
何氏给十九擦了擦嘴角,哽咽着对宋清扬说道:“宋神医,十九他再这么吐下去,可怎么办才好哇!”
张老头在她身后说道:“这样下去身体迟早会垮掉,还是给十九吃点东西吧?”
宋清扬用力地摇了摇头:“不行,甭说是药,吃什么都吐……他这是伤了胃经……”
他看向十九的胸膛:“上次那只老虎伤到的地方,不仅仅废了一条气脉……还伤到了胃经,现在受了风寒一下子病症全都发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十九躺在床上,眼睛紧紧闭着;脸色苍白,还没七天就消瘦了不少。
此时他似乎又一次沉入梦境——同样的大漠、大河、黄皮大虎。
————
张九和种远扬站在白州城北门门口。
“回去吧,送到这里就行了。”种远扬看着张九:“刚刚接手,你还有很多要处理的事情,赶紧回去吧。”
张九道:“徒儿定不会辜负师傅的期望,一定会……”
他话没说完,种远扬扬手止住了他的话头,食指指了指他嘴,没说什么,转身上马走了。
张九突然感觉到,方才他话头止住时,有一道隐晦目光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但是这种感觉稍瞬即逝,让人不再确定。
张九皱了皱眉头,然后转身回去了。
他走之后。一个人影匆匆从在城门后的角落里经过。
————
西北。
沮渠夏站在矮山上。这里可以俯瞰底下所有人。
穿着黑色盔甲、举着红色旗的军人。
骑在马上,眺望这边的将领。
这两类人,他杀得够多了。
好像这十天来,杀了很多武朝的人呢。
有点记不清楚了,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呢?
沮渠夏有些恍惚,他手中捏着一个绿色的琉璃小瓶。
那是背弓奴留给他的,遗物。
背弓奴那张弓,和藏在拐杖里的那根箭,都留在了武朝边境。
他感觉到神智有一瞬间的抽离——胃里传来的饿感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但是,他舔了舔自己焦裂的嘴唇。
然后掏出那个绿色的小瓶子,在自己暗黄色的长刀刀锋上碾碎。
杀不了皇帝,只能把这点毒用在这些说不定就潮水似地涌上来的兵卒身上了。
没洗过澡,也没换洗过衣服的沮渠夏,身上很臭。
血液的腥味,汗水的酸味。
武道宗师也会发臭。
他已经三天没进食了。
三天前被围在山上起,以小队形式上来送死的兵士身上,就再没携带过食物。
武道宗师也是人。
人是铁饭是钢。
沮渠夏觉得,今天可能是他最为虚弱的一天了。
甚至都不确定还能不能撑到明天。
沮渠夏有些茫然。
到底为什么要刺杀皇帝呢。九年前。
恍惚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有想起。
————
相比沮渠夏的茫然,韩松则冷酷认真得多。
他本来就是这种性子,入魔之后四肢经脉的疼痛无时不在提醒他时间不多了。
记得十几年前,在沙场上和徐阳一起,每次他去喊援兵的时候,都在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了,所以更加要冷静。
这是徐阳的原话。那个“生而知之”的男人,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性格魅力和领袖精神。
韩松身边,张俊彦盯得他死死地。
在张俊彦看来,韩松比沮渠夏更加可怕。
因为沮渠夏必死,而韩松,可能还会继续杀人。
哦对了,沮渠夏刀下亡魂,已经不下三千人。
这是个恐怖的数字张俊彦想到。但是想到师傅和师公对他的叮嘱,他咬咬牙便更关心韩松的神色。
那青色的眼眶,眼睛里像是有火在烧。
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个男人的五官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种很容易让人着迷的内蕴。
张俊彦知道自己长相继承了白州和江南的优点,所以其实在别人夸奖自己外貌的时候,会有一种淡淡的自信和优越感。
这种感觉隐藏地很深,他自己都很难感觉得到。
但是细看这个男人,他已经消瘦下来的两颊,唇吻,眼睛,眉毛……
有一种世事沧桑的男子气概。
一路往西北来,张俊彦对这种气质十分敏感。
这是一直在南方的张俊彦很难拥有的气质。
而,一路以来,韩松身上最为明显。
他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韩松感受到了他的目光,没有说什么。
正道,和魔道……
有区别吗?
武功,不都是杀人手段?
何苦绕来绕去猜谜呢?
他仰头,看向俯视天下的沮渠夏。
俯视天下么。
果然还是宗师的气度啊,这行为。
但是!
韩松突然兴奋了起来,尽管这情绪被掩藏得很好,但是一直在观察他的张俊彦,敏锐地发现了这点。
但是沮渠夏完全没有发现他们!
作为宗师带队的、大部分都是岁月境以上的小队,沮渠夏在人群中没能够一眼看出他们来——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沮渠夏已经不在状态!
是时候了!
金印对韩松说:“皇上有令……我全听韩先生的。”
韩松点点头,对几人说:
“其实我本来只打算一个人来会会沮渠夏的……但是有诸位,今日必杀此獠。”
“诸位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做好回不去了的准备……不然,还来得及回头。”
“没人反悔就好,那么现在是接下来的安排……”
————
十九浑身发凉。
若不是还轻微有些呼吸,几乎就要放弃他了。
“最多再过半个时辰,就必须唤他醒来……不然会出更大的问题的。”
宋清扬说道。
何氏侧坐在十九床边,也瘦了不少。
从医理上说,十九的病很难解;没有办法服药,只能通过针灸或者推拿——但是现在体质太虚,完全不能这样治疗。
现在的十九小脸上还隐约有着痛苦。
宋清扬想到他以前那动不动就笑吟吟的双眼,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在揪着不放。
雷胖子、温华也来看过几次。
温华的伤快好了,武功也开始每天练习。只是雷胖子很少像以前那样粘着他不放,他常常往十九那里钻。
至于张老头、宋清扬、何氏,几乎每天都呆在十九床边。
宋清扬出手解穴,十九皱了皱眉。
睁开了眼睛。
那是一双渴求活下去的坚强眸子。
他先吐掉口中积余的涎水,然后开口问周围熟悉的大人们:“我睡了有多久啦?”
何氏抢先说道:“已经睡了……两个时辰了。”
十九说道:“娘,我想看书……”
何氏道:“你好好休息,看什么书?身体好了,不就随便你怎么看?”
十九摇了摇头,说道:“我想看书。”
他居然挣扎着下床来。
一众人马上把他按住,道:
“要看也行,别乱走动啊。”
“你想看什么书,雷哥给你拿来。”
“别动啊十九。”
十九看了看周围这些长辈,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温暖。他看着宋清扬说道:“师傅,我想看我爹爹留下的那本书……”
“我想我爹爹了……”
————
韩松则不然。
已经压制不住魔焰滔天的他,几乎是一动手就被沮渠夏察觉。
但是这时候,他们一行人已经摸到离他只有二十余丈的距离。
金印第一个出手。
但是沮渠夏却迎上了韩松。
韩松想到一路走来看到的那些将士的尸骨。
和当年大哥死去的惨状。
就压抑不住内心的杀意。
他手中没有武器,因为他最强的就是一双肉掌、十根手指。
这是必然的厮杀,沉默无言。
沮渠夏手中暗黄色的刀锋上,有隐晦的绿色。
看起来,有妖艳的美感。
韩松身法诡异,在刀锋所及之前,绕到了沮渠夏的身后。
沮渠夏头也不回,马刀回手就是一刺。
马刀说是刀,但造型细长,如剑,可劈可砍可刺。
韩松呼地伏地!
这不合常理的举动,让沮渠夏的一击再次落空。
仿虎形。
韩松咆哮嘶吼,似乎要把那种仇恨全部宣泄出来。
这也是发力方式。
一扑!
沮渠夏刀势已老,抽身向一侧退去;
一纵!
韩松蹂身而上,仍然腹部贴着地面!
那不是人类的行为,对下肢的要求太高,发力的角度也不对。
强行发力,肯定会很别扭难受。
但是韩松仍然向沮渠夏冲去,如同猛虎掠食般无畏且霸气。
沮渠夏用刀背挡住了他的十指,一声刺耳的刮擦声响起。
金印剑到!
他的配剑中金子的含量很高。对此韩松其实只有四个字评价,华而不实。
沮渠夏手中暗黄色的马刀,在金刀上硬生生怼出一个缺口来。
金印一击不成便向后退去。
王满杀到。
张俊彦出剑。
他二人速度不够,所以来得迟了。
王满的拳头,张俊彦的剑。
在沮渠夏看来,实在是……浪费。
因为二人少了精髓,只是些傻瓜力气、绣花架子。
他不屑出刀。
脚步一错,沮渠夏向韩松那边冲去。
韩松躲闪刀芒,向后退去。
“武朝那娃娃皇帝,还是低估了我啊。”沮渠夏想道。要知道,他的成名已久,仅凭一个老头子宗师加上两个年轻人,也还是不够。
只有这个魔道中人,才有伤得到他的狠辣。
那两人攻击落空,而韩松也反击了一爪。
沮渠夏一惊回神,回刀,但是韩松已经跃出了刀芒之外了。
心口处衣服破了。
若是再来一次,说不定就殒命了?
沮渠夏立马开口,用蹩脚的汉话说道:“中原武林,正道居然也和魔道之人混到一起了吗!你,小子,你这剑法我认得,是碧峰山居士的亲传,他当年杀起魔道修士那可狠得很,只是现在徒子徒孙,越来越不像话了!”
这几句话都是说给张俊彦听的。后者听他说出师祖的名字,不由得羞愧起来,一下子攻势减缓,沮渠夏得以喘息。
韩松大口喘着气,沮渠夏的每一刀都很难躲,但是他可以。
他的身法步伐已经超过了沮渠夏,这是最大的优势。
还有一个优势……
“一起上!”
韩松大吼一声,正面迎上沮渠夏。金印从左,二人从后。
沮渠夏也打得拼命。内力激发下,他手中的马刀一瞬间变化得金黄。
炽烈得烫手。
金灿灿的,耀眼而美丽。
比起金印手中浮夸的长剑,纯粹得多,也荣耀得多。
这是大漠勇士才能够有的“天赐”之物,那年从单于手中接过时,沮渠夏就发誓要效忠单于,做他最锋利的刀。
今天,这柄刀也不会断,它会扫平一切!
韩松的压力最大。沮渠夏的眼睛中有莫名的狂热,而韩松的眼睛里,那是愤怒。
怒不可久。
金印对着沮渠夏旋转着的马刀流口水,那是非常值钱的好刀哩。
沮渠夏旋身,暴喝着挥舞马刀。
金色的刀芒画成一个圆。
想起来,徐阳若是还在,看到这招,说不定会笑着起个叫做“旋风斩”的名字?
刚刚沮渠夏说了什么,韩松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胸膛被刀锋擦过,无畏地冲上去,一爪在沮渠夏腰侧撕下一块皮肉。
在下一次刀锋到来之前抽身而退。
想起来徐阳,他就觉得心里难受。
于是忽略了胸口伤了又伤的地方的隐约麻痒。
王满的拳,张俊彦的剑,都被一刀划过。
拳头渗出血,而宝剑折断。
沮渠夏还在质问张俊彦:“你和魔道之人合作杀我,难道你师祖师傅会答应?”
而金印的犹豫救了他一命。
又送了他一场好富贵。
他终于出剑,而这一剑插入了沮渠夏的脖颈,沮渠夏登时立死。
金刀脱手,一切都结束了。
匈奴最锋利的刀,也还是会被折断的刀。
几人就像是突然被抽空一般,不顾风度气度地瘫在地上。
沮渠夏,死了,而他们还活着。
至少现在还是。虽然,会不会马上就兵戈相见呢?
————
十九看着那本先帝留下来的武道感悟。
那些字在他发虚的眼眸中看起来犹若是在跳动。
就像是,儿时那天他看韩松舞剑,剑锋卷起飞雪时一样。
————
十九卧床多日的消息自然瞒不过孟宗。
孟宗只是皱了皱眉,他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宋清扬已经是白州城最好的大夫了。
若是宋清扬还在宫中,说不定也混的到全国最好这样的名号。
这个消息,还是先瞒着鹰隼吧。
说到鹰隼。
他带着一帮衙役捕快,直接冲向了游侠会的集会地点。
捕了十几人。
但是早就发现异常的张九则没有露面。
他现在正被官府通缉。
罪名是:谋逆、蓄意杀人以及预谋刺杀朝廷命官。
其实只要有第一条罪名就够了。
但是鹰隼不依。他很后悔这次没能够做好。
明面上,游侠会已经没有了,这次的行动已经由竹先生报告上去了。
接下来,他和孟宗就该是启程去济南府了。
终于知道十九大病了一场的鹰隼,第一次对竹先生生了气。
尽管藏得很深,但是孟宗一眼就看了出来。
“你不高兴?鹰隼,你果然还是太嫩了。”
“你对我的埋怨,太明显了。”
“这次的行动失败,肯定也是你先露出了马脚吧。”
“真的要是让你穿插到敌后……你这城府太差太粗浅,还不如送死。”
一番话,说得鹰隼几乎要哭出来,不管怎么说,训练了多么多,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最后,竹先生总结了:
“这件事回济南再说。现在给你半天假,去看看十九吧。”
“——慢着,这是你最后一次叫‘韩七’的时候了。”
他喊着几乎要跑起来的鹰隼,带着歉意地笑笑,说道。
————
大军退去。
“咱们走吧,向皇上邀功去。”
击杀是算在金印头上的,这老头儿笑得皱纹都闪闪发光,催促着众人赶紧起身。
还不忘记把那把马刀捡起。
“等等啊,金老……”王满开口说道。
“怎么?”金印反应很强烈,生怕别人抢了了自己的功劳一般。
“……我好像,中毒了……”王满脸上满是苦涩地说道。
“中毒?”
几人惊讶地检查了一身,其中金印反复检查了好几次。
“这马刀上有毒!”
韩松这时才觉得胸口已经没有了知觉。像王满那样,伤在手上,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异样。
这时王满对金印说道:“五百两银子!砍断我双手!”
话音刚落。
金光一闪,王满的双臂就离开了肩膀。
然后金印看了看韩松,还想看看他身上能不能赚到一点钱,但是韩松苦笑着摇了摇头。
果然还是……回不去了吗?
还在看着他的张俊彦看到,韩松眼睛即将闭上的时候,有一点点液体的影子闪烁了一下。
“你们走吧……金老爷子,日后还请保护好陛下。”
“你……”金老爷子点点头走了,止了血的王满也准备走,张俊彦开口想说什么,却发现不知道还说什么。
韩松看他一眼:“别听他说的,你师傅不会怪你的。”
好像没什么力气发火,他还是笑了笑:“这样,对大家都好。”
韩松还是瘫软在地上,一副惫懒样子。以前每次大战完,兄弟几个都这样,一根手指都懒得动,只不过这次他是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以前是七个人……渐渐地,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么躺着了。
一切回忆一切经历,如潮水般从他身边席卷一遍,而后退去。
韩松闭眼前看着一个模模糊糊的曼妙身影奔来,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还是来了。”
张笑笑等到大军开始退却飞奔上山。知道了韩松将死的赵括,没有让人拦她。
“大叔,大叔你怎么了……”
“大叔,我师傅,她还在等你啊……大叔……”
张笑笑抱着他的头带着哭腔说道,而韩松,只是把头靠在了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笑笑。
————
“十九,你看谁来了?”
“七哥!?”
“韩七”笑着看了看十九的脸色说道:“十九啊,你这身子,还得好好养养……”
“平时摔跤打架时候那般力气,都到哪儿去啦?”
十九也跟着笑笑。
韩七问道:“问你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小兰去哪儿了?”
“小兰?她很久没来过了……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十九老老实实地回答道,面色有点羞赧:“你这样子说,我突然有点想她了。”
韩七点点头说道:“好吧……她们一家子突然就搬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儿,我以为她会和你说呢,所以才来问下你。”
“对了,这次特地来白州城,是要出远门咯。”
“出远门?”
“对啊,我要出去闯荡,见见世面,拜师学艺什么的。”
“哈哈,那可不好吗?”
韩七脸上的表情眉飞色舞:“当然!”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玩闹了一阵。韩七见十九话开始少了的时候,便起身告辞了。
十九仰躺在床上,看着韩七转身而去的背影,不由得脱口而出:
“七哥,保重啊!”
他是多么羡慕韩七这种可以自由去闯荡,而不是像他这样只能够按照父母的安排学东西的可怜样啊!
十九咬了咬牙,对自己说,学武,我一定要学武。
鹰隼没有说话。从这里离开以后,就要面对张九的事情,压力很大的他面色有点沉重,但不管怎样,还是笑了笑。
————
在韩七和何氏等人告辞离开医馆的时候,张九正不知在何处逃窜,躲避着官府的追踪。
而胖子和温华,则在默默收拾东西。
“胖子,你真的不肯跟我走吗?”
温华看着这个低眉顺目的胖子,突然泛起一种舍不得的情绪。
胖子说道:“不了,十九还没好,我在这边他可以好得更快些。”
“……”
胖子接着说道:“以后老大,你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了,有什么事情不要老是发脾气,也不要老是太相信别人。”
温华愕然抬起头,这个实际年纪才十八的大胖子脸上,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可靠感。
这一瞬间,温华有种错觉,在市井里摸爬滚打,挨打长大的胖子其实对这个人生,看得比他这个当老大的,还要清楚。
等等,胖子要是论起挨打,恐怕也不比什么武道宗师差吧!?
但是当胖子一笑,刚刚那种男子气概又荡然无存了。
“嘻嘻,老大,在外边看到有什么好吃的都托人带到医馆来啊!”
温华哑然一笑,一拳擂在了他的胸膛上,发出熟悉而厚实的一声闷响。
这样的一拳,对胖子来说,什么都不算。
温华感受着伤病皆去,终于不再虚弱,生命力量澎湃的身体,不由得眯起眼睛笑了笑。
游侠会已经没有了。
种远扬也远离此处。
胖子也安定了下来。
张九则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终于好了。
那么天下之大,何处我不可去得?
胖子看着这一瞬间扫遍了阴郁的温华,也咧开嘴,笑了笑。
————
挛鞮昊昊身亡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耶曼单于那里。
“这个孽子,居然想去学魔功,哼,死了才好。”
“他也不想想,这入魔功夫要是能学,还能够轮得到他?那么多兄弟都等着呢。哼。”
“今年那汉人武国,本单于还不想打。”
相比起挛鞮昊昊的那些兄弟,领兵在南边和武朝对峙的挛鞮昊昊只是个不上不下的水平。
他既没多少统领天赋,又不会揣摩他的汗父的心思。
耶曼单于已经年近六十,但是他平日里没有显现出丝毫老态。
依然大口吃酒大楼吃肉,翻身上马裸身摔角,仍然时不时地还能要几个女人。
相比之下,中原武朝那小儿徐皇帝,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稚童。
“听说,武朝那娃娃皇帝,打算要选妃了?唔,开窍了这小子?”
坐在王座上的耶曼单于面前,站着他的第一智囊,塞隆。
匈奴和武朝,是两个庞然大物,矗立在人世间,争着夺王朝更迭的胜者。
“正好这次武朝立国九年要大庆,随便从那些女儿中挑一两个送到武朝那边吧。”
塞隆劝阻道:“不可,我匈奴这么多年来,不曾和汉族通婚过,武朝立国不到十年,他们的皇室没资格让我匈奴王女下嫁。”
“哦,说得有道理,那么找几个犯了事想求情的大臣,看谁家有女儿还没嫁的,要是答应去武朝做个天子妃的,就免了抄家和死罪吧。”
塞隆答应一声,下去安排了。
耶曼单于喝完最后一口马奶,玩味地笑了笑。
————
曹骁呆呆地看着手上的捷报,难以想象作为一阵之主帅,居然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出神。
他旁边,站着黎虎和章凯。
两人神色不同,但都有些不可置信。
良久,章凯先说话了:“不可能吧……区区一个宗师,就能杀死韩前辈?”
他印象里,韩松是几个宗师十几岁月都拦不下来的强者,区区一个沮渠夏,即使加上背弓奴也不够看啊。
黎虎低声骂道:“这个沮渠夏,是不要宗师的脸面了吗?居然敢用毒?”
曹骁开口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他首先是个军人,之后才是宗师,用毒只是一种手段,换做是我,也会不择手段,而且”他顿了顿,接着说:“而且他的哑巴仆人,就是死在我们的毒刃之下的。”
黎虎支唔了几下,什么都没有说。
章凯问他:“此仇不报……非武朝之人,韩前辈家眷妻小……你可有办法联系上?”
黎虎道:“末将立即派人去白州,定不辱命!”
章凯:“什么定不辱命?老子现在放你的假,你亲自去!把他们娘俩安顿好!听到了没!?”
黎虎截然答道:“是!”
————
“姐姐,天天在这宫里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好闷啊。”宋璇儿对种琪撒娇道。
种琪一身素色衣裙,道:“你啊,安心等着吧,选妃的日子也不远了,要是我说你啊,还是在宫里认认真真地学点规矩的好。”
宋璇儿道:“啊……这里好无聊啊,姐姐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啊?以前跟我爹爹游方行医的时候见过很多有趣的东西呢!”
“出去玩?那怕是别想了。”种琪蹙眉道:“你现在已经是秀女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秀女还能够活着离开皇宫的。”
“什么!不是吧姐姐,爹爹他说送我来选妃,没选上的话还不能回家吗?”
种琪捏拳道:“要是你真的成了贵妃,甚至是一国之母了,那时候才可以回家省亲吧,至于现在,咱们就要努力进皇上的眼了。”
宋璇儿看着种琪,发现后者的眼神里有种陌生的东西。这种东西她不懂,于是摇摇头问道:“姐姐,为什么要进皇上的眼?”
种琪微昂起头,瞥她一眼道:“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只有成为了皇上身边的人,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比如刚来的那时候,你不想给银子给那唱名儿的太监,但是要是不给,恐怕咱俩就会被拦在外边,连宫门都进不去了。若是咱有了身份,那至少不用在这样的地方受刁难。”
“进不了宫,那还不好?反正这里面规矩严死了,我可不想呆在这儿。进来之后后悔死了。”
种琪呵呵一笑:“可别这么说!要是我俩没进皇宫,京城这么大,举目无亲,你怎么回去?”
“反正我家里派来的人送我进宫门便回去复命了,偌大的长安,只有我俩是认识的。再说一遍,妹妹,以后在宫里,咱俩,可一定要多多帮扶。”
宋璇儿看了看神色有些冷厉的种琪,怯弱地点了点头,她还想问下“黎大人”的事情,不过想到种琪也只是刚刚来京城,肯定也不知道,于是眼珠暗转打定主意,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打探消息。
————
此时,年轻的皇帝正在伏案疾书。
终于,他放下了笔,让伺候的小太监把卷宗奏折带了下去。
他环视了一圈空无一人的书房,沉思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徐颛顼突然觉得后背生凉,惊得站起。
却发现案前茶水早已经凉了,偌大的屋子,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些生气。
“纳妃?朕需要吗?”
他自言自语,却也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得上话吧。
“传王海进来……朕有事问他。”
小太监从门口离开时,这件书房真地没有了一点点人气。
“呵……所以就都好聚好散么?五叔?还有以后的六叔、七叔?”
徐颛顼浓眉微微皱起,淡淡一笑。